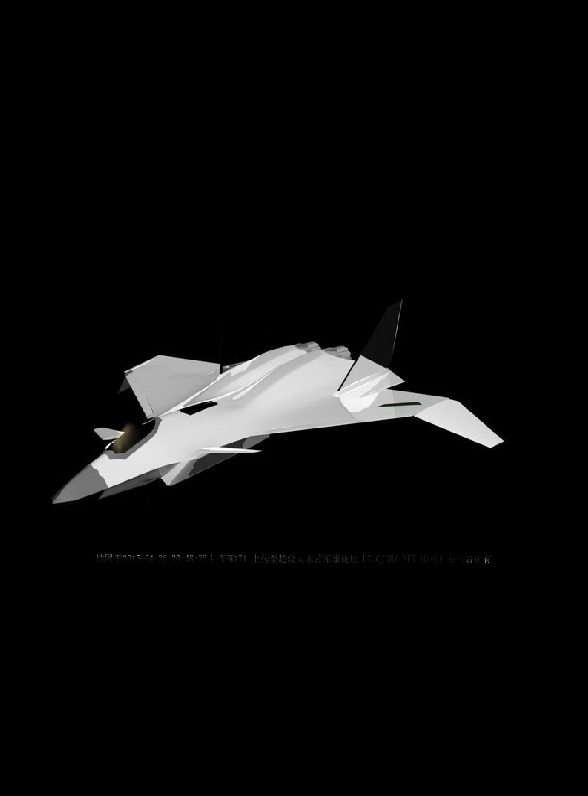雷怒海和童牛儿一前一后,从院子花园的后角门出来,看四下无人,便躲藏在暗影里向东厂行来。
这东厂曾经在雷怒海手里掌管多年,他自然最熟悉不过,领着童牛儿直向西山墙行来。童牛儿虽然不明白他的用意,但知道必然有捷径可走,所以也不问什么,就在后面紧紧地跟随。
两个人走到西山墙下,行出十几丈后,雷怒海站住。童牛儿才见那山墙上原来开着一个一尺多高的洞,是用来排放污水的。但洞口竖有一排粗如鸡卵的铁栅栏挡得严实,别说是人,就算一只老鼠胖了都钻不进去。
童牛儿不明白雷怒海的用意,怔怔地看着他。雷怒海却向他诡异的一笑,然后低下身,把手里的匕首向那铁栅栏上砍去。童牛儿虽然常听人说起吹毛利刃,也见过端木蕊手里的逆龙宝刀,但从没想过这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东西能有多厉害。见雷怒海如此,忍不住在心里冷笑一声,不明白他手里那片破烂的铁片能把如此粗壮的铁栅栏如何。
却不想只听到一声脆响,那栅栏竟然应手而断,干净利索。童牛儿被惊呆,才知掉传言不虚,这个世间竟然真的有这种切金断玉的宝器。雷怒海挥动饮光,把栅栏一一放倒,直到洞口已经宽敞到能容一个人通过为止,然后低身钻入。童牛儿在后面跟随着,两个人向里面摸去。
这诏狱就坐落在东厂的西南角,所以二人进入东厂后没走多远就到了诏狱的外面。抬头见诏狱之中灯火通明,一队队士兵在灯光里站立。雷怒海自然知道这样森严的守卫还是自己曾经立下的规矩,却不想今日竟然成为阻拦自己救女儿的障碍。
其实凭着雷怒海的武功,想要杀进去并不费什么力气。但要是进入诏狱,再带着个活人出来,还想全身而退就难了。这些卫士只要被惊动,就会立刻向在东厂内驻扎的锦衣卫求救。锦衣卫却不比他们,里面有不少武功造诣深湛的好手,若齐力围攻自己,自己恐怕无论如何也敌不过。更何况身边还跟随着一个童牛儿这样的废物需要自己保护,若叫他陷落在这里,就算救出女儿又能如何?谁来养她?自己已经年近六旬,还能有多少天好活?又怎么能照顾痴傻的女儿到老?
每当想到这些,雷怒海都不禁悲从中生,觉得活着毫无希望可言。其实他早就潜伏在那个小院里,已经无数次潜入东厂来探看女儿的安危。但之所以一直迟迟不肯出手救女儿,就是因为不知道救出之后该如何。此时见童牛儿现身,雷怒海恍然他才是女儿最后的归宿。看童牛儿肯拼死来救女儿,以后好好照顾若雪应该不成问题,让雷怒海放下心来。
童牛儿怎样的机灵?自然看得出雷怒海为什么站在这里不动。低声向他道:“我去那边放几把火,把他们都吸引去,你就有机会救人了。” 雷怒海听罢不禁暗暗地赞叹童牛儿聪明。他却不知这是童牛儿最擅长的,到如今这火已经不知道放了多少把了,早已经轻车熟路。
童牛儿在暗影里悄悄摸到自己坐帐的朱雀营的后面,来到存放柴草的地方。他曾经管理这里,自然最熟悉。把在草垛里埋着的几坛好酒扒出来,然后一一打碎,洒在柴草上。从怀里摸出打火的用物,不过片刻就把火点燃了。
童牛儿生火有一手绝的,就是能在最低点燃烧起来,然后慢慢扩大,这样等别人发现起火,想要救应却已经来不及了。这一招是在市井间混迹的无赖都擅长的,因为要靠这个骗吃骗喝,也算是一手本领。
童牛儿待把这堆柴草点燃之后,觉得不过瘾,又到无极营的马棚旁边,把堆在那里的饲料点燃。饲料堆连着马棚,都是被秋风吹拂得干燥的木板搭建的,正好是上好的柴火,一旦燃起就腾火窜烟,烧得汹汹,片刻之间就把马棚烧塌。里面的马匹早就惊炸了群,咆哮着四处奔跑躲避,很快就在东厂的院子里撒开欢了。
这样大的动静自然早就惊动了值守的众兵士,顿时报警的串锣响成一片,把各处的兵士都召唤起来,纷纷撇下刀枪,寻找盆桶打水救火。童牛儿见时机已到,召唤着雷怒海就往诏狱里闯。
诏狱的门前自然也不肯没有人站岗守卫,毕竟这里是看押要犯的重地,没人敢擅离职守,出了事谁也担待不起。雷怒海手下却麻利,只把饮光轻带,就将守卫的兵士放倒在地,叫一边看着的童牛儿暗暗惊讶他手段哦狠毒和武功的高强。
其实在东厂之中谁也没有见过雷怒海使用武功,是以从不知被传言的他是大内第一高手这件事是真是假。此时童牛儿才知道,果然不虚。二人闪身进了诏狱,顺着那条隐蔽在小门后面的楼梯曲折而下,来到幽暗潮湿的地下囚室。
里面值守的兵士听到动静,起身前来观看。可刚近身,已经被雷怒海的饮光撂倒。童牛儿再顾不得一切,大步就往里冲,口中高喊着:“若雪,老婆,你在哪?老公来救你了。”他跑出没几步,迎面就遇到一个守卫过来。童牛儿也不犹豫,手起刀落,把他砍倒在地,然后逼在他的颈下咬牙问:“说,银若雪关押在哪里?”
那守卫早被吓得胆寒,忍着肩头的伤痛颤着声音道:“在里面,左数第二排囚室,到头就能看到了。” 童牛儿曾经在这里关押过,对他们这些专门靠盘剥犯人活命的早就恨之入骨。听他说完,也不客气,把长刀向里一推,结果了他的性命。
童牛儿和雷怒海按照卫士所说寻到那里,果然见银若雪就倒在一堆稻草里,衣衫肮脏,披头散发,已经没有了人的模样。雷怒海看见之后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忍悲道:“孩儿,爹爹来救你了。”一边说,挥饮光把锁头砍掉,将铁门拉开,然后就向地上那人扑去。
童牛儿跟在他的后面,借着昏暗的灯光看着那个趴伏在草堆里的银若雪,却觉得哪里不对,可又说不出是哪里。待雷怒海劈开锁头,扑向那人时,童牛儿猛地醒悟,这个银若雪太胖了,或者说,太壮实了。童牛儿是银若雪的丈夫,时常与她亲热,自然熟悉她身体的胖瘦粗细。而雷怒海并不经常与女儿见面,哪分辨得出?
童牛儿感觉有诈之后,马上向雷怒海大叫:“那不是若雪。”可还是晚了,只见地上那人猛地窜起,把在手里藏着的短刀直向已经扑到身前的雷怒海刺去。雷怒海惊觉不对,想要应变,却已经来不及,那短刀猛地刺入他的胸口。
但雷怒海身手毕竟了得,左手紧紧地握住那人持刀的手腕,右手把饮光也插进了他的腹下,然后拼尽最后的力气用力一划,给他来个大开膛,把里面的下水都抖落在地上。
童牛儿跟着扑进来,想要抱起雷怒海,却见他已经把双眼紧闭。将手在他鼻子下面试探,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童牛儿不曾想到曾经风光一时的雷怒海竟然惨死在自己用来迫害别人的诏狱之中,说起来也算得报应吧。将他轻轻放倒,把他手里的那把锋锐匕首饮光拿过来,然后抵在地上那个还未死的人的颈下逼问:“说,银若雪在哪里?我就给你个痛快的。”
那人早痛得忍挨不过,听童牛儿这么说,倒觉得高兴。断续到:“银若雪关押在,最后那间囚室里。” 童牛儿将手一低,把匕首刺入他的颈下,割断气管,叫他脱离苦海,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最后这间囚室的门是整块厚重木板打制,上面连个气窗都没有,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童牛儿加着小心,先把锁头用饮光砍落,然后一点点将门推开,慢慢探头张望。见昏黑的里面有一张木榻,上面果然躺着一个人,长发披散。童牛儿虽然看不清她容貌,但认得她穿的衣服,果然就是银若雪惯穿的那件素绣襟角的长衣。
可童牛儿还是担心上当,把匕首挡在身前,一步步逼近到这人的面前,低唤道:“若雪。”那人听到这一声,身体猛地一震,含混不清地应道:“相公啊。”童牛儿立刻认出果然是银若雪的声音,喜出望外,扑上把她抱入怀里。银若雪立刻如孩童一般大哭起来,嘴里嘟囔道:“你怎么才来呀,看不把我想死了。”
童牛儿听得好不心酸,跟着落泪,道:“相公来晚了,该罚。相公这就带你离开这里。” 童牛儿一边说,一边把银若雪负在背上,起身就往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