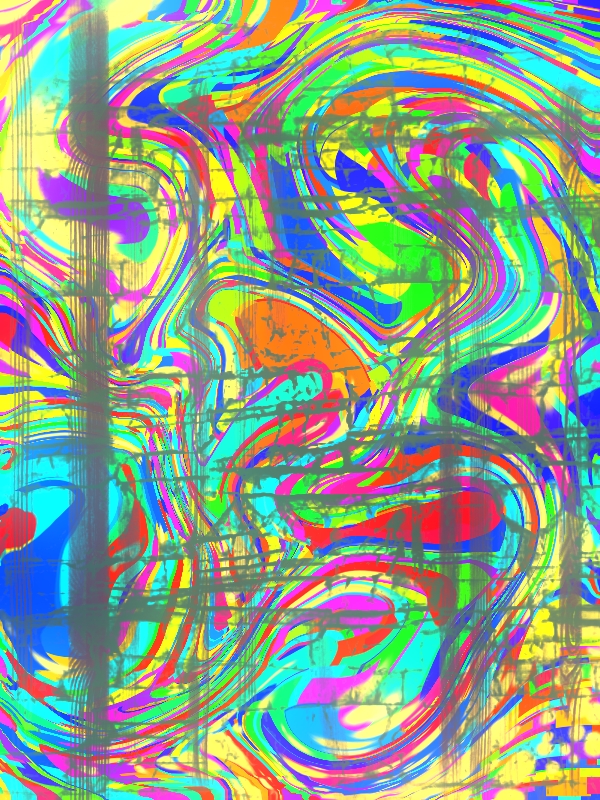可铁刀母夜叉却不是为了这个才扯落面具的。
她趁着雨孤云一怔之际,把银面具抛上半空,双手齐出,分别点向他胸前任脉的天突、华盖两处大穴之上。然后接住落下的面具,重新戴在脸上,把堪比明月般姣好的容颜重新遮掩起来。
雨孤云被点的这两处穴道正是通往丹田气海的窍要所在,一旦被闭塞,立时叫四肢气血不通,浑身酸软,连半分力气都使不出。
雨孤云万不曾想这铁刀母夜叉竟使出这样花巧手段耍诈,待想要防时,奈何双手都在身后,救应不及。只觉得自己在瞬间就成了一堆棉花般轻飘,没有骨头支撑的人,连站立都不能,一截截地瘫软下去。
龙月儿见了大惊,正要向前去扶,却见离得近的铁刀母夜叉已经跨步来在雨孤云的旁边,一把将他搂入怀里支撑住他的身体。右手顺势接住雨孤云因手指无力而慢慢撒开的长剑,提起架在他的颈下,高声道:“若不想他死就别过来——”
后面的众黑衣人见二当家得手,纷纷冲过,手舞刀剑护佑在其左右。
龙月儿见雨孤云临危,急得跺脚,提长剑就要跃上拼命。
老者见势头不对,忙一把拉住她劝道:“你想要你哥哥的性命吗?冲动不得。”
龙月儿无奈道:“你说如何?”
老者道:“且看我问她。”上前一步,向铁刀母夜叉拱手道:“二当家,就算我等输了。二当家心怀大量,放了这小哥,我等就把一百五十两银子奉上,如何?”
他话未落音,听身后的龙月儿叫道:“给她三百两,五百两——只要把哥哥还与我就好——”声音里已带了三分哭腔。
谁知铁刀母夜叉却不为所动,把雨孤云推给众黑衣人,道:“把他绑结实带回山寨里,我们走。”接过黑衣人捡回的铁刀和雌雄双剑都提在手里,飞身上马,先自去了。
众黑衣人见铁刀母夜叉没有其他吩咐,图着省事,用绳子将雨孤云直接横捆在马鞍上,然后一声唿哨,风卷枯叶般痛快地走个干净。
龙月儿在老者铁钳般有力的双手里挣扎不出,哭闹不已。
老者见众黑衣人走远,才撒开手叫龙月儿自由。跪下施礼道:“小老儿冒犯公主殿下,乞请恕罪。还望公主殿下清醒心神,速回大名府调遣军队来攻打她山寨,救出侠义小哥才是上策。公主殿下以为如何?”
没了主意计较的龙月儿经这句提醒,立时恍然。抹一把脸上泪水,咬牙道:“对,我这就去带兵来,且等着——”一句没说完,泪水又落,拧着鼻子哽咽。
她自三岁多些和雨孤云在一起,朝夕相处,从不曾分开过一天,至今十几年。
此时突然离散,龙月儿只觉得不胜孤独,心里悲伤万分,如摘肝胆般难过。
从飞跑着去牵来马匹的乡民手里接过缰绳,想飞身跃上。可身体乏力,险些跌落。老者在侧见了吓得不轻,忙一把扶住。
龙月儿整敛散乱心神,重新上马。拨转着马头兜了一圈才想起问老者:“哪条路是出山的?”
老者也是慌得懵了,急忙跳上雨孤云那匹马,在前面跑着道:“我带公主殿下出山,护送公主殿下回大名府吧。”一老一小乘着夜色奔驰而去了。
这山径崎岖,一路颠簸得厉害,叫横担在马背上,脑袋向下的雨孤云好不难过。
眼见着地面的嶙峋坎坷和两边的狼牙怪石与自己的头顶似只有毫厘之差,好像随时都会撞过来一般骇人,无奈只好闭起眼睛忍挨。
铁刀母夜叉心思却精细,走出不远就回头检视,见此情景倒吓一跳。
才知只有自己在意这个男儿,别人哪肯管顾他的死活?忙叫人把雨孤云从马上解下。
但雨孤云要穴被制,气血受阻,使浑身酸软,自己一个人又骑不得马。
铁刀母夜叉为难片刻,索性把雨孤云扶上自己的鞍前,抱在怀里扬鞭去了。
众黑衣人见二当家如此,都惊得不轻。心思干净的皆猜不出其中缘由;可心思肮脏的却都明白个大概。
但素知这二当家是不容龌龊的火爆脾性,是以都在心里乱猜,没一个敢出声的。
铁刀母夜叉的怀抱虽小,却是不同寻常的温暖柔软的去处。雨孤云虽心怀侠义,可也只是个普通的男儿,正在血气方刚的年纪上,哪有圣人贤士那般坐怀不乱的德行?
靠身在风光如此旋旎的怀抱里,闻着时刻飘荡在口鼻间的馨香,只觉得似连魂魄都醉。
偶然回头,见面对的虽仍是一张冰凉的银面具,但后面那双晶莹剔透的眸子里射出的目光却如春水扬波,悄动涟漪,似含着无限的甜蜜。叫雨孤云的一颗心跳得乱七八糟,不知要临头的是福是祸,该如何应对。
进入山寨,雨孤云被抬进和马厩相邻的一座土屋里。
这里本是储藏饲料的仓库,里面满是干爽的稻草。两名黑衣人将他扔入其中,锁好门扇,拍打着双手去了。
剩雨孤云瘫软在稻草堆里,仰脸望着窗外悬浮在黑暗里一颗颗闪烁不定的星星,心里却觉得好笑。
以为人生便如一场儿闹,是生死无常,变化难测的把戏。不论福祸悲喜临到面前,自己却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只能任凭如何,尴尬着承受。
这样想着,心里坦然下来,叫疲倦袭上眼皮,慢慢昏沉。
迷迷糊糊地睡,直到明亮的阳光刺入双眼。
雨孤云睁目片刻,恍然看清敞开的门口站着一人。正是换了一袭同样白色,式样多些花哨素绣的长衣,面上戴着怪异银质面具的铁刀母夜叉。
铁刀母夜叉环抱双臂,静静地看着雨孤云。片刻后道:“你想好了吗?”
雨孤云听她这句没有来由地问,奇怪道:“想好什么?”
铁刀母夜叉道:“若想活,便嫁我为夫;若想死,我便成全你。”
那时礼教严厉,男尊女卑。门户之间若无悬殊的差距,从来都是男娶女,哪曾听说女娶男?雨孤云是心地干净的汉子,怎容得这般侮辱?被气得笑起来,道:“还请二当家成全。”
铁刀母夜叉却好似早料到雨孤云会拒绝,也不着恼。只叹一声,向门外立的两名随身女侍吩咐道:“去远些地方候我。”
然后缓步走入,在雨孤云旁边的草堆上坐下。慢慢摘下面具,用双手抹一把脸孔,抬起对向雨孤云。
雨孤云最怕看她灿如明月的容颜,只觉得被那脸儿散发出的幽幽清辉逼迫得似要不能呼吸一般的窘迫。
心里和龙月儿的美丽比较,才发现龙月儿还是没有绽放的蓓蕾形色,其中多有暗含的娇俏;而铁刀母夜叉却已是正盛开得恣意的少女妩媚,有叫人无法抵抗的魅力。
雨孤云想要埋头,可又不舍;想要端详,还觉得尴尬。
这般折磨却是让人心里发痒的挑逗,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胜利的战争。
铁刀母夜叉见得他的不自在,微笑道:“怎地怕我?”
雨孤云被她一语逼入无法反复的境地。但又不甘心,反问道:“怎知我怕你?”
铁刀母夜叉道:“若不怕我,怎地不敢看我?”
雨孤云瞥她一眼,道:“男女有别,我怎好辱没二当家的清白?”
铁刀母夜叉摇头道:“都是武林里的同道门生,怎地讲究?”
雨孤云不愿被她抢白,反语相讥道:“既然不讲究,为何还要遮掩面目,不叫人识?”
铁刀母夜叉听到这一问立时无语。埋首半晌,竟哽咽一声,道:“奴家的这份容颜虽然丑陋,却也不是谁都能见的。”
然后抬头向雨孤云道:“可若瞧过,就要娶我为妻,否则我只有一死。”
雨孤云听她说得骇人,虽觉得奇怪,却不肯信,以为她在讲欺人之语。
铁刀母夜叉见得他面上的疑惑神情,自然猜得到其心里所想。略抿双唇,叫更加红润,道:“英雄不必怀疑,且听奴家仔细道来。”
“奴家本姓花,闺字盛开,原就是大名府里的住民。我父母都是良善,凭着经营小本生意养活我和哥哥。奴家从小体弱多病,几曾奄奄。父母怕我活不下来,就把我送到离此二百多里远的净瓶山水泉庵里寄养,叫我在佛前伺候,希望能得佛祖的护佑,活得长久一些。”
讲到这里,花盛开低叹一声,敛眉道:“可谁想我倒是康健起来,父母却先后遭害离世。最恨那个老皇爷,不辨黑白是非,叫我父母短寿——”
雨孤云听她把牙齿咬得咯嘣嘣响,心里显然恨到了极处,觉得惊讶,忍不住问:“老皇爷——怎地你父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