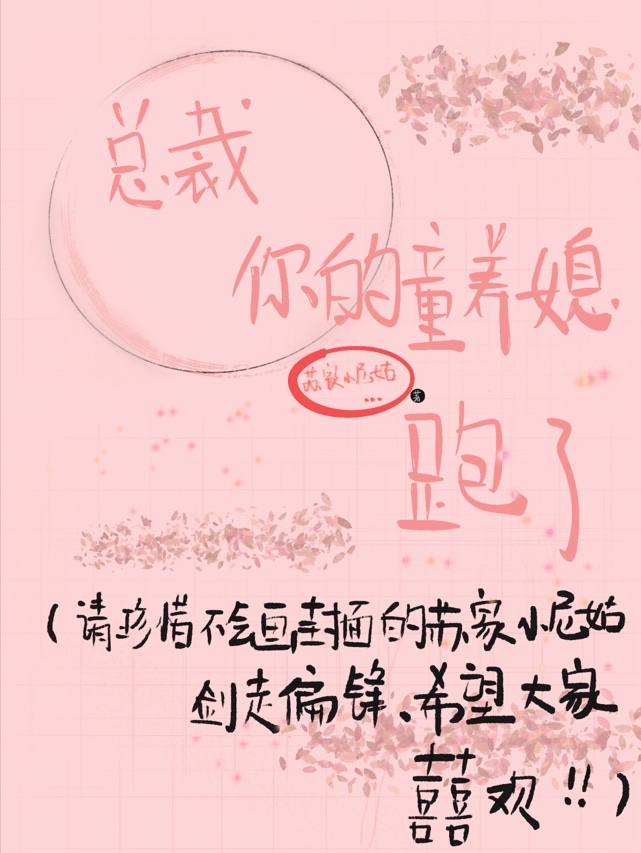雨孤云二十岁时龙月儿已经十六岁,正是桃花初绽的烂漫年纪。
少女的情思虽然浅显,却也早就有心事萦怀。再不肯如幼儿那般时刻纠缠着雨孤云不放,宁愿独自闷在绣楼里拿着涩墨的毛笔在洒金的梅花笺上把某个人的名字写过几百遍也不觉得厌;也不肯在雨孤云唤她时就答应,总要深沉着拿捏一番,直到自己忍不住时才转过脸儿来。
可每当二人面对,雨孤云就总有被龙月儿容貌的明艳逼迫得窘不可当的尴尬,常常叫他暗自奇怪,不明白当年那个连屎尿都不知拉撒的小东西怎地转眼就出落成这般可人的花儿少女?
才知造化最善耍巧,天工总能玉成,在最出其不意的地方幻化出夺目的光彩来把自己照耀。
金莲上人瞧着自己的这一双徒儿都是世间罕有的人中龙凤,自然最欢喜,总有看不够的得意。恨不能把自己擅长的都传与雨孤云和龙月儿才觉得痛快,是以督促起二人来自然严厉。
雨孤云倒能体味师父的用心良苦;可龙月儿还是懵懂的年纪,加上自幼娇惯,养成凶蛮霸道的骄傲性格,却常常挑剔师父的苛责。
好在有雨孤云在其中周旋哄慰,叫龙月儿不舍放纵自己,只恐怕伤到雨孤云的心。
金莲上人原拟以八年为限,还净人情后就回到道观潜心伺候那盏青灯,继续自己还不曾圆满的修行。
可八年已过,她却舍不得这两个徒儿,只任凭老皇爷把自己一留再留。
才知努力戒除了这多年的尘根其实还是不曾干净,总有叫自己心怀喜悦的痴妄之念在胸间泛滥,把自己打落在红尘里不能翻身。
虽然觉得牺牲了几十年的清修可惜,但只要看到两个徒儿的笑脸,就觉得一切都不枉。
这日正是初秋的早晨,天气渐凉。
龙月儿却不肯听娘的劝阻,还是新裁做了一套薄凉的衣衫,仔细地换好。叫丫鬟给自己梳一个利索的发式,用金丝抹额勒了,然后满心欢喜地奔下绣楼寻雨孤云讨夸赞。
她知师兄起得早,此时必然还在后花园的演武厅里练剑,就一路兴冲冲地奔来。
演武厅的举架高大,当中挂着一根垂地的粗绳索,本是用来比较军士攀登本领的。
此时雨孤云正把身体悬在上面,双手使剑,练一套金莲上人嫡传的功夫。
金莲上人所习武功得传自师父上清老祖,是佛家大乘功法里最纯正的一路。但也最难练习,没有十年以上的功夫无法登堂入室,得窥奥妙。
雨孤云练就的双手剑功夫却是金莲上人独习的绝技,放眼世间无人能及。
这手功夫本是女子习练的,其中多有折腰回转的轻灵变化,如风摆苇柳般,显得婀娜。雨孤云因为迁就龙月儿,学习在先,然后传授于她。
可龙月儿贪玩,用的心思远不如雨孤云深湛。加上雨孤云智慧灵巧,身体有力,把其中软弱的招数都变化得刚硬之后,舞起来倒比金莲上人还出色。叫金莲上人鼓掌叫绝,赞叹不已。
龙月儿推门进来,先就叫一声:“哥哥,看我美不美丽?”然后抬头才见师父金莲上人和爹爹老皇爷都在观武台上的大案后面端坐。忙伸下舌头,收敛起张狂,向二人恭敬见礼。可遍寻演武厅里,却不见雨孤云的身影。
正奇怪时,听头上‘哎’地传来一声喊,抬头见雨孤云从绳索的高处掉落下来,不禁惊得失声尖叫,飞身上前来救。
雨孤云这一跌却该怪龙月儿。
他只顾着看她穿一袭红粉的衣衫上用银丝遍绣的灿烂,衬得那张粉白生香的脸儿更加娇嫩照人,叫他心弦大动,魂魄沉迷。却忘了自己身处半空里,让盘着绳索的双腿失力,不慎跌下。
但这多年的下心苦练自然不是枉然,雨孤云的身手之迅疾已经远超寻常,能在电光火石般转瞬的变化之间应对自如。
忙撒手向上扔出一柄长剑,长臂抓住在身前疾速掠过的绳索,一个轻灵的翻腾,落身在龙月儿的面前。
恰巧头顶的长剑正好跟随而到。也不必看,只伸手一捉,就在掌里。然后向后背一挽,旋出一串漂亮的剑花。
龙月儿从来最喜欢看雨孤云在自己跟前这般潇洒地耍帅,还道适才之险是他有意逗弄自己。脸上逞出的表情却矛盾,半含着嗔怪的笑意半噘着嘴儿,将手轻打在雨孤云的胸上怨道:“又吓人家?怎地讨厌?”
雨孤云只笑着不语,一双眼睛从龙月儿的头顶端详到脚下,却怎样都看不够。
他两个在这里卿卿我我的一番郎情妾意如此昭彰,坐在观武台上的金莲上人如何看不出来?
她却也乐得自己这对郎才女貌、金装玉配的徒儿能够喜结鸾俦,恩爱白头,以为必是天下少有的圆满夫妻。
但想着龙月儿是出身金贵的皇亲公主,而雨孤云不过是个皇爷府里的使唤,二人的身份直如天上地下般相差悬殊,老皇爷怎肯答应?不禁转头看他。
老皇爷虽然看似昏聩,却只在应该糊涂时才如此。其实他一生戎马,在生死间游荡漂泊,最能把世态人情瞧得清楚透彻,又如何看不出女儿和雨孤云之间那点不加掩饰的猫腻?
但他以为女儿还小,如此这般也不过是春情初萌的胡乱用情罢了,不值得惊讶。等她大一些,自然会明白自己身份的尊贵,地位的显赫。也自然就会知道该喜欢怎样的人儿,攀附怎样的门庭了。是以此时只把双眼虚眯,当一切都没看见。
雨孤云收双剑在手,和龙月儿一起来在金莲上人面前执礼请教。
金莲上人微笑着点头,正想评说,听门外传来报号之声。然后见一名府役手执一封书信急急地进来,躬身道:“皇爷,有金莲上人的八百里加急传送书信到。”一边说,快步呈放到大案上。
金莲上人听了暗自奇怪。自己非官非宦,怎地要惊动驿使用这般急迫的速度送书信来?又有怎样不堪等待的事情要如此呢?见老皇爷捏在手里端详,心里不禁有些焦躁。
但此念刚起,马上暗诵道号,以为自己持心不够端正,叫执着之欲纷乱。
老皇爷只粗看封皮就已经明白大概,转手递到金莲上人的面前。
金莲上人见上面上首写着老皇爷的封号,立刻明白就是这几个字叫官家以为重要,是以用八百里加急的方式送达。看后面缀的自己名字的手体似是师兄的笔迹,不禁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抽出内瓤展开,见一块白净的素笺上红阑肃穆,只有“师父驾鹤,速归。”这几个字入目。
金莲上人怔怔地看着,却说不清心里是悲是喜。
若说悲,但道家虽然只修今生,也知活着即是受苦。为道的一世清修也为死后能得欢愉喜悦的圆满。师父终于如愿,这本是可喜之事。
可若说喜,一想起从此再看不到他慈祥光明的笑容,听不到他煦暖人心的教诲,叫自己似乎丧失了可以指望的依靠般孤独无助,心里便似嚼烂黄连般,不是个滋味。
也才知万法都可悟,唯生死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是修行到今日的自己也不堪面对的险隘。
老皇爷年纪虽苍,目光却锐利,在旁边把素笺上的内容看得明白。低叹一声,道:“上人敛悲吧。”
抬头向还在大案前立着的府役吩咐:“去为金莲上人准备行囊。另外从府库里取一千两黄金、五十双玉璧,还有丝绸锦缎各十匹,先叫人送到祁连山的上清观里,是为老祖做丧葬法事用。”府役领命去了。
老皇爷转头看向金莲上人,见她仍旧呆呆地回不过神来。
送走老皇爷和金莲上人后,龙月儿眨着目光顽皮的眸子向雨孤云道:“哥哥,你我有多久没有出去玩耍过了?”
雨孤云怎样聪明,立时明白她的意思。笑着道:“你和老皇爷说吧,我可再不敢去讨骂。去年陪你到东京汴梁城买衣饰,你差点惹出祸端,叫官府来公文询问皇爷。若不是师父遮掩,皇爷必要责怪你我。你却还不识趣,又想着出去撒野吗?”
龙月儿见雨孤云态度如此,心下不甘。忸怩着捉住他的一臂抱在怀里求道:“哥哥,只有你能叫爹爹那老昏聩——”
雨孤云听她言语不敬,忙把手臂抽回,假装恼道:“休说,当心叫人听了去。”
龙月儿也是一时失口,自知不妥,把手掩在嘴上转动眼珠四下瞧着。见各处空荡,没有人来往,笑着打了雨孤云一掌,嗔道:“又吓我?”二人一路耍闹着回到龙月儿的绣楼里。
金莲上人自在房中的蒲团上静静地坐着。
目光虽然盯在供奉的三清老祖面上不动,其实心里却如风吹苍茫,叫万尘飞起,弥漫天地。
想起师父上清老祖当年怎样在野狼口边救下被饥贫不堪的父母遗弃在祁连山上的自己;又怎样把自己从小当做一个男孩儿一点点养大。而上清观没有女院,当年还只是功德堂主事的师父又怎样力排众议,专为自己另建女院,供自己修行至今。
想起师父生前总说:“人生一世,最不堪被声名所累,是脱尘的锁链,开悟的屏障。”
是以上清老祖虽然道法精宏,参悟高深,却只肯默默无闻地帮人度化,从来不叫名号彰显。
如今提起上清观,信徒都知师兄和自己的森严道法,却不识上清老祖的金光灿烂。目下师父圆寂,有多少人会去凭吊呢?想来师父生前宁愿默默,必也不在意死后的冷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