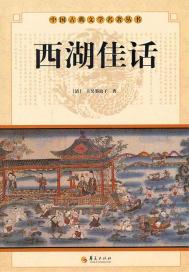老妇人将碗筷摆好后,眼看相携入房的童牛儿和银若雪吟吟而笑。
原来昨夜二老刚刚上床,不等温存成欢,却听隔壁木床吱嘎作响,银若雪叫得一声比一声尖锐,直折腾了半个多时辰还不见歇。
二老初时还笑,后来却被那叫声挑逗得情起而相拥一处,这一夜倒比以往尽兴。二老始信二人果真是夫妻。
老妇人见银若雪将手扶在腰间,低声告诫道:“你已有孕在身,夜里不要做得狠了,当心动了胎气。”
银若雪此时才知老妇昨夜所言早起腰痛是怎样滋味,羞红双颊。低头笑道:“我是不肯呵,可他——他总是不够。”
童牛儿在侧却哼一声,道:“我便够时也停不下来。谁叫着要死要活的?”
银若雪听他把自己昨夜情炽之时所叫言语说出,不禁又羞又恼。下狠打了童牛儿两拳,急道:“你——你怎地赖皮?”
童牛儿忙笑着拉住她手哄慰道:“好——好——是我要死要活的,行了吧?”老妇笑着轻叹一声,出屋去了。
童牛儿见二老又到院中饮茶,便将银若雪拉入自己怀中坐下,搂抱了夺过她手中筷子,道:“我来喂你。从今而后你再不需自己动手吃饭。”
银若雪听了这一句笑得双眼眯到欲无,她却不知这是男儿惯用的哄慰伎俩。天下女子若皆不喂不食,怕一个也活不下,都早被饿死了。
童牛儿一边喂着一边问:“还痛吗?”银若雪噘嘴道:“不动便不痛,一动便痛得厉害。”童牛儿道:“歇歇吧,过两日再去探山不迟。”银若雪笑着拍他一掌,道:“今夜你别来惹我就好。”
但童牛儿对林凤凰万分牵挂,又怎等得及?
自林凤凰被劫掠至今,童牛儿在心中自责不已。以为都怪自己疏于防范,才让方威有机可乘。数日前为救林凤凰清白,自己曾绞尽脑汁。如今倒好,不屑说她的清白,便是性命能不能保得住都难说。
凤凰天生貌美,若落入老翁所说的梁济寺花和尚之手,岂不要受尽凌辱?若真如此,她还怎活得下?每想至此,童牛儿都觉得一颗心好似掉进油锅里一般,被炸得上下翻滚,痛不可当。
他以为愈早动身寻找,林凤凰生还的希望便大一分。是以不敢耽搁,待在床上将银若雪哄睡之后,便在腰间插了利斧,肩荷扁担,向二老谎称去山中打柴。要了几张面饼背在身上,另挂一捆长绳,独自向翠屏峰上行去。
他一路走来,想着自己身边这三个女孩儿,掂量着她们在心中的份量,愈觉得有趣。
赛天仙自风尘中来,世事早已窥破,没了少年的浮浪轻狂,每日只想着操持家务,服侍自己,没有其他念头可想。平淡得似杯中白水,已没什么滋味可品。但却可活人性命,时刻不能缺少。适合为人妻子。
银若雪初通情事,万念皆新,心中所想虽都是云里雾里的,但却有趣。只是需时时哄慰,堪惹人烦。若说滋味,倒如瓶中蜜水,虽然甘甜,却不可多饮,多饮只怕要腻。她虽有朝一日也会淡如白水,但那一天太过遥远,自己怕等不及,只在此时做个家外之家最好。
而林凤凰璨如天上星斗,虽曾近在咫尺,却总觉得遥不可及。唉,她是太过完美,只适合做自己梦中所想的那个便好。但偏偏是她最让自己忧烦牵挂,魂梦相随。只要是为她,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了无遗憾。
午间坐在森林的树墩上吃干粮时,见两个猎户背挂弓箭,手提山鸡野兔走过。童牛儿忙拦住打听路径。
二人听他说要去梁济寺,皆吃了一惊。稍长那人打趣道:“去那里作甚?当和尚吗?”
童牛儿早想好应对之词,苦下脸来,拉长声音道:“二位大叔不知,我那过门才几天的媳妇前儿个被一群和尚趁夜劫掠去了,至今杳无音讯。人都说怕是梁济寺中僧人所为,我想着去问问看,若真是好讨要回来。”
二人对他所言立时便信以为真,另一人急道:“傻兄弟,若落入他们手中,还讨得回来吗?怕只能收回一具尸首吧?还是回家另寻一个的好。”
童牛儿却扭了身子抹泪道:“我俩个自小在一起长大——我——我只要这个——”二人听了都神色黯然。
稍长那人叹一口气,道:“你若去寻,定要找那庙中当家的主持通明大师。如能求得他心软,或可有一线希望,至少能保你性命无恙。”
童牛儿点头应下,心中已生暗恨,想到:看来这梁济寺中的僧人确是恶类,已在此地为患。今日被我遇着,定要想办法铲除掉他们。
另一人也叮嘱他几句,并将身上所剩干粮解下给他,道:“此地离梁济寺尚有一天多的路程,留着吃吧。”童牛儿见皆是肉脯,暗暗欢喜,执礼相谢。
二人走出不远,稍长那人又返身回来,拉了童牛儿道:“你这孩儿也真命苦,还这般痴心。唉,倒是难得。我告诉你个法子,你看。”手指剑阁道:“那里面住着一群人,其中有个叫翁九和的,人称飞天神龙,是个讲理的人。你且去求求他看,他若肯帮你,你媳妇或许还能回来个完整的尸首,别抱好念头。”在童牛儿的肩头拍拍,转身去了。
直走到夕阳落山,也没有望见梁济寺的山墙。
这山路虽不甚陡峭,但曲折迂回,如羊肠盘绕,却也累人。童牛儿看天色近晚,无奈只得选个背风的草窠,扯些干草铺垫在身下。就着肉脯吃过大饼,然后和衣而卧。
想着这一夜不见自己回转,银若雪必要牵挂,心中甚觉不忍。但念头刚起,困意袭来,便朦胧睡去。
可连梦还不及做,已听到一片喧哗之声在耳边响起。睁眼迷糊片刻,立身寻找,才见距自己数丈远的小路上正行来一群人,约十五、六个,手中都举着火把,火光照耀下可见当头的正是个和尚。
那和尚头颅甚大,青色脑皮反映着火光,隐约可见上面颗颗黑淤的戒痕。后面跟随的都是青壮男子,衣饰不同,走得也慢。众人在说着什么,正到热闹的地方。童牛儿侧耳细听,不过几句,已大致明白,原来他们是要投到梁济寺去当和尚入伙的。
童牛儿心中一动,忙自草窠中窜出,手脚轻悄地在后相随,偷听众人言语。片刻后已知这些人来自不同地方,相互皆不熟识。胆子愈大,一点点向前面靠拢。待走出七、八里后,已紧跟在那领头和尚的后面。
童牛儿已知和尚法号觉能,到这梁济寺入伙也不过半年左右,原是厨下的火头师傅。说话颠三倒四,只是个混吃摸喝的小角色,也不看在眼里,和众人一起拿话逗他。
这和尚却傻,生怕大伙将他小瞧,亟不可待地将所知事情和盘托出,一一道来。童牛儿才知梁济寺中僧人所为之恶竟比自己相像还要猖獗,几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心里恨得愈加地狠。向觉能道:“你们杀这多人,官府不管吗?”
觉能哈哈大笑,道:“小老弟,官老爷只要拿到银子,他怎舍得管你?把你管死,谁去孝敬他?岂不是自断财路?从来官匪皆是一家,官要护匪,匪要养官,千古如此呵。”
这和尚本是痴愚之人,不懂什么道理。这般言语原是听来的,今日正好学舌卖弄一番,深觉得意,却不想他几句话已把这县治中的大小官员皆都卖了。
童牛儿自小在市井间混迹,对官匪互养,共通为患这类事并不觉得稀奇。只是猖獗到如此程度,用如此血腥手段敛财却少见,甚觉吃惊。向觉能道:“那一村子的人都杀光了?”
觉能将手一摆,道:“不屑说人,便是鸡鸭都不剩个活的。你道都怎样了?都被我们煮着吃掉了。哈——”他自觉这一语说得有味,先就大笑起来。
跟随众人多数是良家子弟,不曾做过恶事,心肠没他狠毒,倒都笑不出。童牛儿装傻追问道:“大师不是出家人吗?怎地还吃鸡鸭?”
觉能将嘴一撇,道:“什么出家人?天底下哪有真正的出家人?不过是用来骗人的掩护罢了,你倒当真?”
童牛儿又问:“抢了多少金银?”觉能道:“穷乡僻壤之地,能有多少?拢共不过几十两罢了。”童牛儿皱眉道:“只这点金银又何苦要杀那么多人?”后面跟随众人也有同感,皆作此问。
觉能扭脸愠道:“杀便杀了,哪有什么道理?大爷我杀人只图个痛快而已。”童牛儿暗自咬牙,恨不能抽出腰间的斧子立地便将他劈成两半,以消胸间忿气。后面跟随众人虽多数默默不语,却也有几个拍手叫好附和。
童牛儿又问道:“我们若参与其中,一次可分多少金银?”觉能道:“我们这里最公平不过,你抢掠得多,分的便多;抢掠的少,分的便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