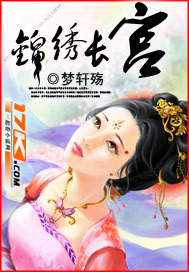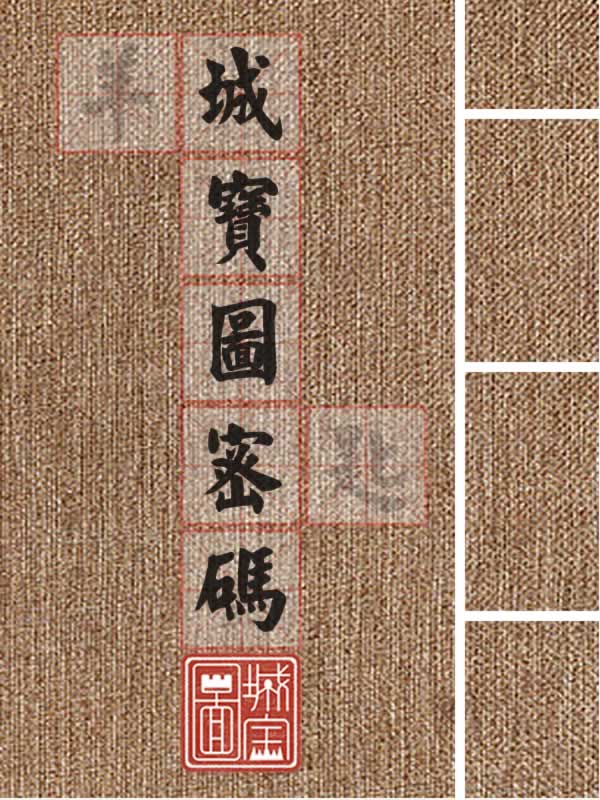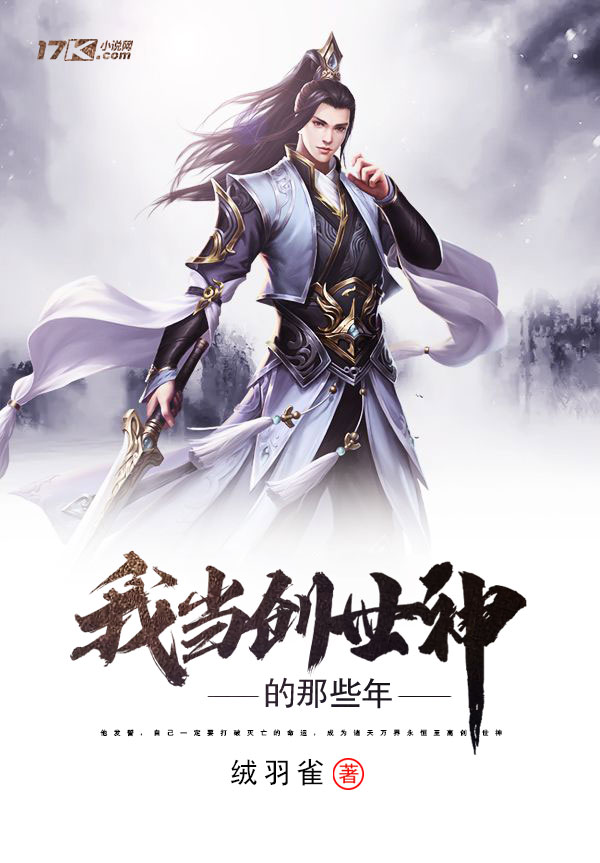第五节 孟家上学读书受教育情况
我家虽然是中国儒学大师孟子的后代,也不知从那代远祖时就离开书香门第,改作工匠手艺了。但是思想信仰上还是传统的儒家思想。
我们三大户孟家的几代人中,没有吃斋念佛的,也没有信“洋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供祖宗不供菩萨,逢年过节,给“祖宗牌位”烧香上供,上坟烧纸,不到庙里烧香拜佛。他们以忠孝节义为道德标准,既不是有神论者,又不是无神论者。他们对生命的看法是:“人死如灯灭”,也就是说人的肉体如过去油灯的“灯碗”,性命如“灯油”,灯油耗尽了灯就熄灭了,只剩下空碗。人的性命精力耗尽了,人就死了,只剩下肉身。对神鬼的看法是:“信则有,不信则无”,鬼神存在于人们的心里,而不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上。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神敬善人,鬼怕恶人”等民间格言。这种朴实又有些愚昧的世界观,也是旧中国众多老百姓精神状况。
对于文化学习,从我们孟氏家族来说也是比较重视的,是希望让自家的孩子读书成才的。但是,过去的读书的目的和现在是不同的。
过去的中国是小农经济社会,广大农民是没有文化不认识字的,因为当时从事农业生产也不需要读书识字。那时上学读书就是为了脱离农业生产,优秀者通过县内考试,取得县政府授予的“秀才”学位,类似现在的初中毕业生。“秀才”中的更优秀者通过省里的考试,取得省政府授予的“举人”学位,类似现在的高中毕业生。“举人”中最优秀者通过中央政府的考试,取得国家授予的“进士”学位,类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取得“进士”学位后,国家就给安排工作,成为“朝廷命官”了。如果再能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就等于是有工资的“研究生”了。如果再能进入翰林院,那就等于进入科学院当研究员了,若能获得“大学士”的官职,就等于是“院士”头衔了。而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等于是优中选优再选优,经过几次淘汰,进入最后一关是非常困难的。当朝廷缺少官员时,有的举人也可能被“提前录用”安排工作,而秀才是不能成为朝廷命官的。有些举人和秀才,也可以从事官府雇佣的“书吏”、“师爷”一类的事务性工作,俗称“做事的”,但在社会地位上属于临时工。有的秀才成为富豪家庭雇佣的管家、账房先生或教书先生,也有的成了乡村的私塾老师。还有举人和秀才,不甘心落榜,一次一次的总去“应试”,结果一事无成穷困潦倒,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激烈竞争的考试文化中,老百姓中多数人对“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是望而却步的,他们觉得与其供子女上学成为“孔乙己”式的人物,还不如直接就让子女当“闰土”式的农民。所以,先把小孩子送到私塾或学校念点书,检验一下孩子的智商,一看学习成绩平常,不可能成为学习尖子,也就不再供他们上学了。这些孩子自幼受到家长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学校学习成绩一般,不能名列前茅,自己也就没有进入仕途的信心了,也就自认天生不是靠耍笔杆子吃饭的材料,认命干庄稼活了。
听老人们讲,在清朝时农村没有学堂,只有私塾。而且也不是村村都有,许多世代务农的家庭,没有让孩子读书写字的要求,教书先生也就没有更多的市场。那时国家没有普及教育一说,私塾老师的工资,是学生家“摊”的,给钱给粮食都可以。富裕人家多给些,穷苦人家少给些。平时吃饭也是各家轮流吃,住宿就在学校里。一个村十几家、或者二三十家供养着一个老师,问题也不大。而且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灵活,因人施教。没有明确的学期和年级区分,老师对学生只有作业没有考试,当然这些因人而布置的作业也等同于单独考试。农民家的孩子,可以在冬季或农闲时去念书,农忙时就下来在家干活。所以穷人家的小孩子,一般是男孩子都可以上一两年私塾,学一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之类的初级文学知识,和背诵小六九、打珠算、丈量土地一类的数学知识,大概属于启蒙教育吧。再往上学什么四书五经之类的高深知识,准备考秀才、中举人的就少了,考进士中状元等就更不敢想了。一来是家里穷,只要能劳动了,就要去干活,没空念书。再有也是多数人智商低,高深知识学不进去,虽然私塾先生因人施教,但是如果完不成老师布置的背书、释义、写大字(毛笔字)、做文章的任务,也是要打板子(用戒尺打手掌)的。小孩子常由于不会背书怕挨打,也就不愿意再上学了。家长一见自家的孩子常挨打,就知道孩子不是读书的“材料”,走不通“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之路,也就不再花费钱粮供孩子继续上私塾读书了。
当然,过去也有穷家的孩子智商高,小时候半农半读,成人后白天务农,晚上读书,靠学习成材的。据说中国古代社会,为了鼓励穷人家的孩子读书成才,也是有国家“助学金”的。穷人家的孩子考中“秀才”,就可以到县办的书院去读书,准备日后考取“举人”。穷秀才去书院读书了,家里没人种地了,县衙门每月给几两银子的生活补贴,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养家糊口。穷秀才考上“举人”后,到省里的书院去读书,国家给的助学金更多了,同时也可以得到一些乡绅的赞助。如历史上的朱买臣、吕蒙正和戏曲里的陈世美等人,都是穷人家出身的。当然,穷人家的孩子想读书成才,除了天资聪明之外,还要有“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等刻苦学习的精神。所以,古代社会那种穷家出身通过读书当官的人,是非常罕见的。
辛亥革命后,虽然有“拆了大庙改学堂”的举动,但那时国家办的小学校是很少的,还没有中学。经过“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以后,私塾也少了。那时的老师是国家发工资的,学校是要收学费的,而且除去寒暑假、礼拜天、都要按时到校上课的。所以,穷人家的孩子还是去不了“学堂”读不起书的。
据《蓟县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蓟县就把过去的渔阳书院改建成“两等小学堂”,设文学、数学、地理、历史和体操等课程。辛亥革命后,城里又陆续建立了兴隆庵、龙泉庵、白塔寺等初等小学,1928年城内的“两等小学”改称“县立第一完全小学”。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蓟县的国办小学越来越多了。在日伪时期的1941年10月,蓟县城里在“渔阳书院”旧址(现在的“蓟县一中”校区内),建立了“蓟县初级中学”,每年招一个初中班,学生42人。到1945年,招收四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也就是原来的初中三年级班升为高中一年级班,等于有了一个高中班。日本投降后,蓟县被共产党接管,1946年国民党占领蓟县城区后,蓟县中学撤离蓟县城,与玉田县、平谷县的中学合并为“联合中学”,进行打游击式的流动教学。1949年1月,平津战役后,联中分开,各自回到本县。蓟县中学回到县城旧址,改称“河北省立蓟县中学”,但只是有初中班,没有高中班。
解放后,国家号召男女儿童都要上学读书,而且学费也不多(我读小学时每学期一元钱学费),穷人的孩子也念的起书了,但是在本县只能念到初中毕业。解放初期,蓟县的初中毕业生还要到通县陆河中学去读高中(当时蓟县隶属河北省“通州专区”管辖,后来通州划归北京市管辖,蓟县改归河北省“天津专区”——后改称“廊坊专区”管辖)。
1955年“蓟县一中”才设立高中班,以后初中毕业生就在本县读高中了。
到1966年时,蓟县的学校分布情况是:一般的村里有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乡(后改为公社,全县38个公社)里有高级小学(五六年级),区里有初级中学(区后改为工委,那时全县分八个工委,只有城关工委片有“蓟县一中”和“敦庄子中学”两所初中学校,其他工委片各有一所初中学校),县里有两所高中(“蓟县一中”和“上仓中学”),一所中专(“杨津庄水电班”,不是国家办的,不包分配,类似现在的培训班)。天津专区(蓟县那时属河北省天津地区专员公署管辖)有廊坊师专(大专)、廊坊农机化学校(中专)、杨柳青卫生学校(中专)、杨村师范学校和蓟县师范学校(中专)。那时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省办或者国家办的大学。不是特优秀的小学生,很难经过层层筛选,考进更高级学校的。我和堂弟孟凡荣读小学时,蓟县已经达到普及初级小学的程度,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报名上学。但是能考上高级小学的也就一半左右。到高小毕业升初中时,又要淘汰一大半,到考高中时淘汰的就更多了。1962年我考上初中一年级时,全班50个学生,后来通过留级降班,及有的升学无望的学生中途退学,到1965年我初中毕业时,全班还剩38个学生。我们这38个参加中考的学生中,只有八个人考上高中,三个人考上中专,一个人被选调上了海军学校。从我们西南隅和南关联合小学1960年毕业的三十多个同学来看,只有陈德光我们两个人初中毕业后升学了,通过上学由学校代表国家为学生分配工作的则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全部被分批淘汰出局了。
从我们老孟家到蓟州后的情况看,“继”字辈的老哥仨在山东老家时念过私塾,能写字绘画,略有些文化,这也是作油漆彩绘工匠的工作需要。来到蓟州落脚谋生后,“广”字辈的和“昭”字辈的也念过私塾,有些文化,会写会算。当然,绘画和裱糊的手艺是祖传的,不是从私塾先生那里学的。
但是辛亥革命后,到了孟昭信的儿子这代,就供不起孩子全去学校念书了。因为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废除科举考试之后,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的,灵活办学,可以临时就读的私塾没有了,县城里的新式学校少,招收学生不多,收的学费较高,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上不起学。二来是新式学校上学很正规,上学的孩子只能专心上学,除了星期天、寒暑假之外,不能随便旷课。穷人家的孩子想农忙季节在家里干活,冬闲时候去念书的习惯行不通了。再有就是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传统的佛教、道教等寺院香火减少,无力维修寺庙雕梁画柱的油漆彩绘,孟家祖传的手艺无处施展,孟昭信改行了,开始置买土地维持生计,儿孙们都是种地的农民了。而农民种地对读书识字也没有迫切要求,所以,孟宪成(1909年出生)和孟宪增(1914年出生)都没读过书,十多岁就开始跟着大人下地干活。
1928年后,蓟县城里的小学校多了,城内的四个“隅”都建了小学校,收的学费也低一些了,招收的学生也多了。这时孟昭信的三子孟宪奎(1920年出生)和次女孟宪春(1925年出生)就在白塔寺初级小学上学了。孟昭信的孙子孟庆云(1925年出生)、孟庆华(1928年出生)、孟庆余(1933年出生)、孟庆宇(1938年出生),都在白塔寺小学念过几年书。这几个人中,只有孟宪奎学习成绩好,在蓟县城里读完高等小学,1935年又去北京读中学。孟庆云、孟庆华和孟庆余都是只念二三年,没到小学毕业就退学了。孟庆雨在白塔寺小学毕业后,没有考上高小才在家务农。
孟庆云等三兄弟未能小学毕业就不念了,按照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天资不足,没有读书成才的信心。1928年后,孟昭信让自己的儿子孟宪奎、女儿孟宪春以及孙子孟庆云、孟庆华都去白塔寺小学上学,也是希望他们通过学习出人头地的,可惜女儿和孙子的学习成绩一般,看不到发展前途,才没有供他们到小学毕业。他们自己也是对学习没有信心了,才中途退学的。
二是家庭困难造成的,由于家里缺少男劳力,孟庆云、孟庆华、孟庆余都是很小就跟着大人干农活,对读书没有多大兴趣,所以才只念二三年就不上学了。
孟庆云和孟庆华自幼丧父,虽说在大家庭中,与母亲一起和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共同生活,但家境并不富裕,当然要帮着大人干些农活了。
孟庆余十三四岁失去母爱,父亲给人打工或下地干活,需要他在家做饭和照料弟弟,自然也就没有心思读书了。
孟庆宇是在1946年后才上学的,能读到小学毕业,是由于赶上好年代。可惜孟庆宇也缺少学习文化的天资,初级小学毕业后,没有考上高级小学。这也符合多数农家子弟的正常情况,因为天资聪明的学习尖子,成绩优秀出类拔萃的学生毕竟是很稀少的。
1948年之前,蓟县的国办小学虽说越来越多,但也不是每个村都有,乡下的许多小村里没有学校,农村里许多穷家的孩子都不能上学。像孟庆云孟庆华居住乡下的岳父、妻兄们都是因本村没有学校而没上过学的文盲,女孩子更不能上学读书了。
解放前蓟县许多老百姓家的姑娘、媳妇们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那时城里虽然上学方便,许多家庭也不让女孩子上学读书。因为那时期女人很少参加社会工作,绝大多数都是家庭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而家务劳动也是不需要读书识字的。那时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针线活,俗称“女功”,同时还要学习洗衣做饭,这才是女孩子的“真本事”。女孩子十五六岁或十七八岁就要出嫁,到婆家如果不会做针线活,洗不干净衣服,做不好饭菜,是要被婆家和邻居们看不起的。至于你有没有文化,认识不认识字,则是无关紧要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老百姓家里的女孩子上学读书的就很少了。我母亲、二婶、姑姑都没有上过学。
总的看,在解放前,我们从山东老家迁徙到蓟县城内西南隅的三大家五代人中,只有孟昭信家的孟宪奎一个人在1935年考到北京上中学了,而且在参加抗战后,在军队中也成为军官,遗憾的是为国捐躯了,家里没有受益。孟昭瑞和孟昭凤两大家在解放前出生的儿孙中,连上高小读书的都没有,更没有通过上学读书的途径而脱离农村的,都是西南村的农民。
总的看那时期蓟县的文化人很少,如果能够有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就可以在县城里找到一份脑力或半脑力劳动的工作,成为“做事的”职员了。当然,在战争或政治动乱年代,也有些没有文化的人通过参加战争或政治活动而当官的,可这是一种特殊现象,和通常的依照文化水平高低,进行社会分工择业是两码事。
解放前,我们老孟家的这种读书受教育的文化状况,正是中国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