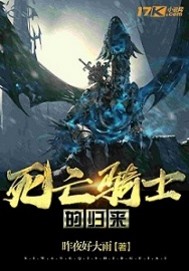上官芊打开冰箱,从过期七天的吐司里取出一片,重新数了一遍,还剩四片,默默将这个数字记在脑中。
吐司用餐刀一分为二放在盘子中,微波炉30秒打热摆上餐桌,取下榨菜口袋的架子倒出几粒,清点后是五粒,用手指将一粒小的拈回口袋,剩下四粒放在半片吐司上,盖上另外半片,几乎是本能的一口咬下,生命延续的味道。
餐后收拾垃圾,虽然离上一次清理已有十天,依然没有多少需要丢掉的东西——两张正反面都写满字的纸、擤过鼻涕的四个卫生纸团、一个空VC药片瓶、一个吃光的喜糖小纸盒。
放下喜糖盒后上官芊拿起桌子上的喜帖:送呈 上官芊 谨定于公历二零一九年二月二日(农历戊戌年腊月廿八)为新郎:吴东 新娘:杜韵举行结婚典礼,敬备喜宴恭请您及家人光临。席设:紫罗兰大酒店(滨江区望江路66号) 时间:中文十二时零八分 敬邀。
停留的时间比正常阅读稍长一点,最后还是轻轻丢进了装垃圾的小袋。
出门将垃圾袋放进垃圾桶后,回身的上官芊忽然被巨大的不安攫住了。
一楼自己的房门前,楼梯口下面,油布干瘪地躺在地上。
上官芊冲上前去一把掀开油布,没有奇迹,那个,那个不见了!
“纸板,模型级的,木头,铁丝,绒布……”上官芊换了一只手握电话,在膝盖上擦干手心的汗水。
“就是个普通模型吧,还是自制的,你直接说价值吧。”电话那头打断道。
“价值?……根本无价!”上官芊咆哮道。
“吼什么吼,让保安帮忙找找,不到立案条件。”警察挂断了电话。
上官芊将头埋进膝盖很长时间后,眼泪开始慢慢流下。
河边破烂的篮球场上,四个痞子用脚踢着一只猪,每蹬一脚“猪”便往前滑行几米,突然从“猪背”里站起来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噗”地一声吐掉嘴里的烟头。
“无聊,我走了。”外面站得最近、鼻梁上架着小圆太子墨镜的一人用脚踩停模型猪。
“刘果,不要动。”穿橘黄色外套的一人往后退了几步,开始朝猪屁股助跑。
“你妈的。”见来者不善,猪肚子里的年轻人忙蹲了回去。
一道黑影从旁窜出,挡住模型猪前面,生生受了这记飞腿。
橘黄外套在收腿和耍帅间选择了后者,全力出脚后冒着摔倒的危险在半空旋转了半圈站定。
上官芊捧着肚子上的球鞋印,背靠在猪身上慢慢滑倒。
“你……他妈谁啊?”
气势汹汹的四人围了上来,猪肚里的刘果爬出来后,愕然望着地上五官抽搐的上官芊。
“为什么……”上官芊伸出食指,因为痛到岔气说不下去。
橘黄外套蹲下来给了他一个耳光:“你谁啊?谁让你撞我脚的?”
“就是啊,你这么一撞他的脚都断了,该怎么赔偿想好没有?”太子镜附和道。
“我们讲道理,就当意外,赔个一两千块也就是了。”
痞子们轰然大笑。
“……芊哥?”最后凑近的刘果看清后,拎着上官芊的衣领拉他坐了起来:“我在你门口找到的这个,不会真的是你的吧?”
“是…是,你是?”
“我啊,刘果啊,你三楼的。”
“刘果?”上官芊睁大眼睛,脸色苍白的点点头。
“算了算了,误会,是我邻居。”刘果朝同伴摆摆手。
橘黄外套往地上啐了一口痰,慢慢起身;太子镜突然开口:“邻居?邻居又怎么样?”
“算了伟哥,是老实人,从小就是好学生,小时候我妈常常还拿他教育我。”
“从小好学生,长大家里蹲?”太子镜待众人笑过,突然指着朝这边跑来的胖子说:“我说是这货的。”
胖子拼命挥动双肘,上半身作出竭力奔跑的姿态,下肢却完全跟不上节奏,痞子们顺着太子镜的手指看到这幕,发出近似猴子吃到辣椒的怪笑。
“一二一,一二一。”一人好事指挥道。
停下来的巴浦洛夫双手撑住大腿拼命喘气,太子镜径直一把扭住了他的耳朵,巴浦洛夫大叫一声双脚踮起。
“还有帮凶,坐实了。”
“不要动他!”上官芊大声喊道。
“你说什么?”太子镜扭过头:“家里蹲大哥,叫人听话是要花钱的。”
“算了……伟哥,何必……”刘果朝太子镜走近一步,看着墨镜上面凶悍的眼神欲言又止。
“你晓得,我最讨厌听人下命令了。”太子镜举起右手,狠狠一巴掌将巴浦洛夫扇向刘果,刘果躲开摔倒在地的巴浦洛夫,噤若寒蝉地侧开脸。
“现在谈谈吧,明抢可不行,这么好的模型,我们五个人做了几个月,你们打算花多少钱买?”
“这是我的模型……”上官芊一字一顿道。
太子镜笑了,慢慢朝上官芊走去。
突然山坡上响起震耳的引擎声,一辆黑色川崎从40度的斜坡上加速冲下,落到平地依然没有减速,直冲向众人。
除了太子镜外的所有人惊呼着散开,摩托“吱”地一声急刹,停在和太子镜四目相对的位置。
太子镜举起粗壮的右臂,摩托车上的人没有动,墨镜“砰”的一声粉碎,伟哥像是中弹般僵直地前扑倒地。
“就这个玩意?”獾指了指上官芊背后。
上官芊艰难站起来,抱住猪臀。
巴浦洛夫不无沮丧地揉着青肿的左脸。
“你们慢慢弄吧。”
“喂。”
“我先走了。”
“喂!”
獾转向发出声音的橘黄外套。
“打了人就想走……”橘黄外套伸手摸向腰间:“你谁啊?”
“我叫程欢。”
“程欢……”橘黄外套凝视着对方,突然停住手里的动作:“‘十二黄道’?”
“那个,早就解散了。”
“是…是,我们不知道……对不起!我们马上走!”
“喂。”
橘黄外套感到后脊一阵凉意。
“把这个带走。”獾指了指昏迷在地的伟哥。
站在二十多米高的堤岸上望去,脚下篮球场上的两人细如蚂蚁,其中一只拖着肉虫般的猎物,步履蹒跚。
“那,还好吧?”
“没事,有个轮子有点变形,我有备用的。”上官芊痛哼一声,答非所问地说。
“你说模型,我以为起码是价值上万的藏品级手办。”
上官芊不置可否地扯了扯绳子,轮子滚在坑洼的地面上嗤嗤作响。
“当然,这个做工也很……不错。”巴浦洛夫望了一眼硅胶做的猪头,违心道。
上官芊点点头,脸色稍微缓和说:“谢谢,谢谢你们,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找回来。”
“很简单,整合小区和联通公司的城市监控,目标分析程序是现成的,因为不是专为你这项委托编的,所以这个不单收费。”
“我该付你们多少钱?”
“标的物价值可以忽略——抱歉没有冒犯的意思,本来应该按四类事件的基础价收费,但是你也看见了,中途出现了暴力事件,可能要上升为三类——两千块,新春8折活动折算一千六百块吧。”
“你说多少?”上官芊停住脚步。
“一千……六百块。”
“一千六百块?!这么……这么……贵?”上官芊慌乱地搓起手来。
巴浦洛夫面色讪红,比对方更加尴尬的样子。
“可是我只有六百块了,连卡上的。”
“这个,就算四类委托的起步价也是……八百块。”
上官芊眼神突然一亮:“明天!等明天庆典过后,我有一千二百块的酬劳,就够了!”
“好,那就好。”巴浦洛夫如释重负地叹道。
两人一猪在稍微缓和的尴尬气氛中继续向梯步的方向走去。
“巴……”
“巴浦洛夫。”走在前面的巴浦洛夫回头。
“对不起,巴浦洛夫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没用……指的哪方面?”巴浦洛夫犹豫一下,斟酌问道。
“因为大学期间就开始加入了猪协,没有去找能赚钱的工作,一时冲动两年前就和家里断绝了关系,”上官芊苦笑道:“虽然留了套旧房给我,但是父母已经不认我这个儿子了,现在全身上下只有几百块,没有女朋友,工作以外连朋友都没有……”
“等等,您说的什么协?”
“猪协,猪科动物权益保障协会。我是橙市分协的副**,不过连**也不过三个人……”
“猪科……冒昧问一句,那您不吃猪肉的吗?”
“那当然。”
“其他肉类呢?”
“要的,只是牛肉更贵,实际上也吃不起。”
“这个……是有宗教上的缘故?”
“当然没有,怎么能和宗教混为一谈?”上官芊正色道。
“那您在这个协会,具体从事什么工作?”
“倒也不是很多,主要是每月向CSAPA写信反映情况、争取资金之类,还有向本地生猪养殖场提供义务服务,有时不定期也组织募捐,还有一些抗议活动,主要是针对屠宰场……”
“动物保护协会,还有屠宰场,有反馈吗?”
“CSAPA从来没有回过信,但是城南屠宰场的主任接见过我,我代表协会递交了安乐死方案。”
“安乐死不也是死吗?”
“哪有那么简单!”上官芊有点激动地抹了一把头发:“我们当然希望马上停止杀戮行为,可是要对抗的是几千年的传统,那么大的风车,像堂吉诃德那样冲上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明白了,你们很了不起。”巴浦洛夫肃然起敬地点头。
上官芊认真观察巴浦洛夫的表情,确认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后语带感激道:“谢谢你,你是为数不多没有问我动机的人。”
“动机?不就是觉得需要去做吗?”
“谢谢,你是一个好人。你肯定也不吃猪肉吧?”
“这个……我……”巴浦洛夫结舌,所幸来到了梯步前,见上官芊吃力的想举起模型,忙伸手帮忙抬起猪头。
“对了,你刚才说庆典是什么?”
“猪之节,每年2月2日。”
“据我所知,法国特莱苏巴西镇好像有这么个节日,不过是在7月。”
“确实是仿照法国来的,多数流程也差不多,但是有个问题,Trie Sur Baise和橙市的庆典都是以分食烤猪作为结束,我们会在这个环节之前提前退场以示抗议。”
“不参加不就得了。”
“求同存异、包容——这是猪科动物的美德。”
“那你们主要做什么?”
“去年我是猪叫比赛的季军,所以今年得到了参加猪车游行的荣誉,而且就是排第三位,巴浦洛夫老师,你还有獾老师,明天请一定莅临好吗?我也好当面把酬劳给你。”
望着上官芊不掺杂质的热烈目光,巴浦洛夫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为什么我也要来?”堤坝上懒得下车的獾拔出香烟吐气:“还有,明明就是在这个烂球场,你们昨天为什么又要把那只猪搬回去?”
“演员不能在观众之前出场——原话。”背对獾的巴浦洛夫举起手机,朝堤岸下五颜六色的嘉年华大棚拍照。
组织混乱的庆典差不多半个小时后才进入正题的游行,上官芊的模型猪果然排在佩奇和波鲁克?罗森之后,只不过不论色彩和尺寸都远逊于前面两位,站在高处望去颇为寒酸。
“咦,还能边吐舌头边摇尾巴那,在里面一定忙死了。”借助手机镜头当望远镜的巴浦洛夫赞道。
“我能走了吗?”獾生无可恋道。
又差不多半小时,游行散去,人群开始往大棚下聚集。
一个黑瘦的身影快步从梯步跑了上来。
“巴浦洛夫老师!獾老师!你们什么时候到的?”上官芊跑到两人面前,滑稽的额发被汗水紧紧粘在额头上。
“一直都在,Byebye了。”獾开车离去。
“那个……没关系?”巴浦洛夫指了指下面被小孩子们盘据的模型猪。
上官芊回头看了一眼,露出慰然的笑容长叹一口气:“没关系了,都结束了,一年的准备、新年、二十八岁的日子都结束了,今天还是我最好的朋友结婚——曾经的,没钱随份子也就不好意思去了。”
巴浦洛夫望着对方眼眶湿润的笑容,不知说什么才好。
“不过总算没有辜负这一年的付出,你们在上面都看到没有,表现还可以是不是?”
这有什么表现可言——巴浦洛夫深以为然地连连点头。
“那就好了,”上官芊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泪)水,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有家赞助商临时退场,说是比去年少了一些——正好火腿肠厂的钱我也不想要,可能只有一千,麻烦你和我去ATM上取剩下的。”
信封里只有八张钞票,上官芊涨红了脸开始数第二遍。
“不用给了。”
“不需要你们同情。”上官芊垂下手,紧攥手里的信封。
“不是同情。不伤害别人,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这种行为应该支持——这是阿欢的交待。”
“什么意思?”
“唔,这样说吧,不是免单,代表蜜獾事务所向你们协会的捐赠。”
“谢……谢谢!”热泪盈眶的上官芊鞠躬道:“马上,我马上回去给你们开收据。”
“不必了,上官先生,再见了!”巴浦洛夫挥挥手转身,却发现没有獾的摩托车那样适合耍帅的交通工具,只得将手叉进衣兜。
河边有人点燃了烟火,爆破声掩盖了上官芊再次道谢的声音。
巴浦洛夫斜睨一眼光芒黯淡的烟花,当然不可能出现昂贵的日景烟花——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