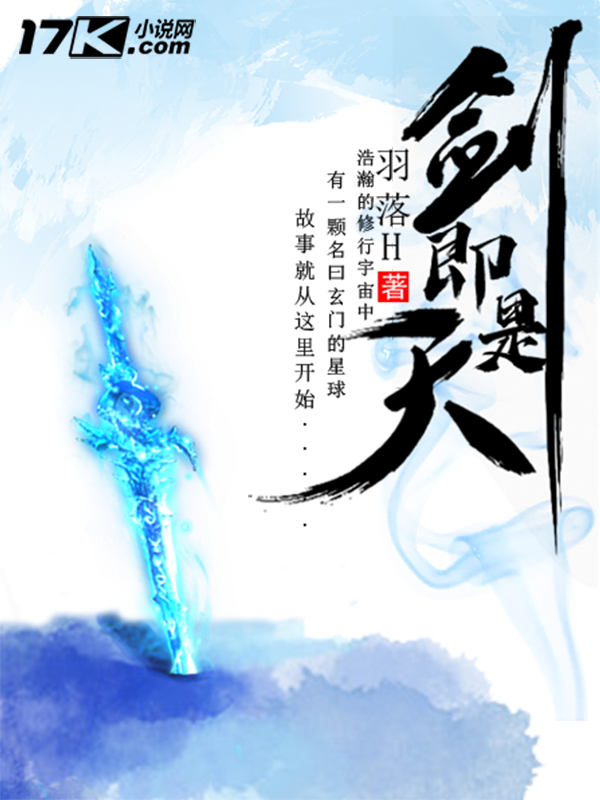欲坠的阳将余晖抛洒大地,那昏黄的光好似饱含世人垂暮的长吟。
咯吱。
那般刺耳之声迎合那般轻缓的心跳再次作响。
老人将那扇古朴的好似一阵风就能洞开的木门轻轻合上,抚须低吟:
“妥妥一壶酒钱。”
他满意的笑笑,弓着背将倚靠在门槛旁的背篓顺势揽到肩上,又拾起脚边锈迹斑驳的柴刀,迎着残阳,影子渐渐拉长。
老人名白,字长溪,是樵夫,也是一位受孩子簇拥的说书先生。
若恰逢赶集,孩童则拉伴结伙将他团团围住,吵着嚷着要听他讲述县城外的故事,他们狐疑好奇并乐此不疲。
老人的小屋坐落于江郦郡县城外二十余里处,依山而建,门前有小溪横流。
傍水西行,约七里处,可见一山。山有奇树,高二十丈有余,合抱足三人矣。形如凡木,遇水见长。
夜幕已近。
那孤长高昂的小调萦绕山岗袅袅不绝,其间砍伐倒折之声长长短短自成曲谱。
老人将背篓放于高石,于低处与其相互贴合。
倏的,一声短浅的闷呵自他的身体倾泄而出,好似生命自垂暮的不甘,于岁月催人年迈的不满。
时值七月,烈日烘烤过的大地,不见得半点雨水。下山的路不再泥泞,干燥的发裂,较之老人脚掌的沟壑也不遑多让。
老人没有似以往那般原路返还,他要去履行独属于他们的十年之约,就在那座小城里,和年少时爱慕的她,在这初七之日。
云郦郡县地处云州西北七百余里,只见一条大江将其南北分割,自东向西纵横而过。
其水运之发达迅速,是邻州间商货互通的优选渠道。为此,云郦郡县便成了云州的商贸枢纽。
当老人行至县城已近亥时,云郦县方圆十里依然灯火通明,流彩熠熠。
只见那绸般的暮被火光烧穿似的难以遮掩这座喧嚣的城。
而城里,目光所及的彼此依偎着的恋侣可谓比比皆是。
小桥上,楼船里,人流中,屋檐下,是那般谈笑自若。
害羞些的,只见女子悄悄将柔荑拽住男子衣摆的一角,低着螓首蹴着脚边的碎石,一步一步思绪漂浮。
孩童们似乎也不想轻易宽恕这般能够随意支配的时日,三三两两的,成群作队的,在闹市嬉笑玩耍。
那般活泼可爱模样,不时惹得过往的恋侣眉目传情脸颊绯红。
“老先生来了!”
“去听故事喽!”
瞧见老人,孩子们仿佛幻化成一只只扑食的乳虎,在人流里穿梭,就好似一条条新生的充满朝气的支流往一处溪流汇去。
而面对这般气势的场景,老人也只是弓着背立在那里,面上干瘪松弛的皮肤咧出道道沟渠般的褶子,“无他,熟尔。”
“先生我帮您!”
“你们别与我抢!”
“与我抢?拿来吧你!”
若非众所目睹,那些听客大概会在脑海里肆意的上色出一幅《孩提市井哄抢图》。
不过这般场景倒是与“哄抢”一词并非毫无关系,不同的是孩子们“哄抢”的不是糖果玩物,却是热衷于表达的那份热忱的爱。
孩子们“分到”手中的木头呈现出块状,几个他们巴掌的大小,却仿佛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活跃。
这些木块都将被送到木工那,经他们巧夺天工的双手化作一只只精致的小船,大块些的,会被雕刻成华美的楼船。
工序的最后则是通过一些特殊的锻造处理,迫使船体在使用时达到能够漂浮的沉重。
这般,一块块曾被孩童放于手心把玩的木头,一经入水便成为了能够载物的船只。
“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呀?”
“今日我们不讲故事。”
听闻此话,孩子们将眼中流露的失望难过表现的一览无遗,老人只能歉然一笑,
“今天我们不讲故事,你们同我一道去见见我的娘子如何?”
“娘子是什么?好吃嘛?”
“娘子就是你嗲的媳妇,也就是你娘。”
一男童解释道。
“嗯?好啊好啊,额正要去娘那呢!”
“。。”
靓仔沉默。
这小吃货脑袋一歪,一副此行正好顺路的模样,惹得众人哭笑不得。
“咳,小家伙,你怎得一个人跑了过来?你家大人在何处?”
老人收敛了些许脸上的笑意,低头询问。
“嗯,额看见那些哥哥姐姐都往这里跑呀,额就跟过来啦!娘她就在旁边啊,诶?额娘走丢了!”
小家伙端起一副严肃的神情,小手叉腰,好似被抛弃了般。
“噗哈哈哈!”
众人再度大笑。
望着这小家伙垫着小脚丫子瞩目四顾的模样,老人脸上是一片无奈的笑容。
只见他悄悄接过一步轻轻拉住她那如润玉般的小蹄子,柔声道,
“走吧,咱们去找你娘,可还记得你娘带你去的何处?四周有何景致呀?”
小家伙把头摇的跟簸箕似的,老人想要说些什么,却见她轻轻合上眼眸,旋即伸出一个小指头对老人点明了方向。
“额能感应到娘她就在前面。”
也不顾上诧异,小家伙反倒是拉着他向前方走去,仿佛走丢的并不是她,而是年迈的自己。
若赶上这般喜庆的节日,那当然少不了热情拉客的民间艺人。
石桥侧岸,只见一个油翁打扮的中年艺人,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持两尺竹竿,挑油壶而向其口,油自钱孔入,而钱不湿。
众人叹为观止称其技艺超群,问起诀窍,其人故作高深,答曰:
“师承家父,世辈相传。我亦无他,唯手熟尔。”
啪啪啪!
“勤之一道虽属小道,倒也蕴有一丝大道之理,而在这贫瘠腌臜之地能窥之一二倒是不易,小爷我心情不错,赏!”
众人闻声而去,只见一身穿锦衣华服的白衣男子将手中的折扇拍打的啪啪作响,身旁两名佩戴斗笠面纱的黑衣男子随行,而其中一位手掌一翻将一锭银子抛了过来。
不等哗然掀起三人已然临近,众人不由自主为其让出一片空旷之地。其中少数人不为所动,可见这些人服饰各异,似是来自三宗五派。
“白黎溪。”
白衣男子略微驻足,旋即向开口之人望去,其目中闪过一丝讶然,却不动声色的微笑作揖:
“我道这般地界谁人识我,原来是石兄,久仰。”
“白家少爷,不知可否让你的属下收敛收敛武势,惊扰到此地百姓在这般喜庆之日倒是让我少了些许乐趣啊。”
也不等白黎溪应下,只见石昊大袖一挥,磅礴灵压骤然降临,那两名随行的黑衣男子各自闷哼一声,跌退许步。
白黎溪见状目光一凝,正要出手夺回场面,却又好似瞧见了何物,拱手对石昊歉然一笑:
“石兄教训的是,他们二人不知礼数扫了石兄雅兴是在下这个主子的失责,我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你们二人还不快去给石家少爷谢罪。”
听闻此言,其身后二人强行稳住内息的紊乱,向石昊低头赔了罪。
“啊!少..”
众人哗然大惊。
只见前一刻还气血方胜的二人,此刻已被斩去头颅没了气息。
“小爷我是让你们以死谢罪,不是在此地低声下气的告罪求饶吧?可惜了。”
白黎溪将手中染血的折扇递向身后的虚空,摇头笑道。
倏的,一名黑衣男子悄然出现在他身后缓缓接过血扇,随即又取出另一把润玉折扇单膝托起。而地上的血渍与尸体也已经被另一位黑衣男子收起清理。
莫说凡人,即便在场的一些修士也被此子的漠视人道所惊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