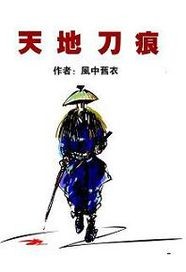“我也不是白雪。”这一句话是杜鹃说的,她的声音沙靡靡中带着一丝丝的甜美,即便是在怒气中也难掩那一段风情。
黄华叹道:“哎……雪少爷又忘了自己的身份。”
其中一个白衣人道:“雪少爷不该忘记自己的身份。”
又一白衣人道:“雪少爷只有一个,是谁也不可能模仿替代的……”
“我们不是雪少爷,也替代不了雪少爷。”
“只因这天上地下只有一个雪少爷……”
“雪少爷就是你……”
“你就是白雪……独一无二的白雪,上天的宠儿……”
“雪少爷是天下姑娘心中最好的情人,也是天下厨子眼中最佳的食客,更是天下间好男儿的好朋友……”
“一遇白雪误终生,没有人会不喜欢白雪,也没有人会不想成为白雪……”
明月越见朦胧,池水烟波浩渺。
时间仿佛已过了很久,他们四个白衣人的话却还没有停。
他们已将这些话反反复复对杜鹃说了很多次,好像在强迫杜鹃接受这件事。
杜鹃根本无法躲避,她只能瘫倒在小舟上被迫听着他们说了一遍,又说一遍,忽然发现自己的思想非但已完全无法集中,而且似已感到被他们说的话左右了。
忽然间,她竟仿佛觉得自己其实就是白雪,自己真的不该忘记这个事情。
那铜炉中的香烟还在一阵阵飘过来,慢慢的摄入她的思想里。
杜鹃突然用尽所有的力气咬了咬嘴唇,剧痛使得她突然清醒。
她立刻尖叫道:“不要再说了,我已明白你们的意思!”
黄华微笑道:“看来雪少爷已经记起来了自己的身份。”
“我明白了。”杜鹃道:“他们的声音不像,气质更不像,我曾经问过勾栏里见过白雪的妓 女,她们说过白雪的声音沙沙甜甜,更像是中性的女人说的话,他们四个都是男人,虽然说话声音压低也带着沙哑,可只要细听熟悉的人还是能够很容易看穿是假的。”
“何况白雪身上从来还一种极淡而充满诱惑性的气味,这种气味恰好是女人的克星,也就是这样他能死死吃定了无数女人,这是其他人怎么模仿过也模仿不来的……”
“哦?”黄华似乎感了兴趣,他饶有兴趣的望着杜鹃,道:“是吗?”
“你们自然知道要靠这样的易容术骗过阳春等人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你就想到了找一个真正的女人来假扮白雪!”杜鹃已经一步步的想明白了,她惨然道:“而我的眼睛天生狭长,身形可能也和白雪相差不远,最重要的是我出身勾栏,身上有别的女人没有的风尘味,这种气质在一个女人身上可能不讨好,突然出现在一个男人身上却是最能勾动女人心坏……”
风尘味,她身上不只是一段风尘味,举手投足之间更有一段奇异而独特的风情。
她出身高贵大家,后来却流落低贱勾栏,身上自然而然的夹杂了最上流的高贵内蕴和最下 流的骚媚入骨的风情,就好像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圣女与荡 妇的合体。
这种独特的气质一旦穿上白雪那一身独特而醒目的装扮,竟能勉强鱼目混珠,大有几分相似,也正是如此,或许能骗得过阳春的火目真睛。
“昔日七叶一枝花果然厉害!”杜鹃冷声道:“你们计划周全,我虽看不穿到底要我假扮出现做什么,但是肯定能够借助天时地利做到百无一失……若方才那月中人真是拜月教小公主,只怕江湖传说是真的,白雪真的已经为了对抗阳春而投靠了拜月教。”
“这样的计划委实过于厉害!”
黄华淡然道:“这本是雪少爷你自己想出来的主意,我等只是依计行事……”
杜鹃怒道:“我已经看穿了你的把戏,你还这百般作态,难怪你要自称自己是条鬼了,行事果然鬼鬼祟祟,见不得光的!”
她这话便如一根刺,深深的扎了过去,她要扎在黄华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黄华似乎根本听不见她说什么,只是继续道:“雪少爷,此次龟城之役,痴鬼决不再退缩,只求此身早去黄泉,于愿足矣。”
杜鹃已经浑身冰凉,她知道黄华早已存了死意,而和一个一心求死的人是绝对没办法讲道理的,她忽然尖声呼喊:“就算是要我为你们卖命,我也要知道怎么做!!告诉我该怎么做!!”
黄华恭身道:“请雪少爷下令,属下听令。”
“好,我下令!”杜鹃厉声道:“我下令!我下令让你去死!”
黄华面不改色,依然恭敬道:“是,属下遵命!”
杜鹃一愣,她脸上露出残忍的微笑,眯着眼尖声道:“你听清楚了,我要你…去…死……死,你可知道?!”
“属下知道。”黄华缓缓从袖中取出一柄尖刀,左手上抬扯掉束发的冠帽,一把抓住自己的头发,右手反手一转,已在那脖子上一刀摸了过去。
他竟说死就死,真的完全听从杜鹃的命令!
杜鹃尖叫一声,她实没想到黄华会真的一刀杀死他自己,她更没想到的是黄华的身体居然不倒,他一手提着滴血的尖刀,一手抓住自己的脑袋,直直的站立着,那双死去后泛白的眼珠子勾勾的望着杜鹃,似乎还在等待着杜鹃的下一步命令。
“你……你是死是活?是人是鬼?”杜鹃已经被吓得要哭出来了,手脚阵阵发麻冰凉。
“我早已死去,本就是鬼。”那颗被割下来的脑袋上的嘴巴还在一动一动的说着话,没见过这种场面的人实在很难想象其中的可怕景象。
“吾名痴鬼。”
明月如洗,皎洁的月光淡淡。
地面亭中香烟缭绕,一个穿着黄衫的男子头颈无首,一手提刀,一手拎头,竟有些像是上古大神——刑天。
刑天断头不死,如今黄华竟也有这样的本事?
杜鹃猛翻白眼,现在她只恨不得自己马上就昏过去,昏过去了这一切都结束了,再也不用受这样诡异的摧残。
“你看着我……”那颗不死的头颅阴测测的说着,“看着我的眼睛。”
杜鹃霍然低头,想闭上眼睛不去看,可她的心底又好像有个古怪的声音在呼喊:看吧,就看一眼,看一眼……
“我知道你很害怕,也很辛苦了,来吧,看着我,马上就可以不再痛苦了。”
她终于又抬起了脑袋,怔怔的看了这死灰色的头颅一眼,目光竟再也无法移开。
从缥缈氤氲的烟霞中看过去,他忽然发现黄华的脸已经又换了一张脸。
换了一张很好看的脸,这张脸在微微笑,笑的很斯文,很好看。
这个已经死去的头颅,忽然间竟似已变得有了生命,获得了新生。
这样的微笑似乎已经渐渐的笼罩在了杜鹃的心房上,慢慢的伸出枝丫,慢慢的扎根下去,紧紧的贴了上去。
杜鹃竟也忍不住微微一笑,她这一笑之后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心里却是百般的不想再看、再笑,可目光偏偏无法从那神秘而妖异的头颅上移开,她的嘴角已泛起一丝温暖的微笑。
这样的微笑已经很像很像一个人了。
“你就是白雪,阳春白雪合余歌的白雪,你本是阳春的好朋友,可是现在他抢走了你的情人的乌静静……”
“你和乌静静本是两情相悦的情人,你们本来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厮守在一起的,可是阳春抢走了她,害的你现在只能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
“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所以你一定要杀了阳春!”
那声音缓缓的说着,杜鹃的面上竟不由自主的露出怨毒仇恨之色,而她的眼睛却渐渐变得空虚和痛苦,她竟完全进入了自己是白雪这个角色里。
“我是白雪。”杜鹃也重复道:“我要杀了阳春!”
她的声音呆板简单,说话更像是三岁幼儿学舌般笨拙。
那头颅继续道:“很好,你已经明白了,不过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强杀阳春,我们要设计好,等到时机成熟才能动手。”
“好不好?”
“好的。”杜鹃已经觉得眼皮有万斤多重,她实在承受不住了:“我想睡一会儿。”
月凄迷,夜凄迷,人凄迷。
“我知道你已经很累了,已经累得连眼睛也睁不开了。这段日子里你实在受过太多的苦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安心的睡一觉吧……”
杜鹃的眼镜终于慢慢的闭上了,她面上的表情也开始祥和下来,“我的确太累了。”
头颅缓缓道:“你要记住,当你睁开眼的时候,你就是白雪,白雪就是你。你是一个活生生的白雪,本来就是真正的白雪。”声音如烟如雾。
“我就是白雪,本来就是……”杜鹃呆板的声音忽然一变,竟然如糯米糖一样的又黏又软,她嘟囔着嘴迷迷糊糊的睡倒在了小舟上,船板很硬咯人生疼,可杜鹃就像是躺在一张很舒服很软的床上,忽然间就已睡着。
她睡着如初生婴孩般恬静。
舟首铜炉香尽,袅袅烟散,仔细看,黄华的脑袋还在他的脖子上,他一袭黄衫,人淡如菊。
四个白衣人早已不知退到何处,看不见踪影。
他一个人孤零零的面对着天上的月宫,脸上更露出如雪般的寂寞。
“八千年玉老,一夜枯荣,问苍天此生何必?”
“这一切又都是何必?”
此问幽幽?
问天极,谁人能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