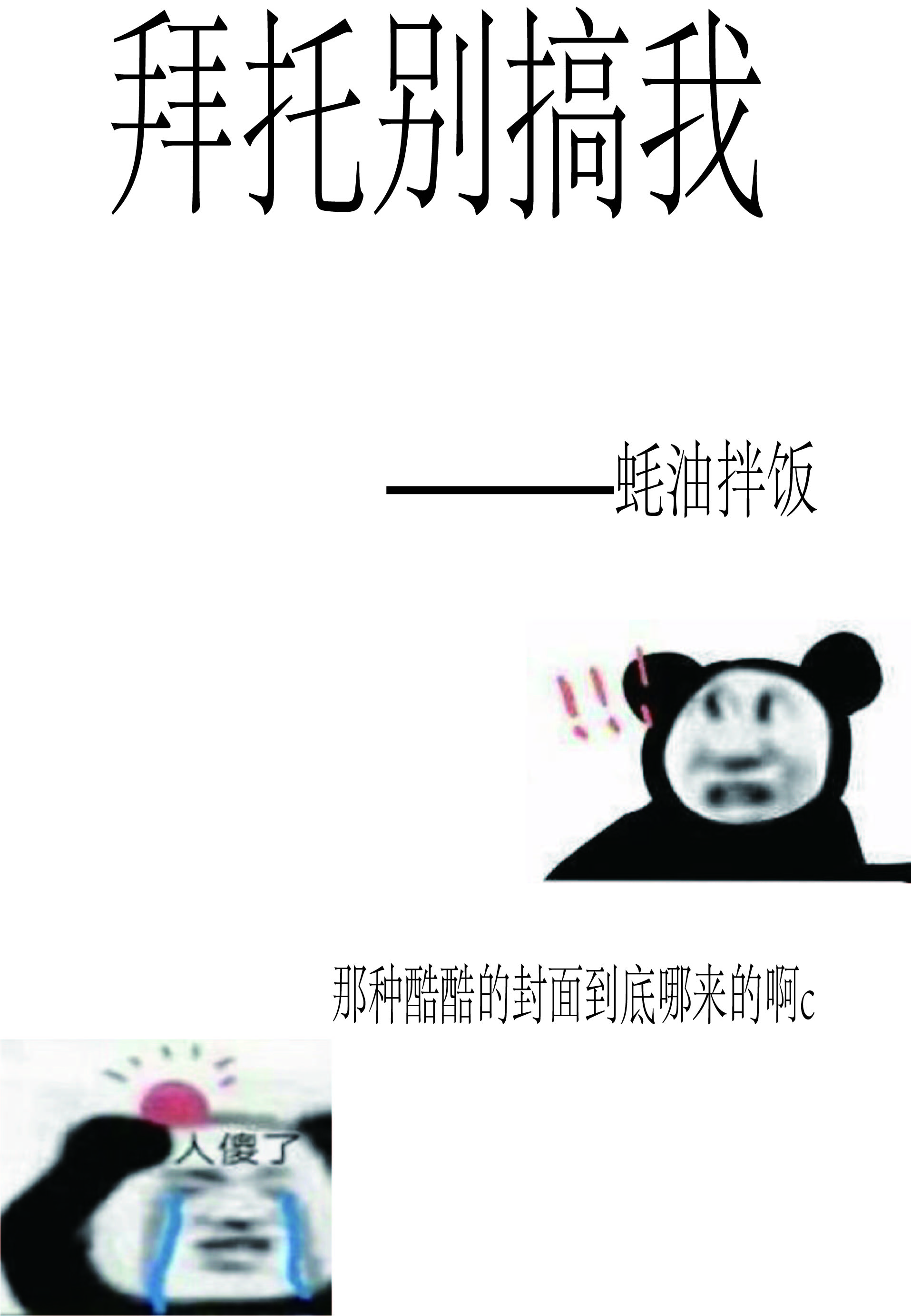当夏瑾瑜一手拉着她走进内室时,怀衫感知到了段若投过来的目光,待要抬起头,那目光也已走远,到了她再也触碰不到的地方。
“人死不能复生,母后节哀!”明裳带着屋子里的人庄重地向皇后行了个礼,她这才松开怀衫的手,
“清婉的死是由她一手造成,本宫隐忍了这几个月都是巴望着她能好起来,谁知,谁知这孩子福薄,竟撒手去了。她生前本宫未来得及好好照料她,替她报个仇,也算能告慰她在天之灵。”夏瑾瑜说着,抹下抹眼泪泪,丹凤眼寒厉地钉了怀衫一眼。
“那件事是个意外,儿臣处罚时清婉也没有什么异议,母后何必要让死者不得安宁。”瑖若毫不示弱地看着她,平淡说道。
“哼!意外?这世上的意外有哪些不是人为的?”夏瑾瑜冷哼一声,并不退让。
“就像当年我母妃突然自尽而亡!”他微微抬高了音量,目光紧紧地咬住夏瑾瑜的双眼,怀衫心里蓦地一顿,他这是在拿自己母妃的死亡作为筹码与她斡旋!
自己何德何能!
她暗自里冷笑,手肘朝后缩了些,将劲道凝聚在掌间,眨眼之间,向上微微跃起, 朝着她的夏瑾瑜的天灵盖猛地劈去!
一道白绫突然翻飞在夏瑾瑜的头顶,化去她掌下所有的力量,怀衫轻悄地立在地上,微微错愕地撇过头,瞧见柳明裳一脸紧张,苏娇玉一向清冷的脸上则带着笑,有些后怕地看着自己手上的白绫,“儿臣冒犯母后了,实在是被太子夫君的话吓住了,袖内的白绫本能地弹了出来飞打在了母后的头上。”
夏瑾瑜头顶的凤冠摇摇欲坠,忙被明裳扶住,整理好。
一旁的宫女垂着头,大气不敢出一声儿。
“好大胆的丫头!”张总管右手抖了抖,干哑的声音突兀地响起“明明是?”
“是我冒失了。”苏娇玉看了他一眼,“张公公一向眼睛尖利的很,过眼的翡翠珠玉从未有过失手的。”
张公公嘴角动了动,手缓缓地垂下,“是,玉侧妃说得极是。”
皇后的目光缓慢威严地在场中扫视一圈,最后定格在了她的脸上,“既然太子舍不得杀你,清婉又没有留下子嗣,那么接下来的七七四十九天,就由你来位她披麻戴孝守灵吧。”
她说完最后看了眼床上收拾整齐了的女子,施然走了出去。
瑖若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待到皇后走出很远,才低声吼了出来,“你这是想干什么?自会玩背后偷袭的把戏么?能不能动下脑子啊!”
怀衫只是低着头,一语不发。
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在心底打定的注意,遂平和了语气,让明裳去给她拿一套孝服。
整个葬礼持续了半个月,她在灵棺前接连跪了三个晚上,头脑昏沉中想起了死了的谢宁璎,眨眼间,世事苍茫,诸多身不由己,只有她选择停留在最纯真美好的年华,保住了那个最初的自己。
“我该去给她扫墓了吧。”她在心里生出这个想法,转过身望向宫门外悠长的空旷,无尽的黑暗层层袭来,宫灯绰约却照不亮前方的路。她想起自己挣扎了这些日子,几次没能杀掉皇帝,心却渐渐岑寂,她转过身看两眼冷白的蜡烛,附身跪着,“林椴衣,你在哪儿?可不可以带我走?”她本是极低的呼唤,心口一颤,身子被一双强有力的手环住,静默地相依,怀衫终是推开了他的手,“太子这么晚了去歇着吧。”
“我会放你走的。”他轻声呢喃了一句,转身决绝的离开,她看不见他的面容和表情,心,在那一刻低沉、陷落再也拔不出来。
葬礼完后,她仍旧被送往青衣巷,宫中怪事频出,接连有宫女后妃莫名患病,查不出根由。
太医从一件件可能引起传染的根源上查起,排查了日产食物、餐具、衣物等,俱没发生什么异常。
青衣巷的活计更重了,皇后下令将春夏秋冬所有的衣物都拿出来洗一遍,同时吩咐各宫将所有的东西用太医配的药水清洗一遍,整个皇后弥漫这一种浓厚的草药味。
青衣巷接连有宫女患病,唯独她安然无恙,怀衫也感觉有些奇怪,用力地吹着厚重的棉袄。
宫里下令御河里的水暂时不能用,她只得艰难地从井里舀起一桶桶水,抬头的一瞬间,看见了院口的谢流碧,手里提着一个布袋。
“西南刚送进一批绸缎,顺带带了些雪梨过来,让你尝尝。”
雪梨不多,只有两个,流碧顺手在桶里洗了,递给她,“来,吃了吧。”
怀衫伸了伸手给他看,“多谢师兄了,可我先走手上都是碱水,还得漂洗衣服呢。”
流碧不由分说地将她的双手摁进水里洗净,后将两个雪梨塞到她手里,“衣服等会儿洗,先走吃梨。”
怀衫无奈,只得拿起一个梨,咬了一口,“我现在吃了,师兄快走吧。”
“呵呵,我家公主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不会吃醋的。”他轻笑一声,目光定格在了院门口。
“皇后娘娘驾到!”
怀衫一口梨噎在嘴里,低下头艰难地吞下,在流碧身后垂下了头,“儿臣见过母后!(奴婢见过皇后)”
“九驸马这么好的闲情逸致,跑来青衣巷了!”
“回师傅,儿臣奉师父之命前来看望师妹。”
“什么师兄师妹的,在这个皇宫你要遵循的是宫中礼仪,你们一主一仆,这样混在一起像什么话!”
夏瑾瑜的话中明显带刺,流碧恭敬地回到,“儿臣知错,谨记母后教诲。”
“嗯,那就随本宫来巡视一下这青衣巷吧。”
流碧上前扶着她的胳膊,附身走着,目光看了看她,又看了看井边的梨。
怀衫忍不住在心里苦笑,吃不吃两个梨真的这么重要?心念一转,忽地想起什么,她的目光艰难地追随谢流碧而去,他已经背过了身随着皇后走远了。
皇后走了一圈,半个时辰后又回到院口,目光深邃地看了她一眼,脸上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怀衫将剩下的一个梨于夜间悄悄递给被隔离在一处偏僻院落里患病最重的彩儿,徘徊不安地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忙去跌找了个空偷偷溜进院子,彩儿的气色与昨日无异,她不禁凛眉,是自己多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