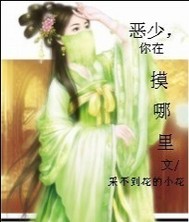“臣妾见过皇上。”夏瑾瑜恢复正色向康玥晁福了福,他没有回头,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谢冰展尚自在将头埋在他怀里哭着,良久,才抽抽嗒嗒地抬起头,委了委身,算是行完礼了。
“你给朕好好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夏瑾瑜忍不住一声冷笑,“臣妾好心好意给妹妹煎了安胎药端来,是哪个不安好心的暗中作祟,导致冰展妹妹流产,臣妾若查出来了,绝不轻饶!”
康玥晁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她脸上的激愤不减,一脸不平。
“将那个送药的宫女找来。”他挥了挥手,脸上是盛怒后的怠倦,是的,怠倦。
他目光空洞地盯着床尾的帐棱,忽然想起了离世很久的她,这么多年过去了,因为她的死,他变得无限宽容,甚至故意对后宫这些尔虞我诈视而不见,可他们却愈演愈烈,他的心究竟该落在何处。
夏瑾瑜仔细地观察者他的一举一动,若说宫中最了解他的人,非自己莫属,所以她心里一点也不害怕,脸上自然要写上莫大的委屈。
“回皇上,宫女鸢儿带到。”
送药的鸢儿早就哆哆嗦嗦地跪下,一连说了几个不知道。
夏瑾瑜走上前去,半弯着腰,不由分说狠狠一巴掌扇到了那个小丫鬟脸上,“本宫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陷害本宫?”
小宫女本就心乱如麻,这一被打,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皇后步步紧逼下,她边哭着边语无伦次地承认,自己送药到半路,突然肚子疼得厉害,急着如厕,便将药放到前往展玉宫的路上的一处草丛掩好,便跑去如厕,然后急忙跑回来,将药送到了淑妃娘娘那儿。她实在不知道路上发生了什么事。
“走!带本宫去你放药的地方!”夏瑾瑜说着,一把拉起她的手,将她拖着朝屋外走去,“你们跟着去看看。”皇帝对贴身的太监说道,又指了指屋外的人,“让太子妃和她身后的那个宫女夜跟去吧。”
明裳和怀衫领命,跟在夏瑾瑜和宫女鸢儿的后面,一路拖拖拉拉,宫女鸢儿将她们带到路边的一处灌木,明裳盯着灌木下的草丛,有明显的被压的痕迹,草尖上沾了些黑色的药珠。
她要看了看灌木的位置,微微皱紧了眉头,怀衫也将一切看在眼里,一回头,这儿恰好是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往凤瑜宫,一路上还有其他妃嫔的宫殿,另一个方向,是条小径,一边傍湖,一边是草坪和假山,而小径的尽头,三四里外正是太子东宫。
原来夏瑾瑜故意磨蹭许久,便是为了设下这个局,将嫌疑转移到其他妃嫔更重要的是太子身上。
如此心机!不能不说是绝处逢生!
冰展在皇帝的臂弯里打量着众人脸上的表情,知道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她在暗地里绽放了一个微笑,被脸上深深浅浅的泪痕和皇帝的手臂所遮挡,所以分外妖娆,而无人知晓。
“太子妃,你告诉皇上都看见什么了吧。”
“是母后。”,明裳说罢看向皇帝,“禀告父皇,儿臣随母后一行,果然在一处灌木下发现草有被压的痕迹。只是、、、、、”她说道一半兀自顿住,目光探询地看着康玥晁。
“有什么都说出来吧!”
“请父皇和母后恕儿臣无不敬之处,儿臣方才敢说。”
康玥晁目光阴沉地看了夏瑾瑜一眼,夏瑾瑜依然是一副愤懑的表情,听了明裳的话,淡然说道:“你看见了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不敬的。”
明裳这才说道:“儿臣在发现被压过的草尖上沾有细小的黑色药珠,想是有人在动装药的锦盒时不小心把药洒出来了些,只是淑妃娘娘喝药至今已过了一个多时辰,这些药珠还在,令儿臣有些不解。”
“你继续说。”康玥晁的目光已锁定夏瑾瑜,看着她的神色由得意慢慢转为惊诧而又强自保持着,复又恢复不平。
“现下虽已是初秋,天气还没凉下来,儿臣以为,这些药珠应该早已被太阳晒干了。但这些知识儿臣的猜测,请父皇恕儿臣无罪。”
怀衫不由暗自惊叹,明裳师姐果然心细如针,而且机敏过人。
“皇后,你怎么看呢?”皇帝的脸上已漂浮着一曾阴冷至极的微笑,显然是生气到极点,一句话也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臣妾也觉得明裳分析的有理,这一切根本就是有人在暗中设计好了的,臣妾恳请皇上,彻查是谁在背后作鬼!”
她的目光环绕房中一圈,态度强硬,不容有任何勇气质疑。这就是夏瑾瑜,即使情况再不利,她也要已不容置疑的高傲来粉碎所有的猜想,只是心长在人的体内,她能做的只是威慑到她们的嘴而已。
“你是六宫止住,后宫之事,朕就交给你一手彻查,真相信三日时间对你们已经足够了吧。”
“是,臣妾领旨。”夏瑾瑜毫不示弱地行了一个礼,退下,明裳见状,给其他两位侧妃使了个眼色,一齐退了下去。
“太子妃心思敏捷聪慧,本宫可否向太子借用你三天,待水落石出后,再亲自送你回宫。”
“为母后分忧解难,是儿臣的本分。”明裳说着便转向夏清婉,让她向太子转告此事。
夏清婉一愣,才回过神,俯身答道:“是。”
怀衫跟在她们后面回太子 宫,瑖若在书房里看书,夏清婉带着丫鬟进去向他禀告了明裳要在凤瑜宫待三天的消息,瑖若驱散四周的奴仆,走过去,一手紧紧捏住她的下巴,“夏瑾瑜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她若敢动明裳分毫,我保证你再无机会活着走进凤瑜宫。”
夏清婉第一次没有回避他厌恶愤恨的对视,面露嘲讽,眉眼带笑,“这一切不都是太子安排好的么,对着我,你还需要掩饰么?”
从第一日开始,他从不吝惜在她面前展示最邪恶、最残酷的一面。每一次的宠幸,在别人眼里,是无上的恩宠和莫大的荣幸,只有她知道,每一次自己都被折磨地死去活来,痛地锥心刺骨。他知道怎样掌握分寸,将她的身心折磨遍,却不露出任何瘀伤的痕迹。她早已不对他报任何希望,既然注定他们站在敌我的对立面,注定了她是夏瑾瑜的侄女,他们就应该这样,势不两立,相互折磨,将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羞于见人的那个自己,彻彻底底地展示在彼此面前。
瑖若愣了愣,看着她满眼的决绝,不由松开了手,第一次,他的语气软了下来,“你下去吧。”
“臣妾告退。”她行了个礼,脸上的泪痕都未来得及擦,逃也似的打来门,跑了出去。
怀衫正端着两杯茶,差点和她撞个满怀,发现她脸上的泪痕和下巴上的红印,她不由一愣,“婉娘娘,您这是怎么了啊?”
清婉仓促地看了她一眼,掩面跑远了。
“进来!”屋里传来瑖若的声音,她只得回过头,端着盘子进去,“给我讲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淑妃娘娘的孩子没了。”怀衫讲茶递给他,不由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