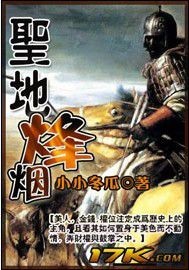?【郓城县】
史进乔装打扮,经过郓城县几道搜问盘查之后,便进到了郓城县来。一踏上郓城县里,史进便朝着宋江的外宅去了。沿着熟悉的小道,在街巷里七转八转便来到了那朱门前。那朱门两扇紧闭,史进微微推了推,连条缝隙都不曾留,看样子像是从里面闩住了。这青天白日,缘何从里面反把罗门锁了,莫非宋江出了什么事?想到这里,不禁有些忐忑。
史进赶紧抬起手来,往下抖了抖有些肥大的袖口,当当当地便叩响了罗门。
这院里不见有人应话,也不见人来开门。
史进便抬起手来又敲了敲。
当当之声落下之后,院里并没有什么动静。
史进心里紧了三分,赶紧用力地拍响了门板,咣咣咣之声,哄然响起,可是,却任然不见有人来开。史进心里寻思道:“不该听不见啊,怎地不曾有人来开门,莫非人都去了……不对!若是离去,那又是何人反锁!可是,既然反锁,怎地不来应门?!莫非……哥哥家里出事了……”史进想到这里,赶紧往后退了几步,略略看了看那一人来高的墙头,约莫着,自己也跃的过去,当下便往后又退了十几步,瞅着了那墙上的落脚点,便疾步快奔,到了墙脚前面,猛然跃起,借着那去势,就半墙腰里踏上一步,双手往上一纵兜住了墙头的边沿,双臂继而用力,脚下踏着墙体几步,就这般翻过了墙来。
史进双脚轻轻落在了地上,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滴,心道:“看着时迁兄弟飞檐走壁那般容易,却不想轮到自个儿翻个墙头也这般笨拙,看来这翻墙越户也不是人人都做的了得,要是时迁兄弟在这里,岂不是好了。”史进的念头一闪而过,四下里在这庭院里看了一圈,只见这院里错落有致,没有什么狼藉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显然不像是有什么祸害发生。
史进本欲开口叫宋江几声,可是,听得楼上似有响动,当下便住了口,轻手轻脚绕过前堂,从侧旁的楼梯上的楼来。史进越往上走,那声音就听得越诡异。那一声声近似痛快的**,像是压抑中的声张。让史进一时间心生猜忌,赶紧蹑手蹑脚转上楼来,越往那门边上靠,男人重重的喘息史进便听得越真。虽然史进不经那事,但是,却也倏然懂了半分。脸上微微泛起一层红霞来,往前迈进的脚步也木木地顿在了门口。
史进此刻心里后悔不迭,怪不得哥哥不来应门,原来却是……我这翻上来,倒是唐突了些,我且退了出去,晚些再来才好。于是,就在史进刚要挪步下楼的时候,突然那屋里的人说话了。
“三郎儿,快,快些,再快些。”史进听得出来,这是阎婆惜的声音。
啪的一声脆响,亮的像是一个耳光,史进没反应过来,就听里面一个男声道:“小浪人,却不知羞!这就来了!”
史进听得这声音全身不禁一颤,这……这分明就不是宋江的声音,可是,眼下不是宋江却又是谁,莫非——史进突然想起那天的阎婆惜在门口堵着死活不让进来的那个男人。史进心里听得心里有些发狠,噌地从靴子里将那匕首持在手里,贴着往那门口去了。
阎婆惜这时候又是一声**,笑嘻嘻之间有些恬怪的意思道:“好好弄你的,你打我屁屁作甚!”
“留的这般肥臀不是与人拍,却又是怎地用处,哎呦。”显然,那汉子被阎婆惜扭了一下耳朵,稍稍有些吃痛,当下打情骂俏着又在床上滚着。
史进用匕首将那纸窗戳开一个洞口,抬眼望进去,只见一个浑身赤裸的汉子此刻正抱着阎婆惜放在梳妆台上颠鸾倒凤。史进这一眼瞧明白了,当下便想闯了进去,一刀将那后生杀了,可是,史进转念一想,此番来了便是为宋江哥哥除祸,若是一上门来就将在哥哥的院里闹出人命来,到时须连累了他,事情闹大传扬出去,却也不好听,哥哥脸面往哪里放。史进想到这里便顿了一顿神,这才生生挨下这口气,收束住冲动的心神,仔细将那人的脸面记在心里,便抬起手来敲了敲房门。
“嗯——?”阎婆惜和那汉子听见房门声响心里倏然一惊,两人赶紧停下来,两对眸子直勾勾地瞧着门的方向,间那房门依旧牢牢关着,心里这才定了一定。
“你听到了么?”阎婆惜睁着一双大眼,看了看那门,又瞧了赖在她怀里的小张三一眼。
张文远方才确实听到些响动,只是,方才交合之间,非但皮肉撞得啪啪直响,两人娇喘**不止,连那梳妆台也被弄得吱吱扭扭,这些声响之下,虽然三下敲门声惊了两人一跳,可是,张文远此刻箭在弦上,正到美处,哪里还管那些,只当是自己听差了,于是便道:“听着什么,准是你听差了。”
“奴家听得有人敲门咧!”阎婆惜生怕宋江回来,当下便要推张文远起来。
可是,此时的张文远色急的很,哪里这般由她推开,当下一把抱的那阎婆惜更紧了,阎婆惜挣扎两下埋怨道:“真的有人敲门,被人撞破,须知不是玩的!”
“大门锁着,如何进的来,他宋江莫非长了两张翅膀能不声不响地飞进来不成。”张文远说罢不但不放,一把将阎婆惜赤裸的玉体横抱起来,三步并作两步便丢在那大床之上,一身扑上便要使强,他见阎婆惜还不肯与他耍,当下便又柔声细语地安慰道:“宋江是个知礼的人,他要进来时,须得敲门,待到那时,我们照旧,你穿衣开门,我从后院出去便是,当真神不知鬼不觉!来吧,让我伺候得你妥妥帖帖!”说着张文远拿手在阎婆惜鼻头上轻轻一剐便亲起来。
张文远那舌头滑溜之极,功夫也实在了得,弄得阎婆惜忍不住的娇喘,吻过的脖颈更是浮起一片殷红,直把她骨子里的欲望都在这小舌头上钩了起来。阎婆惜听得张文远方才的话,觉得有那么些道理,加上眼下欲火焚身,哪里还有那么多的顾忌——死了便死了,老娘哪还顾得那般多——阎婆惜心里这般想着,高高地扬起脖颈,任由那张文远舔吸的时候,突然那房门当当当又是三声!
这下两人都听得分明,顿时那张文远也直起头来,两人竖着耳朵听那门口的动静。阎婆惜这次再也不肯相信自己听得是幻觉,当下用力一把推开张文远,一把扯了被子盖在自己光溜溜的身上。而那张文远却愣在当下,不知该当如何,唬得动也不敢再动一下。
就在两人屏气凝声盯着门口时候,那门咣咣咣地拍响起来,这力道分明比方才多了三分急躁,两人看着那扇被拍的框框直抖的门扇,被吓的魂不附体。
阎婆惜一面扯了件床头的衣服披在身上,一面故作镇定地问道:“谁啊——?”
门外不说话,当下不再拍门了,抡起拳头来便是三捶,那门扇被拳头砸的像是风雨中的落叶,摇摇晃晃,而惊得阎婆惜却再也张不开口,而那张文远也被唬在原地,全身像是被冻住了一般,一丝都动弹不得。一双做贼心虚的眸子紧紧地盯住那扇哄哄欲倒的门扇,两腿筛糠似地发抖。
“愣着干啥,还不穿了衣服走!”阎婆惜急了赶紧强压着声音喝道。
张文远听了,这六神无主的才恍然过来,赶紧光着屁股跳到那床侧去,将衣服胡乱地往身上穿。可是,刚刚穿了一半,只听得咣当一声巨响,那门扇被一脚踹开,两扇门面哄地一声撞开来,唬的那张文远不及多想便露着半个屁股越窗而出,只听得稀里哗啦一片瓦声响,想罢是从二楼的楼檐上摔下去了。
史进一个箭步冲到窗边,探身再瞧时,只见那汉子摔在前院的青石板上,此刻正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将起来,一把拽开门闩,一瘸一拐慌不择路地只管逃窜。史进看在眼里,冷冷地哼了一声,道:“摔不死你这鸟厮!”
史进回过头来,却不禁有些惊了,只见阎婆惜缩在床角,蜷起身来用双臂紧紧地抱了,方才尽兴云雨时弄乱的几缕青丝垂在脸前,而她那一双眸子滚滚含泪,在眼眶里滚动两转便忍不住答滴答滴落了下来,这哭的梨花带雨,一副受尽委屈的模样。
本来史进心中有气,转身欲骂,却不想看到这般景象,一时间目瞪口呆不知该如何说了。史进知道这阎婆惜又耍什么花招,当下愤愤一叹,说道:“你这是何苦!”
“多——多谢叔叔救命之恩!”阎婆惜哽咽说着便愈发哭出声来。
这一句却听得史进又是一愣,他万万没有想到阎婆惜竟然是这般会逢场作戏之人,当下虽然惊叹于她活灵活现的演技,但是,在心里冷笑之余也不禁出言讽刺道:“你这里头究竟是几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