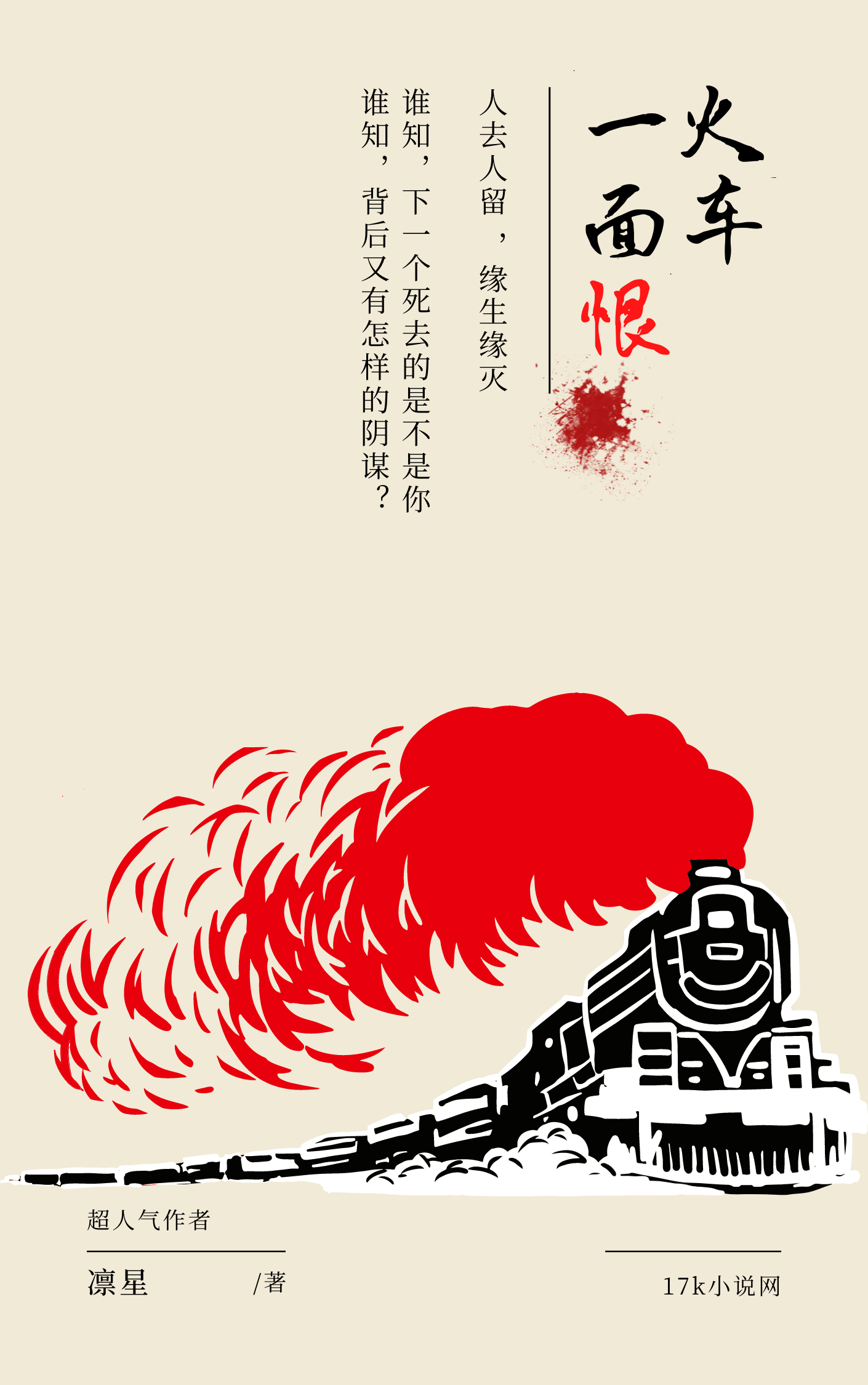在救了言一之后,远颂军仍然没有停下脚步——连禾关距平州的距离不算远,言一他们绕路疾行半日就可以到达,虽说远颂军几千人不知道那条近道、不可能绕路,但也仅仅只需要三日就可以抵达平州。
本来队伍里是没有供伤员休息的地方的,但由于大军在蛮族的驻扎地停留了半天,找到了几辆半新不旧的马车随军带着用来押送蛮人——他们自然是不可能把所有的蛮人都给杀干净了的——马车里关着的都是一些蛮族人的将领。
杨宿自然不会知道占了平州城的人不是蛮族——他还准备凭着这几个蛮族将领去把平州城给换回来——如果换不回来,这几人还可以用来祭旗。
这也方便了言一,杨宿知道了言一被找到的事,又想了下自己家的孩子,还是均了一辆马车出来给言一养伤。
“郎中,我姐姐她现在怎么样了?”游道问道。
“……唉,”郎中先是摇了摇头,“情况不太好,但是幸亏这小姑娘平日里身体不错,养养应该还是能养好。”
“……”游道闻言,先是顿了顿,才继续说道:“麻烦郎中了。”
送了郎中下了马车,游道就看见杜越走了过来。
“行鹿小子,颜舒她……”怎么样了?
“郎中说需要好好养养,”游道皱着眉头说道。
“养养啊……”杜越拉长了声音,“人还在就好。”
……
平州,
“军师,杨宿的军队朝着平州来了。”薛达站在城楼上,看着前方的护城河,开口道。
“来了就来了,”刘旦笑了笑,“他们来了又能如何呢?况且我已经把阿列达死的消息告诉阿赉了。”
“嗯?阿列达死了吗?”薛达下意识地问道,他们可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这不重要,”刘旦斜了他一眼,“只要阿赉相信他死了就行。”
凭他们的力量守不住平州,但是若再加上阿赉那个蛮子的力量呢?他定会让杨宿有命来,无命回!
……
“你说什么?我弟弟他……死了?”阿赉简直不敢相信这个话,“他怎么会死?!”他想到他上一次见到他弟弟的时候,他弟弟还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还笑着说等这次胜利了就回到家中去见阿妈……结果现在人没了?
阿赉想,他不相信,“是谁干的?”
“是……是豊朝人。”报信的人声音都在抖,他害怕大将在盛怒之下会拿他出气。
“豊朝人……”阿赉缓缓地吐出一口气,“他们现在在哪儿?”
“什么、什么他们?”
“那群该死地豊朝人啊——”阿赉一脚踹了过去,“他们现在在哪儿?”
“在、在平州城外……”报信人捂着肚子说道,“他们去攻打军师了。”
“攻打军师?”阿赉反问道,“好——你回去告诉军师,我阿赉定会去助他。”
“是——”
那群该死得豊朝人,“传令下去,让咱们的儿郎们准备好,明日随我去平州城,给小王子报仇!”
“是。”
阿列达为什么能够在军营里那么嚣张呢?
原因很简单,他是蛮族部落首领的小儿子。
而阿赉则是他的哥哥。
蛮族本来生活在豊朝的北部,过着逐草而居的生活。
但是由于北部草原的气候变得愈发恶劣,蛮族不得不向南迁移,本来他们向南迁移是影响不到豊朝的——但是蛮人的生活方式实在是与豊朝人不同,他们的羊和马,破坏了边地百姓辛苦种出来的粮食,而他们时不时的捺钵习惯,更是让山里的猎户苦不堪言。
蛮人们活得愈发自在,边地的人们就更加痛苦,百姓心生不满,加剧了豊蛮冲突,时常会发生一些斗殴,惊扰到了当地的郡守,当地的郡守便驱逐了蛮族人。
郡守们想得很是简单——既然是他们导致了民心不满,那么把这些蛮人赶出去,不就一劳永逸了吗?
可事实永远不可能像他们想得那么简单——蛮人被赶出了边地,边地的人们恢复了以前的生活,
但是离开了边地,蛮人们根本就无处可去,他们生长的草原驱逐了他们,投奔的新城也瞧不上他们,无数的蛮人冻死在了那个寒冷的冬天。
于是,蛮人的首领们决定,他们要推选一个王出来,一个能够带领他们向豊朝人复仇的王出来……
阿列达的爷爷,就是蛮族的第一任王,他带领着蛮人躲进了豊朝边地的深山里生活,养羊、喂马,休养生息了十余年,终于在一个春天出来,攻打了豊朝的边地城市。
重新出来的蛮人不再是以前的蛮人了,他们痛恨那些驱逐了他们的豊朝人,便见人就杀。
郡守们没有防备,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城池被蛮族屠戮殆尽。
边地的惨状被告知到了国君的耳里——那时候的国君也是一个硬气的人。
他一面恼怒于郡守们的见识浅薄,一面把边地的城池分派给了各个善战的将军,
将军们带着自己的亲卫出兵边地,没出一年就把那些只知道使用蛮力的异族驱逐干净了,蛮人又恢复了原来无家可归的原状,也加深了对豊朝人的仇恨——豊蛮之间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在上一代国君在位期间,蛮人在对战豊朝人的时候,一直都处在劣势,没占到什么好处,
直到这一代国君昏庸不作为,蛮人那边又出了阿列达的父亲——那个枭雄一样的人物,豊朝人便开始了节节败退。
直到杨宿的出现,豊朝人才又扳回了一城。
蛮族占了边地外部的三座城池,而平州就是外部城池之中最后一座,一旦蛮族人占据了平州城,那么无异于把他们剩下的城市直接暴露在蛮人的眼皮子底下——这就是为什么杨宿那么着急的原因。
由于平州城的重要性,能够驻守平州的将军,别的可以不要,但一定会是对朝廷忠心耿耿且为人小心谨慎的。
但杨宿却忽略了另一层问题——那就是将军的私心。
驻守临州的将军,同传琅本就是同一门下的,一听到是临州来人,他自然会放松警惕——更不要说平州城的将士已经饥寒交迫了好些时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