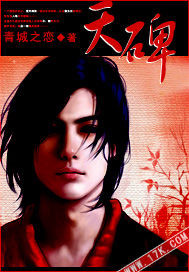我在黑色中。
黑色中矗立的,是有着三十年历史楼。
雨下的很大,江州的天气如一楼老爷子的脾气般固执且奇怪。
一切和三年前都无差异,包括那嘎吱作响的铁门。
我刚从遥远的不周市跋涉至此,身上没有一丝是干的,雨水顺着身体,滑向水泥地板,地板也跟着受罪。我对它说了句对不起,而后转身上了楼。
熟悉的阶梯,那是我曾梦寐以求的。五层,她家的大门伫立眼前,黝黑,威严。我没有敲门,一旁的台阶上,我坐着,时不时抬头仰望那明亮的灯泡……
我想起了三年的奔波。本可以选择踏入室内,尽情享受光的暖她的柔,和世间的美好,爱情的喧闹。
可惜,我偏爱理性,而后一切崩塌,于心不忍,也只得奔向苦海。
我记得残忍离开的原因,也记得厚颜回来的原因。我记得所有,就像玻璃后的蛋糕,清晰的看见,也只能如乞丐般远远的眺望。奶油的香气,面包的味美,可望而不可及。只有蛋糕的光鲜亮丽属于我,以及那冰冷玻璃……
走时,下着雨,回来,雨更大,没停过。雨里,亘古不变的是我的伫立。一群狗也在伫立,它们是中华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狗,并引以为傲着,昂首挺胸地伫立在雨中。它们失魂落魄,目光呆滞,任凭雨水的击打和冲刷,跳蚤虽冲下来几个,但并不影响它们活蹦乱跳。它们在绒毛里享受着,和狗一样毫无畏惧。它们一起在雨里观察,审视着世间万物。
我在楼里,望着楼外,是层层细雨。
突然的,仿佛发现了什么,一条狗冲着远方吠一声——那是一位特征明显的中国人,他有一双丹凤眼,蹲在墙角,重点是他的衣服是李宁的,手机是华为的。所以他浑身清净,没一点毛病。
那狗显然不这么认为,那群狗也不这么认为。它们冲着他狂吠。
他显然不明白这群狗为什么要这样干,因为他穿的鞋是耐克而不是鸿星尔克的,所以枪响不绝。
“你不爱国!”
“滚出中国!”
它们仿佛这样也确实这样叫着,谩骂充斥着整个雨夜。更多的狗闻风而起,不分青红皂白地跟着谩骂。
男人解释了,他的鞋是别人的,自己的鸿星尔克被人换成了耐克,狗不管。
男人愤怒了,狗更欢。
男人哭了,狗笑了。
男人无奈自杀,狗们一哄而散。
它们那刚杀人的嘴里竟吐出:“那不关我的事。”男人的尸体大声说:“是它们杀的我啊!”
人们听不见。
它们是这样给刚来的路人解的:“他叛国了,这是应有的惩罚。”男人的尸体咆哮道:“我只不过是穿了双鞋!”
路人们焕然大悟。
“叛国,真是死有余辜!”
一个路人发出疑问:“是真的吗?”
狗们有的生气,有的不屑,但都统一以不可置疑的语气说道:
“你要叛国?”
路人逃走了。
我只是想笑,转身上了楼,也便忍俊不禁了。笑声充满了楼里,回荡在雨夜和杀人狗的耳畔。狗们不觉不安,静静伫立在雨里亘古不变雨里,等待着下一个猎物。
“只是玩梗,只是上头,只是随口一批,只是缺德一乐,何必上纲上线,装什么众人皆醉你独醒。”
这是狗们的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