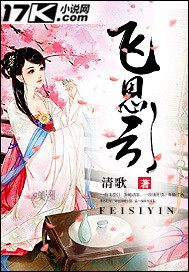第一百五十章 自饮自斟
刘冲眼见濮阳帝目不斜视,一下朝回到王府内便头也不回直接扎入书房内,听暗卫回报的王妃的下落及田桂的下落。自从自青州回来之后便日日如此,日复一日,却从不见好消息。身为一心效忠王爷的下属,看在眼中,难受得堵在心中。
一路屏退好些见礼的王府下人,刘冲随在濮阳帝身后走进书房,只见濮阳帝果然一成不变地径直迈向书房内的桌案,随手拿起案上的折子便低头批阅起来,似乎连刘冲跟随在他身后走进来都未发觉。
刘冲见此,只觉心中堵着的巨石越发沉重。
如此下去如何了得,刘冲踏步上前就要劝说些什么,却见一道黑影在他之前突然出现在濮阳帝的案前,突然得好似乍现的鬼魅,一身黑色的行头,出现得悄无声息几近不可察觉,待发现之时那黑影便单膝跪在案前,蒙着黑巾低头恭敬道:“禀王爷,尚无田桂的消息。”
原来是来回禀消息的暗卫。
案上之人似乎早有预料,头也不抬一径不停下手中的紫毫笔,勾改批写,连眼皮亦不见抬一下。
暗卫习以为常,低着头未见王爷有新指示,当下黑影微晃无声无息消了身形,消失在书房内,鬼魅的身形好似从未出现过。消失去往何处,自然是继续追查田桂的下落,并生擒归来交由王爷亲自处置,这便是王爷自青州城归来后下的第二条死令。
至于第一条……
刘冲小心地瞟了一眼案上之人,只见主子面上专注于笔下的折子,眼神波澜不惊,平静的吓人。越是平静,平静之下的暗藏的杀机越发惊人,刘冲对此清楚无比,王爷便是越平静越深沉之人中的翘楚。若是田桂被生擒,那后果于田桂而言简直无法想象,绝对会令他宁死不宁生。
就在刘冲想得胆寒之时,又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案前,与前一人如出一辙的装扮及动作,径直单膝跪在,敬畏道:“禀王爷,尚无王妃的消息。”
微动的紫毫笔一顿,随之飘出一道淡淡的声音:“加派人手。”
“是,王爷。”暗卫沉沉一叩首,身影一晃了无痕迹消失了踪影。
寻找王妃的下落,是第一条死令。
果然如此。刘冲见此,心中更是堵得慌。只有跟王妃切身相关的事王爷才会有反应,其余的,只怕是责任加身之下的例行公事。
“王爷,王妃只怕是有事受阻,不能尽早回来,待过些时日定会归来。”刘冲不由急道,只不过这话是要安慰主子还是说服自己,毕竟那样的险境,王妃又不通武艺,如此之下最大的可能便是……
头也未抬,濮阳帝依旧注目于案上的折子,紫毫笔行云流水地来回动着。刘冲话音落下半晌,方慢悠悠扔出一句话道:“下去吧。”
刘冲一听只道急于再说些什么,但见濮阳帝批阅着折子根本未见分神的模样,张了张嘴,终究将话语咽了回去。王爷与王妃的事,外人终究无法插手,现下只有找到王妃,一切方能迎刃而解,只是王妃是生是死尚不知晓。
暗叹了 口气,刘冲道了声:“属下告退。”边躬身行了一礼,退出了书房。
正行至书房门口外十余丈,便见迎面走来一名翠衣的侍女,半低着头恭顺安分的乖巧模样,而她手中端着一方紫砂托盘,托盘上托着一个竹子印花的精致紫砂茶壶及一只精致的茶杯,茶壶壶嘴冒着氤氲的雾气,内里显是刚刚泡好的茶。迎面走近,只见该名侍女眉目秀美,唇红齿白,却是爻兰绯院内的侍女之一——离莺。
眼见是离莺,刘冲眉头几不可见地一皱,离莺不是在王妃的清风居服侍么,何时分配了服侍这些服侍王爷的事务?看到离莺此去的方向,刘冲眉头皱德更紧。就在快擦声而过之时,刘冲突然不动声色道:“等等。”
离莺半垂着头,听到刘冲的声音停下脚步,端着茶转过身来面对刘冲欠身行了个礼,小声道:“刘大人有何吩咐?”头却埋得更低,一副听候指示的安分模样。
“这茶可是端给王爷的?”
“是。”
刘冲盯着她的头顶半晌,方挥手道:“小心点,莫要打扰王爷。”
“是。”离莺没有抬头,小声又道了声是,欠了个身,与刘冲错身而过朝书房迈着小步娉婷走去。
就在擦身而过的下一瞬间,一阵淡淡的香味飘过,香味独特而清淡,悠悠滑入鼻翼,便是鼻尖留香,弥留不去。
鼻尖闻到那阵香味,刘冲转头扫了一眼离莺埋头进入书房的娇俏身影,眉头顿时皱紧。吊仙,那是吊仙的味道,离莺的身上为何会有吊仙的香味?
而端着茶壶的离莺半低着头走进书房,捻着小步小声走近桌案,轻声摆了茶具,轻声倒了茶,便离了书房去。濮阳帝在书房处理事务之时无需他人侍候在旁是府里之人都知晓的,是以日常侍女将茶点端到书房后便会自行离去,以免打搅。
而一直低着头没有左右四顾,直到走出书房,方小心地回头看了一眼书房内,视线在低头批折子的濮阳帝身上停顿一下,转头离去。自始至终全然安分守己的侍婢模样。
半晌,濮阳帝方放下手中的笔,后背一靠靠在檀木椅的椅背上,随手端起手边离莺倒好的茶喝下一口。
入口的茶已经凉透了。
濮阳帝一顿,看向书房外,已是残阳如血。
视线一扫,目光定定地停在书房内右方的桌椅上,就那么定定地看着。那是备给到书房与濮阳帝商议事务之人坐的,上好的檀木桌椅静静置在那处,一桌两椅,两椅分置在桌子两旁,桌上是常备的茶具,茶杯为防尘而反扣在桌面上,而濮阳帝似乎看着看着出了神。
好一会儿,却见濮阳帝突然端起他案上的紫砂茶壶朝那桌椅走去。
端着茶壶坐在那处桌子的左手边椅子上,只见他拿起桌上的两只茶杯摆正,分别给两只茶杯倒上茶,将其中一只茶杯移至桌子右方,放下茶壶,端起另一只倒上茶的杯子,朝无人的桌子右方微晃了一下手臂,似乎是敬茶的姿势,嘴角突然勾出一丝温柔的笑意,随后自行饮下了他手中的那杯。
慢慢悠悠饮尽那杯茶,随之又自行倒上了茶,竟是又朝右方无人处敬茶一番,而后饮下杯中的茶。
残阳如血,早前端来上好的茶早已冷透,濮阳帝却似乎饮得愉悦,一直不停的动作好似要将一整壶冷透的茶饮光一般。
在他对面,桌子的右方,分明空无一人,最初始他倒下推过去的的那一杯茶亦安静地停在那处,就那样安静地静置在那处。濮阳帝却一直不停地朝空无一人的那处敬茶,时不时还会伸过手臂让手中的茶杯碰一下那只静置的杯子,每每如此,他的眼神总是温柔得不可思议。
明明是自饮自斟,那模样却好似与什么人饮得尽兴。
残阳暗了下去,暮色渐渐沉下来。
濮阳帝一人仍一人与虚空对饮。
曾记得,那处桌子爻兰绯曾坐过,桌子上的茶具爻兰绯用来饮茶过。那时,爻兰绯在华酒城外伤了左腿,尚未痊愈,回到王府后,第一次来到他的书房来找他。
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