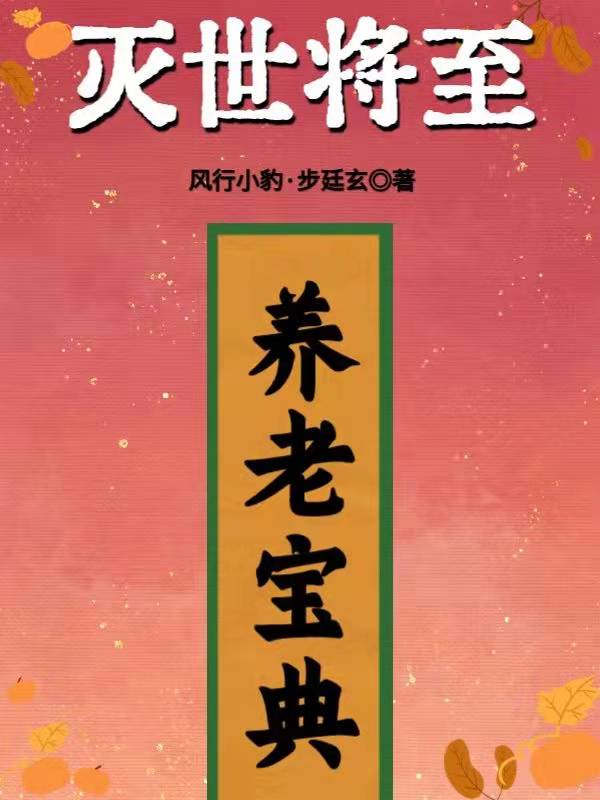最先传到长安的不是霍去病胜利的消息,而是赵信的叛变。解忧二话不说,骑上马背朝城西奔驰而去。
“要么你自己下来,要么我上去接你下来!”解忧站在房梁下,与梁上妇人对峙着。
“我不下去,下去就死了,你走,你快走!”少妇受了惊吓,手里抱着孩子,哆嗦着回答。
寒风入屋,拨动无根乱窜的烛火。
“你逃不了,廷尉的人马已经在路上,他们不会像我这般客气。”解忧不耐烦道。自从赵信叛变的消息传到长安,解忧就马不停蹄赶来,皇帝的诏令下达廷尉府还需时间,她可不想耽误,她要抢在他们逃跑之前找到赵信的家人。
“你走,你也不是好人。”少妇谩骂着,背上箩筐中的孩童似有所动,忽然大哭起来。
“至少我没有背叛大汉,吃里爬外的东西,不得好死!”解忧斜眼瞥着她,她从心底瞧不起这些贪生怕死之辈。
“我不信,打死我也不信,他不会丢下我们母子三人不管。”少妇念叨着摇篮曲哄着孩子,孩童哭声渐弱,似乎真能入睡。
“他本就是匈奴人,匈奴单于伊稚斜封了他右贤王,还把姐姐嫁给他,如今他是风光无限,哪里会管你们的死活?”解忧把前线的消息传给她,她很是反感这等忠贞一世绝无二心的女子,尽管她自己身上也有某种相似的特性。
“你骗人!他不会这样的!”妇人直摇头,流下的眼泪却骗不得人。
“一个为了活命能背叛自己祖宗的狗贼,对我们大汉能有多少忠心?上次我们汉军饶他不死,这厮只会越发爱惜性命,打不过就投降,也是情理之中。”解忧不由得废话起来。
少妇却不依不饶,抵死不下来。二人对峙间,少妇脚下一滑,身子一倾,好容易扶住了廊柱,却顾不得背后的孩子从箩筐中滑下。
眼看孩子落地,少妇一阵惊呼。解忧双脚一蹬,飞奔过去,赶在孩童落地之前以右手接住,却因不及掌握平衡,整个人撞到墙上,左手一阵吃痛,房梁又落下一层灰尘。
“儿子!儿子!”少妇尖叫起来,不知是喜是愁。
“赵信不顾你们母子死活,你还为他如此,他这种人值得什么?”解忧轻拍着因受惊而梦中呓语的孩童轻蔑道。
少妇听不进她一个字,直言道,“我从一开始就跟了他,到最后也会跟着他,没什么值与不值。”
好一个贞烈的女子,可惜了。解忧摇摇头。
“赵信折损我汉军千余人性命,我杀了他的孩子,他也值了。”解忧怀抱着熟睡的孩童一脸邪笑,“当真是稚子无知,死到临头还睡得这么香甜。”
“你?你说什么?”少妇面临再度失去孩子,忍不住哭出声来,“你好歹毒!”
“纵我歹毒又如何?这孩子的性命本就是我救下的,就算立时杀了他也怪不得我。怨只怨他的父亲叫赵信。”那孩子不知为何,竟然适时哭了起来。
烛火“啪”一声爆出一朵火花,妇人惊惶得越发站不稳。“砰”的一声,大批人马破门而入,解忧冷眼瞧着,为首的正是以严酷著称的廷尉张汤。他干瘦的脸上没有半点笑容,颇有几分催命鬼的姿态。此时他环视屋内,对解忧道,“烦请翁主将这孩童交给下官,让下官请这妇人下来。”
少妇一阵惊呼,憔悴的双目布满了血丝。解忧却不理会张汤,反而将孩子单手举起,“你看好了,要么你乖乖走下来,要么我立刻摔死他!”
张汤倒吸一口气,他深知解忧绝对说得出做得到,拱手道,“即便这人犯罪大恶极,也应交由廷尉府审问方可定罪,还请翁主将人犯交给下官。”
解忧依然直直看着少妇,目光凌厉决绝。那妇人终于撑不住,几番挣扎下哭泣着顺着梯子爬下房梁。连同两个孩子,带着对解忧的恨意,她走进廷尉府的囚车。
“你一定很想杀了我吧。”解忧心中这么想着,脸上依然是无动于衷的表情。
“敢问大人,陛下会如何处置这两个孩子?”手中空空的解忧忽然问。
张汤枯瘦的脸上呈现出惊异,那一瞬竟有些看不清眼前的女子,难道心狠手辣的刘解忧动了恻隐之心?他随即拱手道,“以翁主对陛下的了解,他会怎样处置?”
解忧默然。
张汤再次补充道,“这两个孩子尚未成年,按大汉律令,该当没入官府为奴,至于那妇人,相信不必下官说了。”
张汤那发白的胡子在寒风中飘起,待到人犯都押解上了车。他的属官都站在数丈之外,他趁着无人对解忧道,“前些日子有人相继到廷尉府投案,密告淮南王刘安谋反,不知翁主知否?”
解忧一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以不知随口应付过去,由始至终不曾正眼看张汤。
张汤确是眼都不眨一下注视着解忧,他敏锐的嗅觉不会放过任何线索,继续道,“臣曾启奏陛下,淮南王的孙子和幕僚门客先后叛逃来京,事情太过凑巧,只怕有人在背后设计。”
所谓告发淮南王谋反的谋臣们,雷被,伍被,乃至淮南王孙刘建,究竟多少是她的算计,或者说推动?解忧自己也说不清,她自认为只是适时推了一把,让一切在恰当的时刻爆发。
“陛下怎么说?”面对不想来往的廷尉,解忧喜怒不形于色。
张汤道,“陛下说,一切按证据办。”他的声音中势在必得的笃定,不管对谋反的诸侯王,还是别的什么人。
“大人可有证据?”解忧脸上带有一切尽在掌握的笑容。
“翁主所指,是淮南王谋反的证据,还是方才所说那件事?”张汤眼睛里闪着犀利的光,如同野兽见到猎物一般。
解忧冷冷牵起嘴角,“世人传说张大人刑法严酷,最喜罗织罪名来建立自己的功业。以解忧看,张大人凡事讲求公正,一切以法令行事,世人总这般自以为是冤枉了大人。有张大人主持刑律,还怕有人故意陷害淮南王不成?”
解忧负手而立,任凭风霜侵袭着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