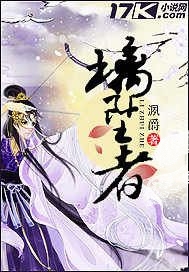天色渐暗,鹅毛般的大雪飘在长安城的每一片砖瓦上。霍去病与青荻乘马车回府。他不喜欢这种慢悠悠的方式,纯粹为迁就青荻。一骑红尘雪中行才是他惯有的畅快。
一路走来长安都是寂静的,多数人躲在屋中围炉赏雪喝酒暖身,少数商旅赶在城门关闭前匆匆进城,溅起一路雪泥。
霍去病掀起帘子催促车夫快些,不经意被一匹快马蹄下飞起的带泥的雪块袭击了。他抖抖落入怀中的污垢,斜着眼心想什么人这般放肆赶在他霍去病面前胡来。这一瞟不要紧,霍去病目光完全随那飞马而去,直到飞马完全错过马车彻底远去。霍去病跳下行驶的马车,尚未站稳便急急朝后望去。
“吱呀!”车夫立即停下。青荻探出头来问他何时。
“没什么,继续赶路。”霍去病跳上马车,思绪却好似被什么东西牵引而去,不时的掀开帘子朝刚刚走过的路望去。
“你见到什么熟悉的人吗?”青荻心跳得厉害。
霍去病矢口否认,“没有。是见到一匹好马。”
青荻想起他刚才心神出窍的瞬间,嘲笑道,“我说霍将军,你什么好马没见过,长安城来了几匹新马只怕都要先到你军中报到去。”
霍去病明知她讥笑他,却道,“那是过去河西被匈奴占据,中土与西域的商路不通。如今我们拿下河西一带,西边的好马商队只会源源不断朝大汉而来。宝马名驹也不再是过去那几种。”
青荻对这些事不大留意,只因霍去病喜欢,便附和道,“难道刚才那匹马连你都没见过?”
霍去病摇摇头,“那匹体格精健且耐力极强,估计是胡马。长安城的胡人商队多起来了,他们固然是为大汉的奇珍异宝而来,但也时常带些我们没有的东西而来。”
以往父亲与哥哥提起塞外胡人总是一副幽怨不满,他们常年在边关被匈奴欺侮惯了。而霍去病好似不计前嫌,对这些一概报以友好接纳的态度。如今陛下厚遇投降而来的匈奴人和为商贸而来的胡人,亲眷中贵戚不少,对此颇有些微词。而霍去病竟然想得这般高远,她对自己的丈夫又添了一分敬重。
其实霍去病没看错,那骑马之人正是解忧。她已悄悄回到长安,除了跟刘彻汇报过,跟其他人都没有来往。连时常进宫探望父母的卫长也毫不知晓。
如此相安无事过了个把月,解忧才去陪刘彻下了一盘棋。
“回乡祭过祖了?”刘彻这是明知故问,解忧即便暗中算计了他,也会把面上做到滴水不漏。
解忧说道,“拜过父母和先祖了。”
“你伯父楚王身体怎样?”刘彻漫不经心问道。
解忧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没见到他,不知道。”
刘彻嘴一抿,知道她又没按他的意思去办。解忧却不等他询问,不打自招道,“我回去是拜祭故人,他又没死,有什么可见的?”
刘彻知道这个孩子死心眼,说道,“叫你回乡祭祖是跟楚国的亲戚们熟悉一番,你却只顾着拜祭,你这样不动声色有谁知道你做过什么?”
我就是要不动声色让你不知道我做过什么。她这样想着说道,“祭拜过就是祭拜过,黄土里埋着的那几个人自然知道。”
刘彻却道,“这就是你太年轻了,有些事还不懂。祭祖祭的是死人,却是做给活人看的。你不三跪九叩行大礼哭天抹泪,别人怎么知道你诚心不诚心。”
解忧抓了一把棋子握在手心,“我不在乎。”
刘彻正欲出言教训一番,却听宫人来报,“隆虑公主又来了。”
一个“又”字表现出连宫人都不耐烦了。解忧吐吐舌头,一脸嫌弃样。刘彻重重看了她两眼,示意她不可乱说话。这意味着她可以旁听,解忧竭力控制自己的心跳,生怕这小小心跳声足以令地动山摇暴露她的心虚。
这隆虑公主一进来就抹起眼泪,来来回回说着那几句话求陛下开恩。刘彻本已十分厌恶陈家的人,看在亲姐姐的面上没对这家过多处罚,可隆虑公主却不答应,“皇上你开恩吧,削了他的爵位等于治了他的死罪呀,这叫他以后如何在亲戚中有脸做人呀?”
有脸做人?他昭平君何时做过顾及脸面的事情?你隆虑前来哭诉不就是怕夷安的婚事黄了吗?列侯可以尚主,多大的荣耀,我的女儿嫁给你儿子还委屈呢。刘彻被她哭得心里慌乱,又想到姐姐当年的如花容颜因嫁给一户不堪的亲眷硬生生被折磨成黄脸婆,心生怜惜道,“姐姐不必难过,大汉有大汉的律法,如若因为朕的亲戚而轻易宽恕了他,反倒令朝臣们心生不满以为朕有心偏袒,往后只怕越发严待他。朕这么做是为他好。”
隆虑公主却说道,“姐姐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自从生下他就百般疼爱,不曾叫他受一点委屈。他虽然平时有些任性,心地却是最良善的,对皇帝您忠心耿耿,对夷安公主敬重爱护。可这次,他在廷尉府的大牢里整整住了一个月。您还不满意,还要削了他的爵位,取消他的婚事,这叫姐姐如何在陈家人面前交代?”
这位隆虑公主真该跟平阳公主学学如何说话,一个母亲生的孩子,言行措词的差距怎那么大呢?又或者近朱者赤,她跟那行为不端淫乱不堪的陈家人相处久了,人也变得粗鄙起来。您那宝贝儿子纵横长安的罪行谁人不知呀?刘彻不忍戳破姐姐颜面,只好继续安慰。
隆虑公主索性撒泼起来,“我儿子好心收留那个剑客,剑客却坑害我儿子,真是禽兽。朝中这些臣子没一个好东西,往常哪个不是对我们礼遇有加,如今见了我们就躲!”
一旁服侍的宫监都听不下去了,眼看这隆虑公主从陈家祖上说起,把他家那点芝麻大的功劳夸到天上去,好似要把开国的功勋之臣们统统踩到脚底。宫监鄙夷的望了一眼,又看了看解忧。解忧一贯鄙视这些仗着权位身份行为不自律的皇亲,平素口舌之斗也毫不给他们脸面,这虾子这么好一个落井下石的机会怎么连一句话一声嘲讽都没有?
解忧心里却想着,尽管骂吧,恶毒的骂吧,骂得越多她心里的不安越少,昭平君是咎由自取。她不知的是,这昭平君平素惹事太多,斗鸡打猎喝酒时得罪人无数,好容易犯了个能治大罪的事,正义的长安人岂能放过?还不好好收集罪证,把他往年做的零零碎碎的错事譬如砸了谁家的店铺毁了谁家的农田非礼了谁家的姑娘一齐上奏?解忧不知道,她只想毁了这段婚约,长安人可是想要昭平君性命呀。掺和进这件事的朝臣有张汤,张汤平素的对头,甚至还有卫家人,人们头一次这样齐心协力要治一个恶徒的死罪。
好不容易等隆虑公主哭累了,刘彻也听累了,命人把隆虑公主搀扶出去。不过隆虑的言行却叫他下了一个决心。
“你去看过夷安吗?”刘彻问道,这话是对解忧说的。
解忧支吾道,“没去。”
刘彻没了下棋的心思,道,“也不知道她这几天怎样了,自己的夫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宫里人前人后言语不大好听。还以为你会去安慰她呢。”
解忧心中冷笑,安慰?只怕她快活的快要飞上天去了。嘴上却慢条斯理说道,“夷安的心事我不大懂了。”
刘彻却笑,“解忧也知道自己的无能为力了呀。”
解忧暗想,她心里喜欢谁你比我清楚着呢。早早将她的亲事定下,真不知是误了谁的终身。不过她该庆幸刘彻没有如夷安的心愿,也该庆幸青荻被霍去病喜欢上,不然她往后还不知怎样跟夷安见面呢。
这盘棋终究没有下完,不过也不必继续,棋力再差的人也该看出志在必得的刘解忧很快会击败心烦意乱的刘彻。当然刘彻不会认输,“棋还没下完,看不出胜负,朕改日再与你对弈。”
他命人把棋盘原原本本移走,解忧随即告退。不知为什么,她心底有一股不安,好像棋局未完一切总有变数。
她带着这种不安的心情一路走下去,却完全没注意到一个俊俏的身影偷偷靠近了她。
“解忧!”背后传来的叫声险些把她惊得灵魂出鞘。
“我的天哪!你吓死我了。”解忧拍着胸脯啐道。
夷安手中执一根狗尾草,喜笑颜开道,“我都不知道你这么胆小。不就是忽然叫了一声嘛,我脚步也不轻,还以为你听到了。”
解忧轻声说道,“瞧你高兴的样子,陛下跟我说起你的婚事,还怕你心里难过呢。”
“有什么好难过?我高兴来不及呢。谁要嫁给那个废物了,只会给我们刘家蒙羞。”她神采飞扬,前所未有开心着。她完全没想到挣脱了这段婚事能这般开心。
解忧摇摇头,心想能保住她这一点纯真之心也好。
“我还要多谢你呢,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夷安话没说完就被解忧捂住嘴。她摁着夷安肩膀道,“千万别说,以后也别说,这件事只能烂在你我肚子里。一旦被人知晓,你和我都会陷入万劫不复。”
她不是威胁,也没有刻意夸大后果。显然解忧从刘彻眼中看到解除婚约的决心,他正在盛怒之中。但他此刻对昭平君有多少不满,也意味着真相揭开时对解忧会有多少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