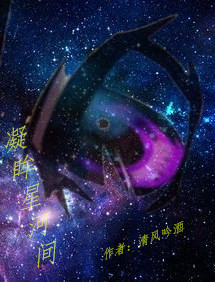“那漫天的弓箭像雨点一样密集哗啦啦落下,把马车活生生钉成了靶子。尸体堆积了一地,眨眼的功夫就把落羊小道填满了,胡虏的马匹迈不过去,那些匈奴人就各自下了马,可死尸堆了一地呀,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尸体一堆一堆的,匈奴人眼看没有他们要找的人,只好离去了。可这却难倒了给他们收尸的人,乌溜溜堆了一地的尸体已经发臭发胀了。于是他们在尸体堆里刨呀刨呀,愣是没有找到解忧翁主的尸首,长公主你说神奇不神奇?”每每说到这里,主仆二人总是捧腹大笑,好不痛快。
原本这甘泉宫受了匈奴奇袭是大汉朝的一桩苦事,刘彻这个帝王似乎觉得难为情,故而每每想起皆略过不提,外朝内宫诸人也装作全然没这回事。但对于卫长而言,这确是一桩大大的好事,她的心腹大患她假象中的情敌刘解忧终于一命呜呼见高祖皇帝去了。
自事发到今天已过去了半月有余,解忧的尸骨仍未被发现,而生还希望却越来越渺茫。寻找尸首的人回来禀报,翁主的尸首怕是跌入悬崖,或被野狼叼走,或入秃鹫腹中。解忧的死亡似乎已成定局,她昔日在宫中朝廷内外结下的仇敌无数,但在陛下郁郁寡欢的情形下敢这般大张旗鼓兴高采烈庆祝的唯有卫长公主一人而已。
因为无一人生还,汉军侍卫们对抗匈奴军队的惨烈景象已不得而知,但好事者具备超凡的捕风捉影能力,依旧能从收尸的人口中打听到不少有关尸身伤痕的描述。卫长公主是最高调的好事者。
这些天以来,她把别人口中的只言片语连同自己的想象结合,与侍女一起绘声绘色讲述着。一时间,平阳侯府把这些当成最重要的事。
想起解忧过往如何气焰嚣张如何仗势欺人,她大感酣畅淋漓,不禁问起侍女,“你说除了我,还有谁在家中偷偷庆祝呢?”
侍女想了想,奉承道,“其他人即便心里欢喜也断然不敢说出来,唯恐伤到陛下的痛处。”
卫长嗤笑道,“我就讨厌那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明明心中得意偏要装出悲悯之心。听说朝臣们要为那些牺牲的侍卫立忠烈祠,还有不识相的宗室说要把解忧和那个衡玑供奉起来。”
侍女说道,“可是陛下并没有应允。”
卫长公主摇摇头,“你并不了解我的父皇。没见到解忧尸首,他心底还存了一丝念头,指望她能死里逃生。其实所有人都明白,她怎么可能还活着?我父皇生怕一旦允诺了,事情盖棺定论,这一丝念头也断了。”
一个颀长的影子映在窗棂,眼尖的侍女推搡了下振振有词的长公主,示意曹襄正阴沉着脸从窗外经过。
“哼!就知道他还在为那个死人伤心,”卫长气不打一处来,说着立马起身朝屋外走去,挡在曹襄面前道,“人都死了好些时候了,你难过什么?你为她伤心欲绝,她临死前可未必想过你。”
“够了,人都殁了,你还说什么。”曹襄这些日子有些魂不守舍,有意避开妻子,不想跟她斗气。
“对呀,人都殁了,你还想什么?”卫长按原话顶回去。
曹襄苦着脸,为后半生都得对着妻子而感到无奈,“我说人都不在了,你有再大的怨气也该消褪了吧。解忧活着的时候你对她没有半点好,现在都去了,你就别幸灾乐祸了。”
“你说我对她不好?我哪里对她不好了?”卫长嗓音尖锐刺耳,“你给我说清楚!她住到宫里,那是我的家。她吃的穿的都是我家的,她临走前还把情敌交给我照管,你倒是说说,我哪里对她不好了?”
“对,就你好,旁人皆坏。”曹襄无可奈何。
卫长继续刺激他道,“你以为你做出这幅食不甘味的样子给谁看呢?想跟人说你有多念旧多痴情是吧?比起于单你可差远了,他那才是……只是可惜了……”
听到这里他更是愤怒,大袖一挥踱步而去,“真不知道你干嘛跟死人计较。”
卫长公主心中不忿,“我干嘛跟一个死人计较?就凭她死了还占着你的心我就要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