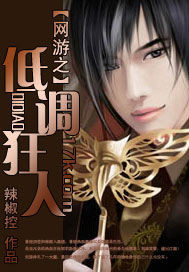月明星稀,无风之夜。解忧独自来到南墙之下,随手执起尖石在宫墙下胡乱凿起来。
墙角气息不顺,格外闷热,她一个人忙了片刻,已是满头大汗。解忧把随身之物丢进土坑里,复又重新填上泥土。她对着无望的月轮,心中默许道:如若上天有灵,他年有人来此挖出解忧之物,也不枉费我来这世上走一趟。
“翁主,一切准备就绪,该启程了。”身后忽然有沉闷的人声传来,解忧悚然回头,只见陛下的随身禁卫已整好队列。
领头的侍卫她认得,他原是与霍去病同一批的侍中郎,他们一个征战疆场,一个伴君出入,誓死效忠陛下。与许多人相比,一身正气而不张扬的他才是真正的贵族。
他今夜的声音低沉沙哑,已无半点天子侍中的朝气蓬勃,但目意坚决,显然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解忧明白,这支队伍的每个人都很年轻,他们这一去绝无可能活着回来,心甘情愿以一己之死换取大汉江山的平安。解忧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曾说过话,那时她太张扬太狂妄,还不懂如何掩饰锋芒。可今天,只要一句话,他们竟可无言将生命托付,视死如归。
而她刘解忧甚至比他们更悲哀。他们死后会以烈士的名义被永远贡入忠烈祠,他们此生的荣光将一直伴随他们的种姓宗族延续下去。而解忧只能在无名的乱葬岗上,草草留下一抹晦暗的痕迹。解忧忽然很瞧不起自己,难道她后悔了?
“立即出发。”解忧一声令下,所有人迅速集结在天子车架周围。甘泉山上夜风骤起,宫灯摇曳,偶有不知情的宫人路过远远侧目而视。
解忧登上马车,掀开车帘,只见衡玑已妥妥定在车内,如老树苍松般。
见到她衣袍沾上的泥土,衡玑问,“你去哪里了?”
“埋葬一些东西,纪念。”千钧一发的时刻,每个人说话都尽量简短。
“纪念什么?”衡玑不解。
解忧转过身去,面对未知的夜色,怆然道,“我曾来过这世间,爱过一个人。”
“护驾”的队伍集结在行宫的石阶下方,行宫内灯火逐渐熄灭,不知内里的人如野草般立于山巅石壁,茫然目视他们——他显然毫不知情。
刘解忧倚在车壁上,悄悄目送毫不知情的于单离去,她心里忽然泛起一丝苦涩,希望他将来能遇到真正的好女子。
这只被视作诱饵的队伍按计划穿行在山岭黑夜中,放眼望去看不到一丝生机。未点燃火把的他们不禁担忧匈奴是否中计。解忧却深信不疑,她的直觉从未如此准确,这是她宿命的债,本应由她去偿还。
“你此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马车行在乱石无数的山路上不断颠簸着,衡玑忽然问她。
解忧目不斜视,“死的时候,有亲人在身边。”
“为什么?”
“因为活到今天也不曾有过。你呢?”
衡玑隐约苦笑,“归葬故里,不做孤魂野鬼。”
解忧默然,所谓心愿未必都能实现。
“前面就是落羊涧。”驾车的侍卫沉声提醒她们。
“可有岔路?”解忧掀开帘子探着,然而前方黑洞洞一片,只有零星的星光勉强照亮道路。
“正是。”
确信了岔道与地图上描绘的一致,解忧悄然抛下一物于路旁,无比淡定目视逃生的道路离自己越来越远。
如此行了大半夜,眼睁睁望着甘泉山远去。混乱的马蹄声却由远及近,如慌乱的鼓点落在他们心上。陆续有略带胡音的汉语传来,频频喝他们停下。
想要兵不血刃活捉他们?大汉的军士们加快挥动手中的马鞭。无数箭镞如雨点般落下,车前的护卫不待言明将解忧推进车里。厮杀声从队伍最后传来,这注定是没有余地的牺牲。位于马队末端的侍卫成为刀下亡魂,随后是仅次于末端的……
那些年轻的飞扬的生命消逝在风中,箭镞终于落到马车上,险些戳穿这最后一层屏障。解忧对衡玑苍然一笑,投身于战斗。
“翁主保重。”驾车的侍卫将缰绳交予她手中,转身跳上刚刚失去主人的战马。
解忧明白,相视一笑间已跃过不少距离,横飞的血肉在眼角瞟过。她生命中头一次意识到生命的消逝如斯惨烈,这或许就是对她漠视苍生的十年岁月最沉痛的惩罚。
“嘶。”解忧肩部一痛,该来的终于来了。顾不得伤口,她以短剑刺入马匹股部,“求你了,求你了,再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