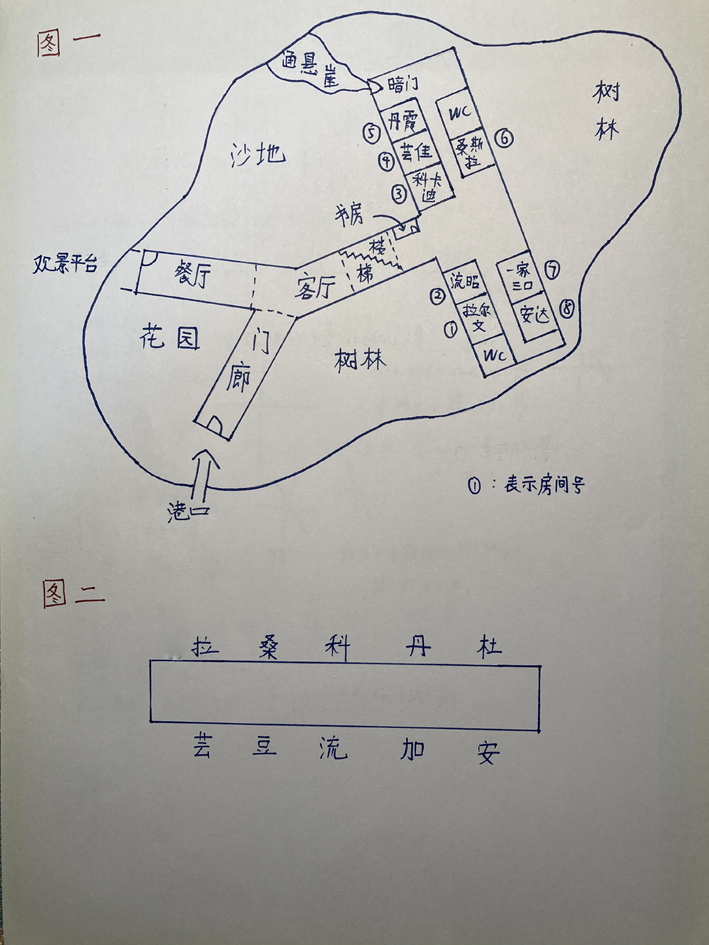暑气颇盛,青荻独自坐在车中闷得慌。她悄然掀开马车左侧帘子,热门袭来,空气虽不那么沉闷,却被热风吹得出了一阵汗。她连忙放下帘子,安心等马车驶过繁华的大街,缓缓来到宫门前。
“到宫门了,请姑娘下车。”守宫门的侍卫依礼请她下车,移步宫中。
内宫宦者在前领路,青荻紧跟其后,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这不是她头一回来宫中,先前那次太匆忙,她在城楼目送霍去病大军开拔后出乎意料被皇后请进宫门,毫无准备之下就与宫眷及亲贵一同用膳,当真失了礼数。那次之后,尽管偶有女子酸溜溜在背后说些不干不净的话,但卫氏的一干亲族异乎寻常重视她的存在,连皇后也常在佳节时派人上门探望,不时暗示她多在宫廷与亲族中走动。这是出于对她的重视还是对霍去病的重视?她不愿多想,安安分分守在冠军后府过着无忧无虑的太平日子。她出自军功世家,心底多少明白,不招惹是非的家眷对远征在外的人们意味着什么。
“姑娘请稍等,容我去禀报皇后。”踱到椒房殿的石阶之下,她点点头,对那些对她报以好奇心的宫女们频频微笑。都知道她是霍府的人,她可不想让霍去病蒙羞。
一阵风过,竟是令人畅快的丝丝清凉之意,还夹杂着桃花的馨香。青荻举目望去,四周树木葱郁,但显然已过了桃花盛开的季节。
正兀自思量着,已有宫女从殿中出来,请她进去。
青荻微笑,小步趋行,按大礼拜过皇后,“皇后长乐未央。”
皇后对她似已十分熟悉,对大礼不以为意,反倒热情的招呼她过来坐。卫子夫虽出身寒微,却不似其他得了势的夫人那般喜好对身边施点小恩德然后欣赏他们感激涕零的样子。当年母亲为奴落魄时也照样拿自己当人,如今她一步登天也照样宽以待人。
青荻不便拂皇后之意,便在宫女的指引下坐到皇后对面。只见皇后面前摆着一盘棋,稀稀落落落着几个子,此时她正一手白子一手黑子琢磨着什么。
“也不知这黑一片白一片有什么意思,陛下每每见臣子总要好好对弈一番。”皇后边说边笑,却似乎只在取笑自己。
青荻略瞟一眼棋盘,她的子都落在棋盘中央,并非对弈之举,大概只是闲着无趣摆着玩,便说道,“我也不知下棋有什么好玩的,值得两个人从早到晚光盯着棋子一言不发。”其实她知道这围棋是上古五帝中的尧帝为管教儿子朱丹而造。棋盘虽小,但这里包含了治理百姓、军队、山河的道理,可惜朱丹并没有听从尧帝的教导。后来尧帝把地位禅让给虞舜,虞舜也用这棋子教导商均。弈棋之术岁流传多年,但大汉精通棋艺之人并不多。
青荻环顾四周,大殿四角均摆设着铜盆,内置寒冰,以驱热气。她忽而想起从前独自居住山林间时,即便盛夏处暑时节也清凉如初春。
她目光不经意移至棋盘旁边的铜尊酒壶,略带花香的酒气缓缓袭来,暖暖醉着人心。原来在这里,青荻浅浅一笑。
“你喜欢桃花酒吗?”皇后见她目有笑意,顺势问道。
青荻实话说道,“在家时父母不让我饮酒,后来,后来也不曾引过。”
“这是宫中特意为公主出嫁酿造的桃花酒,取其桃之夭夭吉祥之意,喝了也不醉人。”
宫女为她们把盏。淡红色的桃花酒清泠泠注入酒盏中,映着女子碧色的宫装,更显娇艳动人。
青荻小心翼翼浅尝一口,酒入樱唇,顿觉浓香扑鼻,更甚方才。而酒的功效也在毫无酒力的她那如花似玉的脸庞上逐渐显现:只见她脸颊泛起淡淡一层粉色红晕,令她那如冰雪般莹白的肌肤更多了几分娇媚。
“滋味如何?”皇后轻声问道,似怕惊扰了她那淡淡的醉意。
“很好。”青荻回答。
皇后一笑,也不计较,反倒侃侃而谈起来,“春天开花时我命人采摘了晾干,前几日我的宫女面上长出黄褐色斑点,羞于见人,几日躲着不敢出门,医女用桃花配了白芷,浸泡在酒里,二七十四天后启封,以酒抹匀揉搓面部,几日后斑点尽去,肤色更甚于从前。”
“从前在家时,我常采撷收集各种花瓣。这桃花,该取无垢且花瓣丰腴者,不过对桃花的医药之用便不得而知了。”青荻自谦道。
皇后说道,“我懂什么医理呀,这都是解忧说的。”她注意到青荻双眸不自觉睁大了些,继续说道,“她说桃花能活血化瘀止痛,于女子肌肤大大有益,若你时常服用,定能使面色红润皮肤光洁。”
“她可真有学识,”青荻低头略想片刻,转而抬头笑道,“我想宫里人定然很喜欢她吧。”
她这一说不要紧,忽听背后“喵”的一声叫声,一只全身溜黑毛色晶亮的猫从她肩头跃了过去,直接落在她们面前的酒樽上,溅了青荻半身。
“这畜生,真不听话。”皇后蹙眉,微微动怒道,同时命宫女收拾几案,为青荻拭去酒滞。
宫女们纷纷忙碌起来,那只引起骚动的猫反倒蜷缩到一旁自顾自舔着毛发躲安逸去了。
“我看你这衣衫沾上了桃花酒色,不如换一身去。”皇后建议道。
青荻本愿推辞,却架不住皇后盛情,便往偏殿换了一身宫装。
本想借机把话题引到解忧身上,不想被一只猫坏了好事。青荻有些泄气,只得眼睁睁看着宫女把自己来时所着衣衫送下去。
待青荻换了衣衫归来,只见皇后似凝神细想了许久,“刚才你说解忧?”
她不隐瞒自己的心思,诚恳的点头。
“你以为解忧是怎么样的人?”皇后笑着问她,如同安慰自家受了委屈的孩子。
青荻摇头,诚然道,“我好像完全看不懂她,她高兴的时候,任凭别人怎样都能够容忍,但一旦不悦,好似谁都亏欠了她全都退避三舍不敢招惹她。”
“我也未必懂她,”皇后的回答令她有些诧异,她指了指墙角,“她就像那只猫,独来独往,言行举止都按自己的步调,永远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很难被旁人影响。高兴时或可迁就旁人,但若有人要把自己的行为方式强加于她身上,只会招致剧烈反抗。”
她们正说着,那只猫嚎了一声便从窗户跳出去了。
“也因为这样,即便这只猫是使臣所献,我也不怎么宠着它。”她不动声色吩咐宫女道,“去把那猫抓回来,把爪子剪去。”
青荻一惊,反倒有些同情,“那猫刚才并未伤着我,若因此被剪去了爪子,只怕它日后行动不便,若是因此受伤……”
话音未落,只听见皇后说道,“我若一味纵容,只会叫它有恃无恐恃宠而骄乱了宫里的礼仪。所以呀,这外来的猫虽看着新鲜终不如我们自家的好。”
说到“自家的”这几个字时,皇后有意无意的拍了拍青荻的手。
黄昏将至,青荻借晚风大易受凉为由告辞。出了椒房殿门,只见那只受伤的猫正可怜兮兮舔着已无利器的猫爪。因宫监的催促,她没逗留一会儿,就朝宫门走去。一步一步,越来越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