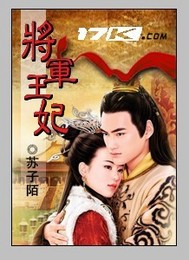这是汉地的元狩二年开春时节,然而匈奴没有自己的四季,他们根据汉地的春种秋收决定骑兵抢掠的时机。
扫除帐子外积了数月的皑皑白雪,于单开辟了一条窄道。
熬过漫漫严冬,匈奴人去年抢掠而来的粮食尚未助他们耐过春季已基本被食用殆尽,不少年迈被军队弃置的老者在饥寒交迫中缓缓死去。于单的日子也不太好过,除了偶尔能猎食的野味,他过着清苦的如苦行般的生活。
“王廷的日子不大好过,于单王子不如去打些猎物。”一旁放牧的老者对于单唤道。他是军臣单于时期的老臣,年富力强之时也曾在骑兵中有一席之地,但如今老迈且重伤未痊愈的身躯已不堪军队的驱使,于是早早退下来,以放牧求几餐温饱。
“不去了,多谢大叔好意。”于单笑的时候咧开嘴露出一排洁净的白牙,或许是远离了兵戈的缘故,他比其他匈奴人看上去更斯文更懂礼数。被剥夺了用兵的权利之后,对他来说连杀戮都陌生起来。
不过他的收敛总会令人想起那有着汉朝皇帝血统的生母和本应属于他的单于之位,老者摇摇头,不禁为他可惜。
“大叔又在叹什么气?是在想念远征的儿子了吧!”于单朗声问道,这里四下无人旷野开阔,隔着数丈远若不放声吼根本听不见。
老者继续摇头,愁绪涌上眉心,目光不由得悠悠飘向远方:汉匈之间新的战争又要打响了,儿子能平安回来吗?
于单却不解他的忧虑,好心安慰道,“大叔您放心,您的儿子定会为你掠来牛羊马匹丝绸珠玉。”嘴上虽这么说,心中却不大乐意:明明可以用牛羊马匹换来的东西,却非要用手足鲜血去换取,值得吗?更何况他身上流着两个民族的血,他是匈奴人,亦是汉人。若在平时,他定然回避这样的事实,但此刻,真相如同母亲妆镜台上的古镜,越擦拭越明晰。不可否认,远在茫茫天涯的那个女子或多或少改变了他的人生。
“唉。”大叔叹叹气,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把从月氏人手中夺取的肥沃土地双手奉送给汉朝人,这一战,能赢吗?
“大叔您歇着,我去去就回。”于单驭马而去。
一夜寒风呼啸,已在坟茔上洋洋洒洒落下大片大片的雪花,盖在青灰黑色的冻土上。
“玦,我来看你。”于单下马,缓缓来到墓前。脚印踏碎积雪,也化开内心深处的疤。
这是他自去年起闲暇时常来的地方,如固有的习惯般融入他生活的细节点滴。在旁人看来,他们的于单王子多少有些过于痴情,在对生育无比重视的匈奴,多数人前脚死了妻子后脚立即寻思着再娶,他这样的伤怀显得过于不合时宜。
然而于单早知如何回避别人探究的目光。母亲坚持把“刘玦”葬入此处时他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王廷走丢一个汉女哪里值得这般掩人耳目,她完全可能在天寒地冻里死去进而尸骨无存。母亲欲盖弥彰的掩饰更让他确信刘玦身份可疑,却因母亲固守秘密不得知悉真相。
于单回忆了与她相处的每一个细节,依然觉得她的到来是昆仑神的安排,来为他灰暗的毫无指望的囚徒生涯描绘上色彩斑斓的富有冒险意义的一笔。
如今看来,这座空坟没能埋葬他的刘玦,却有幸成为他思念她时最好的去处。旁人只当于单王子终日碌碌无为在顾影自怜中消磨了锐气,他得以保全自己的平安。母亲的决定,从来都有道理。
这一天,他如往常一样由墓地回到帐子,却呼吸到不同寻常的仓惶的充满血腥与阴谋的气息。整个王廷乱作一团,战争失败的阴霾笼罩着权力中心。
“苍狼俘虏了我大匈奴数万人马,我要掘了他们汉人的祖坟!”伊稚斜愤怒的将皮鞭挥向帐外,穹庐大帐里悄然而立的大大小小部落王通通无言以对,各怀心事苦苦等待着单于的处置。苍狼是他们对汉军统帅霍去病的称呼,河西一战,这个血战胜出的弱冠少年已名声大震,他不再是卫青的外甥了。
当人们以为掘坟只是一时的气话时他们可大大低估了单于的愤怒,他将目光投向荒郊那数不尽的土包沙丘——埋葬着历代和亲陪嫁汉人的乱坟。
“汉人相信祖坟的风水可以庇护子孙的平安乃至成全他们的荣华富贵,莫不是王廷附近埋葬了太多汉人,乃至压制了我大匈奴的气魄?”如鬼魅一般的匈奴军师中行説不失时宜的向伊稚斜灌输汉人的祖坟论调,不论是出自对汉朝的私仇,还是眼下匈奴军队失去的信心,他都必须将掘坟之事进行到底。
于是,掘坟这一荒诞无稽的行为很快得到匈奴决策层集体的通过,在无视清河阏氏激烈的反对之后,中行説与巫师选定日期,王廷召集了左右谷蠡王左右贤王等一系列重要或不重要人物,在巫师一些列的阵势下开始了这一救赎匈奴人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