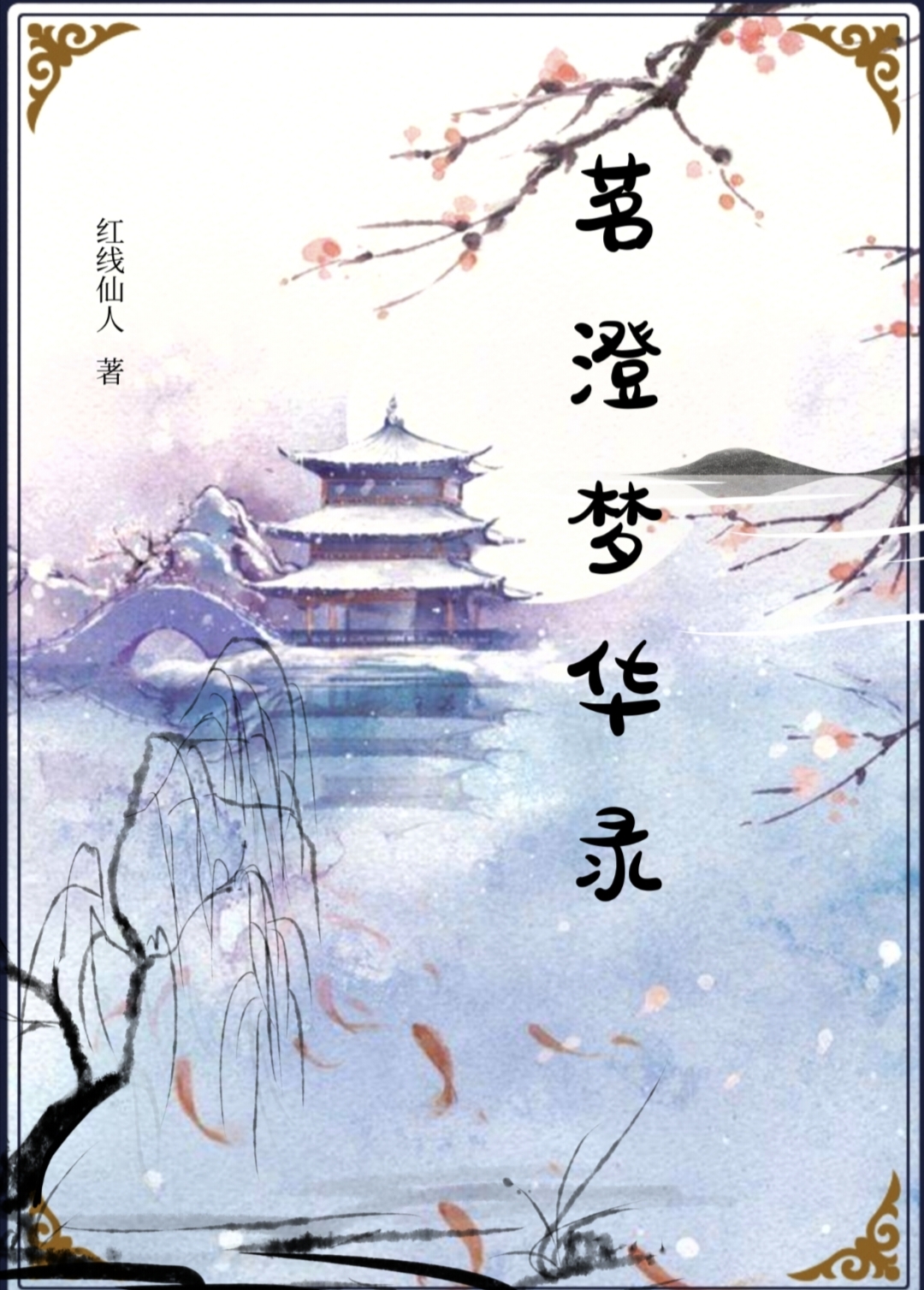房明忠一直认为,是我的出现引发了这一切,是我将晓忠害了。可是他又不得不对我客气,因为他的儿子房晓忠——非要跟我理不清。
十一月了,北京该有些冷了吧?我从衣柜里抽出两件外套,看了一会,扔在床上,又接着翻衣柜——穿什么去呢?裙子?裤子?还是裤子吧,带一双靴子、两双?或者到了那里再买?去燕莎?或者去西单淘?算了,那里的人多死,我也懒得淘。
我洗过澡了,穿着睡裙,一边整理衣服,一边朝正在书桌前做作业的想念说道:“想念,你要我给你带什么礼物吗?你想要什么?衣服还是裤子?鞋子?”他不去,我总不能一点东西都不带回来吧?也太没良心了。
他应道:“不用。”
“那要带北京的小吃吗?”我继续收拾,想了想,跑进浴室,把我的护肤用品拿出来。
他还是那句话:“不用。”他关了台灯,合上他的电脑,走过来帮我收拾东西。
他的手比我巧,很快就将我的一摞东西都收进去了,合上箱子。我坐在床上看着,用脚趾头去勾他的衣角:“想念,真的不要和我一起去吗?”装模作样地再怂恿一下他,别搞得好像我真是去偷情的。和房晓忠偷情?怎么可能?房晓忠那个妖魔,谁知道他对女人有没有兴趣?
我和他,再纯洁不过了。
他抓住我的脚踝,阻止我这样玩,没什么表情:“不去——反正你有人陪,我去干什么?”
这口气,有点怪怪的,我撅嘴:“我和晓忠又不是什么男女关系。”房晓忠那个奇怪的人,他和我,没更多的关系。
崇想念松手,往浴室走去:“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你和他——我洗澡去了。”
哟哟,这奇怪的口气,是在玩吃醋吗?吃醋,吃什么醋,我和他的感情还没深到某种程度吧?充其量,也不过是我们俩一时情动,做了一些亲密的行为罢了。我倒不是在乎他怎么想,而是不喜欢他那样的口气,怪里怪气的,像是我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傅兰兰,唯一见不得人的事,也就是和傅云翔。对于我来说,是好是坏、是高雅是放-荡,我都不需要掩饰。
该是怎样的人,就是怎样的人。
可是——想念,他真的生气了吗?我叹气,女人心还真是善变,前一秒钟我还在想着不在乎他怎样怎样,下一秒钟我已经开始担心他是不是真的生气了。其实,我真的不太懂想念对我有怎样的感情,有时候我觉得他不过是因为我有接近他的机会,所以他才会接受我。和我接吻、上-床,从一开始,就是我在主动,虽然上-床那事不是我先提出的,但也算是我先勾引了他。
所以,我总觉得其实他对我的喜欢也不过是五六分吧?想念这个人,有时候你真的看不透他。
叹气,我关了房间里的灯,先上床睡觉了。大概真是困了,躺了一会就已经开始迷糊。也不知过了多久,身边有人躺了下来,我翻了个身,背对着他继续睡。
睡裙被撩起了,手指不安分了。我睡得正好,不想动:“别……困。”
我被重重地压住了,趴在床上动弹不得,几乎要窒息。我一下子清醒了七八分,侧过头想要抗议:“干嘛?好重……”
我咬住唇——想念这么突然,这么用力,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他在咬我的肩膀,声音沙哑:“你说,你是不是喜欢房晓忠?”
我呜咽起来,辩解:“不是,我和他,没有。”我不缺男人,晓忠不想要女人,就这么简单。
“真的没有?真的?”一遍遍地追问,崇想念像变了个人,他成为了野兽。他扣住我的肩膀,要把我揉碎。
“没有……你轻点。”我咬着唇。
他根本不打算听我的,从那一次开始,他已经学会了在造爱的时候占上风,将我一点点掌控。到底谁才是络新妇?到底是谁在蚕食谁?
他将我翻转过来,挥汗如雨,我也渐入佳境。渐渐的,身体变了,我与他十指紧扣,动静越来越大,我的脑中出现了空白——我居然从他那里得到了曾经与傅云翔才拥有的享受。
想念在我耳边诱-惑我:“阿兰,我能给你,我都能给你,我们——永远在一起。”
我们同时叫出声,相拥在一起。末了,他趴在我身上休息,又变成了那个可爱的小正太,抱紧我像是害怕我的消失。我亲吻他的脸蛋,低声安慰他:“想念,你相信我,我和晓忠真的只是朋友。”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安慰他,但是——我喜欢他对我这样唯一的感情——应该是唯一的吧?他,没有其他的女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