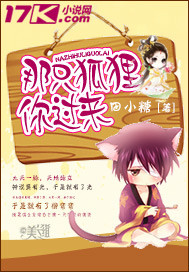夜晚已经开始冷了,我批了披肩,和朵朵在夜里的石板路上走着。山路弯弯,一路上去,有不少亮灯的铺子,里头大都是卖一些土布,上头染了些许花色,吸引城里好奇的游客们。
我们都喝了酒,喝的还不少,一时间,两人走起路来有些弯弯绕绕了,差点撞到人。我趁着脑袋还有些清醒,拉了朵朵往回走:“回去了回去了,再走下去,就要睡在路上了。”
朵朵笑着:“睡在路上还没什么,就怕一不小心脚一滑,真要滚下山去,谁也救不了。”
两人一路嬉闹着回到了旅社,我已经有些头重脚轻了,等到了房门前,差点打不开门——咦?是谁?怎么,又觉得有人在看着我?双眼朦胧地扫了周遭一眼,我进入房间,反手锁上门,一头栽倒在床上睡了。
好冷呢,我往被子里缩,一只手在我的脸上轻抚,下滑到我的脖子那里——
嗯……不舒服,这手要干嘛?为什么卡住了我的喉咙?我有些窒息。
脖子上一松,我得以恢复了正常的呼吸,渐渐睡去。
梦里,有傅云翔,他给我擦脸,擦身子,喂我喝下温水,真好。我转过身,抱住温暖的他,沉沉睡去。真想睡个天昏地暗,再不要醒来,傅云翔,我爱他的怀抱。
米酒虽醉人,却不会在第二天让你感觉头痛,我睁开眼,还不太清醒——
哎?这是?这温暖的人——我愣愣地看着就躺在我身边的傅云翔,他怎么来了?那么,昨晚的一切都不是梦了?
“这么看着我干嘛?”傅云翔睁开眼,看着我笑,“很吃惊吗?”
我也笑了,抱住他:“哥,你怎么来了?”
他亲吻我的额头,很温柔:“我当然要来,有个坏孩子不知道在想什么,一声不吭离开了广州,还不接我的电话,不让我找她。我只好通过锁定坏孩子的手机所在地,又匆匆请了假,来把她接回去。”
我往他怀里钻,笑呵呵:“我想一个人静静嘛!我知道你能找到我,我不担心。”
“你是不担心,我可要担心的,又不敢打搅你,只能等你玩够了才出现。”他狠狠一吻我。
我推开他,笑:“难怪我老觉得这两天有人盯着我,是你啊!”
傅云翔露出奇怪的表情:“你想多了吧?我是昨晚半夜才赶来的。”
啊?那,真是我的错觉了?我想了想,啊了一声:“我知道了,是很多人都被我迷倒了,所以偷窥我,我就有感应了!”说完,大笑起来。
傅云翔捂住我的嘴,又放开,耻笑我:“你太得意了。”
我就得意呢!我想起了什么,问他:“你怎么进来的?是朵朵给的钥匙吗?”
他点头:“我说,我要照顾这个喝醉的妹妹——而且,我在隔壁有个房间。”我笑了,很狡猾,兄妹情深。再说了,这里头两张床,谁会想到他跟我躺在一张床上呢?
傅云翔伸手去拿桌上的一个盒子,递给我:“给你,迟了的生日礼物。”
我接过来,胡乱拆了,打开了这个长方形的盒子,吸一口气——这!
护指,俗称指甲套,是清代后妃护理指甲的必备之物。瞧这,铜镀金累丝的工艺,一个个的小环相叠在一起,做出古代铜钱的模样,拉开了帘子放到阳光下一照,贵气十足。我看呆了,傅云翔搂着我说道:“你不是说过,最喜欢这东西吗?我托人买的,这可是清光绪内务府造办处做的。”
天,他什么东西都能弄到啊?我起了兴趣,套在了手指上,仔细看着,越看越是喜欢——喜欢他这样宠我。
翻个身,将他压在身下,我欣赏着他的身体——这熟悉极了的身体。每一次,都能发现他身上更美好的地方,每一次,都想着如何在他怀里辗转反侧,每一次,狠了心却又迅速地失去了信心——这样的纠葛,有时候,真是惨烈。
“别弄……”傅云翔轻轻笑了,我正用那护指在他身上划过呢。
“你胆敢和老佛爷说不?”我眯眼做高高在上状。
我们都笑了,我脱下了护指,与他亲吻。
木屋的隔音不太好,有时候外头动静大了些,这里头也能听到。我低头吻傅云翔,我们轻抚彼此,控制各自的声音,不让一切传出去。
我不知道戒毒所是怎样去让人戒毒的,但绝对不会像我一样想要奢望一点点去、慢慢地断掉,因为这根本就断不掉。《门徒》说过,吸毒的人是因为空虚,可到底是吸毒更可怕还是空虚更可怕呢?是啊,到底是哪一样更可怕?
我爱傅云翔,这就是毒了。络新妇的爱,不知结局,到底是彻底占有到底吃掉他?还是让我的爱抽离?明明是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却让我如此纠缠不清。
傅云翔的动作很轻,我们像是偷情的男女,害怕被人发现。可是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爱的感觉更强烈了。冤家啊,我要怎么抽离他的爱?
我们都在努力地配合对方,我们想要对方比自己更快乐。
花洒喷了热水,将我们笼罩起来。
“邢飞他们来不了,让我给你带生日礼物,就在外头的箱子里。”傅云翔一边说,一边给我擦沐浴露。
我点头:“哦。”不太关心这个,我关心的,只是傅云翔对我的宠。
我想起小正太了。想了想,我问傅云翔:“想念知道我在这里吧?”
“知道,他要上课,没来。”傅云翔轻描淡写的。
那就行,我溜出来,他可能也蛮担心的。没心没肺的我玩着沐浴露的泡泡球,一吹,往上飞,水珠子一溅,啪,破了。
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