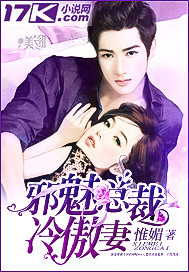我提着婚纱裙摆,脚上的高跟鞋快速地移动,直往孝远寺奔去。身后跟着一大群人,还有我的丈夫——
“阿兰,阿兰!”有人在我身后叫着,我不理会。
身后听到了男人追来时候皮鞋踏在地上的声音,我知道是崇想念——我的半个丈夫。
崇想念,今年二十一岁,刚从国外回来,他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因此,今天的婚礼是订婚礼。所以我说,他是我的半个丈夫。
丈夫,丈夫用来干什么?上床?恋爱?给肚子里的种子一个名分?还是要他来宠爱自己?宠爱到极致?无可救药?乱七八糟的念头从脑子里一闪而过,我继续我任性的一时兴起的逃亡。
孝远寺是个香火极旺的寺庙,在广州很有名,众多信徒来此拜佛,听高僧讲经。此时正是周末,这里的人更多了,我穿梭于信徒和僧人中间,无视他们投来的惊异的目光。
我要见净心。
一个极有名气的僧人,一个注定了要再回到尘世的僧人。
我熟悉这里的一切,我知道他在哪里,自如穿梭在这人海中,我白色的婚纱让我感觉自己像在飞。
甩掉所有人,所有的人。
“净心!”我微微喘着气,带着笑意喊出了这个名字。
禅房里的僧人都看了过来,主角净心,却只是盘坐在那蒲团上,不曾抬眼看我。
但我知道,他知道是我。只有我,才能这样地放肆。
我走了进去,婚纱拖曳在身后,面纱遮住了我的视线,我看得很朦胧。眼前像是隔了一层雾,我则在寻寻觅觅,寻找解脱的阳光。
我跪坐在他面前,轻声道:“我要出家,我不要这世俗了。”
他,依旧没有抬眼看我。
但,我知道他垂下的眼帘里,全是我白色的婚纱。
其他的僧人们知趣地退了出去——他们都认得我,都知道我和净心的关系——其实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净心。”我再次叫出了他的法号。
他终于看向我的脸,这双眼,干净极了,干净到纤尘不染,纤尘不染到容不下一点点的沙子。太干净,让人冷。
他张开了唇:“阿兰,你又在闹,出家?你?”
我嘻嘻笑着:“嗯,不可以吗?我跟着你,我们一起。”这层纱,永远在我和他之间隔起一道纸窗。
他的声音依旧很淡:“这里寺庙,你要出家也不在这里。何况,你,永远不可能脱离俗世。”
“你那么肯定?”我无聊地整理着蓬起来的裙摆,嘴里像是在背诵心中的台词。
“我没有母亲,爷爷奶奶死了,我恨我父亲,我和哥哥不明不白。现在,要嫁给一个小男生。没劲,真的没劲呢!”我叹着气,一双眼却在瞄着他,看他怎么作答。
他的面色是冷漠的,十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他说:“阿兰,你不要装了。”
“装?装什么?”我做出吃惊的样子。
他定定地看了我好一会,又重新垂下了眼帘:“你,沉浸在尘世的欲望、金钱中,你所说的苦恼并不足以让你放弃一切。你根本就没有真正地厌倦,你很明白你想要什么,离开了也不能让你解脱,因为你根本就没想要解脱。”
“就像罂粟,当得到的愉悦被放在最重要的位子,痛苦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净心说完了,干脆闭上眼,似乎不想再搭理我。
我张张嘴,笑了,身子微微颤抖:“净心,你最是无趣的了。看着你,就像是看到一块石头,捂不热,没劲透了!”
他不回答我。
我向一侧坐去,揉揉酸疼的腿,想了想,躺下去,枕着他的大腿休息。
这禅房里,一个不一样的僧人,一个穿着婚纱的俗世女子,以亲密而又疏离的方式贴在一起。
我轻声道:“净心,这世间万物,总有一样东西和自己相似,你说,我像什么?”我喜欢他身上的檀香,可以让人安静下来。
是啊,我到底像什么?
我重新坐起来,掀开了面纱,将脸凑到净心的面前:“净心,你说,我像什么?”
他睁开眼,我们的呼吸吐在对方的脸上。我想起十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这样的状况,他没躲闪,我更不会躲开,我和他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但又有着最奇妙的联系。
我再次问他:“你说,我像什么?我想知道在你的心里,我像什么?”
阳光从我身后打来,婚纱呈现出半透明状,我看到我的影子投射在他的身上,渐渐起了变化,像是奇怪的物种,在温柔地伸出触手,要将他捕获。
石头一样冰冷的净心,看着我的双眼不起波澜,他的眉头甚至都没有动一下。
他一眼看穿了我,吐出了三个字:“络新妇。”
络新妇?那会在交配之后吃掉雄性的雌性蜘蛛吗?她极尽妩媚和诱惑,待他享受了快乐,将他拥在怀中,一口一口吃掉。吃掉他,就是得到了完整的他,身体和爱欲都得到了,一点不剩。
末了,满足地孕育着肚子里的孩子,那是她的,也是他的。她的爱是可怕的,也是最赤裸裸的直接占有——占有全部。
她的爱,真是毒,他对她的宠爱,更是毒,毒到葬身其中。
“络新妇?”我喃喃道,回味着,他已经慢慢站起来,转过身去不看我。
他的声音很低很低:“阿兰,你起来吧,你的未婚夫该追来了。”
我依旧跪坐在地上,看着他的背影出神,十年过去了,他也长大了。这背影越来越高大,身材越来越挺拔,我爱这样的背影。
有些冷漠,有些孤单,有些——固执。
这个背影和那个背影那么地像,像极了,我爱这样的背影。
我到底爱谁呢?我用画笔画下的背影,到底是谁的?
蓝色的,红色的,橘红色的,黄色的,黑色的,紫色的,所有的色彩幻化为飞蝶缠绕在我的身边。停落在我的婚纱上,停落在我的肌肤上,停落在我的脸上,所有的呼吸都被堵住了,我被这色彩淹没。
“阿兰!”身后忽然传来了崇想念的声音。
我转过头,看到他的脸色有些红,气息有些喘。穿着西装的他比我小了足足五岁,我不喜欢小男生,但——他真的很好看。
我看到他,只会想到一句诗词:眼似秋潭,眉若远山。这本来是用来形容女人的,但用在他身上一点都不奇怪。
他扫一眼这里头,快步走了过来,蹲下,小心翼翼地将我扶起:“阿兰,我们走吧,你放心,我会跟爸爸解释好这一切的。”
我看了他一眼——他这样宠我,更甚哥哥。可这宠爱的目的是出于什么呢?
我很清楚。
将面纱重新放下,我朝依旧背对着我们的净心说道:“净心,无论如何,今天的傅兰兰是最美的,你,必须要记住这一天。你,得好好看着我。”
净心没有动,他不肯转身。
我无声地笑了,挽上崇想念的手臂:“净心,你不看我,你从来不肯有半点的感情,你觉得这一切都是脏的,可你也只看透了一半——你也在徘徊和痛苦不是吗?你不看我,今天,你不肯好好看我,你会后悔的。”
他的背影,不动如山。
净心,你很聪明,可是你没能做到洒脱。我了解你,正如你对我的了解。
我站了一会,同崇想念一起转身,离开这里。
我不知道净心有没有转过身,他是那样冷漠的一个人。
傅兰兰的订婚宴和一般人的订婚宴没多大的区别,在广州这个地方,无论是婚宴还是订婚宴,只要酒楼还不错的,菜式和味道都差不多,差别仅在于装修。白天鹅宾馆当然是很豪华的,但奇怪的是,服务却比起其他的酒楼诸如荔湾亭差些;至于味道嘛,有些人会觉得有些油腻。
我选择在了天极品,这是广州酒家旗下的高级酒楼——
我只喜欢吃他家做的鱼,其他的,实在一般,只是服务确实不错,吃过天极品的菜,我总能挑出些毛病来。比如烤乳猪味道怪,比如鸳鸯鸡或咸或油腻——
彼时,哥哥的手正抚过我耳际的发丝,笑着问我:“那阿兰为什么要挑这家酒楼?”
我笑了:“因为我不高兴,我也要来婚宴的人吃得不高兴。”
其实现在想来,真是幼稚,我觉得不好吃,别人说不定吃得很爽呢?
说远了说远了,眼下,我正在被几个男人灌酒——一个二个的,都是哥哥的朋友,狡猾一如泥鳅——怪了,不去灌我的未婚夫崇想念,来折腾我干嘛来的?
我笑眯眯,已经有了醉意,他们在起哄:“阿兰,快点再喝一杯,这点酒对阿兰来说,根本就是湿湿碎啦!”
这间包间里的人,都是哥哥的朋友,军装上的风纪扣已经解开,肩上的两杠两星很是显眼。我指着领头的邢飞笑:“我要是纠察,把你们全都抓起来,关禁闭!”
邢飞笑得比我还灿烂:“阿兰要是纠察,我们就乐意!”
赤-裸-裸的调情,真不要脸!我白他们一眼:“不要喝!”
一搂紧我的未婚夫崇想念的手臂,我看一眼他,把脑袋放在他的肩膀上,眼睛眯起来。崇想念表现很平淡,他美丽的小正太脸蛋有些红润了,大概是喝了不少的关系,他想要接过邢飞的酒杯:“我替阿兰喝了吧,她今天喝得多了。”
邢飞的手一晃,酒杯就没有落入想念的手里:“那唔同的,你和阿兰要分开喝。”他故意夹杂着广东话,知道想念听不懂。
我也不搭理,邢飞这群人,今天存心要灌醉我——
包间门口打开了,我没有回头,但是我知道那是谁,是他,是傅云翔,我的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
“阿兰还被你们困着呢!”他出了声,声音有点儿低沉,有点儿磁性,带着令人心安的味道,像是池子上空吹过的风,柔和舒服。
邢飞手里的酒杯就放到了桌上,冲着我身后的人笑:“傅哥,今天是阿兰大喜的日子嗟!”
“大喜你们就要灌醉她?”声音的主人走到了我身边,转了个弯,站在我和邢飞的中间。我看着他,军装在身,眉眼温润如玉,像是我脖子上最美好的玉观音,不,他是个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