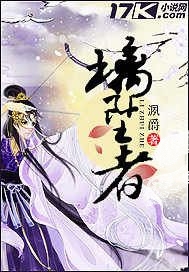“夏郎……我要你……我想要你……”
她的声音充满诱惑与迷离,然而,也带着说不出的凄绝,带着一种破罐破摔、豁出去了的悲凉。
那么我轻一点就是了,轻一点应该没有关系吧……
他正在矛盾地挣扎,殿外响起了庆生的声音:“陛下,钟太医到了。”
他长舒一口气,撑起身体。
她也从刚才莫名的狂乱中,突然清醒。迷离的眸子,逐渐冷却。
“媚烟……”强行压抑的欲望让他的声音带着沙哑,显得无比性感。他温柔地替她把衣襟掩好,恋恋不舍地望了她一眼,才起身出去。
片刻后,他带着一名花白胡子的太医进来。
这位钟太医是太医院千金科的名宿,他给舒雅拿过脉之后,神色凝重。
钟太医站起身,向皇帝深深一揖,“启禀圣上。这位娘娘阴血亏少,肾气虚弱,故而,胎虽能成而不稳。胎儿居于母体,全赖气以载之,血以荫之,气阴两伤,胎无所生则堕矣。故以清虚热为先,兼以补肾固冲安胎。”
高君琰不耐烦地说,“现在的问题是她什么也吃不下,吃什么吐什么,连药也服不进去。朕请你来,就是想请你给她扎两针,让她能够吃下一点东西,她已经两日未进粒米。”
钟太医再次一揖,“如此臣便为娘娘针灸 天枢、中脘、内关、足三里,这四处穴位。天枢为大肠募穴,有调理胃肠的功能,可使浊气下降之效;中脘为腑之会,又是胃之募穴,有健脾和胃降逆之功;内关为心包经的络穴,别走三焦经……”
“行了,行了,你快开始行针吧。不用解释这么多了。”高君琰一挥袖。
太医扎针的时候,高君琰在一旁关怀地看着,舒雅却微闭双目,像是睡过去了一般。
高君琰想起母亲走之前没有来得及嘱托太多的注意事项,便问钟太医,像舒雅这种情况要注意些什么。
钟太医一边扎针,一边公事公办地说,“需忌食羊肉,狗肉,牛肉等燥热之物。需多食补肾养血之物……”
钟太医说了一串饮食宜忌之后,突然紧接着说了一句,“要绝对禁止房.事。”
这句话是接着前面说出来,钟太医的语调和神情并无变化。然而高君琰却做了一个邪谑的鬼脸,看向舒雅。
让他微微失落的是,舒雅没有睁开眼睛,太医这句话未曾让舒雅的面容出现一丝波动。
他知道她并没有睡着。只是她的容颜这样冷,几乎让高君琰怀疑刚才她炽热而迷乱的呼唤“夏郎”,只是他的一场错觉。
这时,钟太医补充了一句,“还有,这位娘娘有伤悲内积于心,思伤脾,忧伤肾。伤脾,则亦吐。伤肾,则阴亏。娘娘若是看不开,这妊娠反应只怕会越来越严重。”
舒雅静静地听着,眼目依然闭着,烛火将她低垂的长睫投下一片阴影。
高君琰的眼神变得复杂幽邃。
行针完毕后,高君琰让庆生送太医回太医院,并且交待庆生顺便到太医院去拿一盒治疗冻疮的药膏。
舒雅一直阖着的双目,终于在此刻掀开,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高君琰还真是细心,竟然注意到她手上长满了冻疮。
舒雅久久看着烛光映照下,满手的红肿淤青。她原本有一双纤长白嫩的玉手。
这是她对那个男人无微不至的爱与关怀留下的痕迹,如今看着,只觉无比凄凉,无比酸楚。
她一辈子都没有给任何男人洗过衣服,萧辰是第一个,唯一的一个。随他征战这半年,她没有让他做一件生活琐事。入秋之后,她依然每天浸泡在冰冷的水里给他洗衣服。
她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去伺候男人了。她发现了,人就是这么贱,你越对他好,他越轻视你,越不懂得珍惜。
“娘娘有伤悲内积于心,若是看不开,妊娠反应只怕会越来越严重。”
想起刚才太医这句话,她仰起头来,靠在刺绣织锦软枕上。浓浓的悲戚晕染了她绝世的容颜,呈现出一种极其朦胧而凄清的美丽。
高君琰进来时,正好看见这幅绝美的图画,让他一下怔在那里。
正要说什么,突然殿外响起传报声,“皇上,护军将军求见!”
虽然这时已经是晚间,但因为是战时,高君琰交待过,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他在哪里,只要是有关前线的军务,都要第一时间禀报天听。
“让他到含元殿东堂等候。”高君琰走过去,轻轻拥住舒雅,沿着她的额头,鼻梁,嘴唇,下颌,迅速地一线吻下,“朕去处理军务,一会儿回来陪你用膳。如今扎了针,应该胃口好一些了吧?朕让御膳房做了你最爱吃的菜哦。”
她淡淡地笑了,点点头。
走出倚晴阁,他匆匆地来到经常办公的含元殿东堂,护军将军韩景桓已经恭候在此,见了皇帝行了一个参拜之礼。
“爱卿免礼。”高君琰随和一笑,“近来兵凶战危,京城防守加严,爱卿辛劳了。”
“这是末将职责所在,岂敢言劳。”韩将军拱手躬身,“启禀皇上,江北有使者过来,声称是北帝派来,要亲自面见陛下。戴将军将此人移送末将手里,此人声称有机密要事,必须立刻亲见陛下,是以末将不敢耽搁,不得不此时来打扰陛下,不知陛下是否要召见此人?”
高君琰听见“北帝派来”几个字,心里一惊,眼底有阴冷的光芒划过。
“你立刻把此人带来见朕。”高君琰等韩将军说完,没有丝毫迟疑就下令。
“此人已在宫门外恭候,待末将亲自去押来。”
高君琰派了一个小黄门,跟随韩景桓一道出去,过了半柱香的时间,带进来一个青衫素冠的清秀书生。
使者从袖中摸出一张纸条,由一名小黄门呈递给高君琰。
高君琰展开一看,眉峰明显耸动了一下。但他很快控制住情绪,问使者,“划江而治,此话真假难辨,北帝将何以取信于朕?”
使者不紧不慢说,“大漠骑兵退至巴蜀边境,吴越国已经入境的水师退回吴楚边境,另一支吴越水师取消来援。”
高君琰手抚下颌,嘴角浮动着一抹莫测的笑。
半晌,他突然问使者,“不知先生贵姓?”
使者深深一揖,“敝姓田。”
高君琰意味深长地笑起来,“田先生见了朕,为何面不改色?难道田先生未曾发现,朕与你们皇帝容貌有几分相似?”
田胜不动声色地拱手答道,“田某出发之前,吾皇已经就此关照过。”
“哦?”高君琰向前倾身,手肘横在案上,脸上带了几分兴味,“那么依田先生看来,朕与北帝,谁更有真龙之相?”
田胜朗声一笑,答道,“楚帝多此一问。田某幼读圣贤,自恃韬略,自然是择木而栖,择主而事。若非效力真龙,岂不负了田某平生所学?”
言下之意当然是说萧辰才是真龙,但却说得极为巧妙。
高君琰仰头大笑,普通人听了他的笑声,都会胆战心惊,不知所措。但田胜面不改色。
笑罢,高君琰扬起手中的纸条,“这是你们皇帝的亲笔吧?想必田先生已经看了。试问,真龙天子可会为一介妇人退师?”
田胜亦哈哈大笑,“楚帝莫非不知道,女人永远只是借口!”
“既然只是借口,那朕还就不还他了!”高君琰脸上是半带戏谑的笑,然而手中的纸条攥得极紧,几乎揉碎。
“吾皇给楚帝一个好借口,可以纾解国难,扭转危局,楚帝若不要,田某亦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田胜昂首挺胸,一脸蔑视,“说到底,楚帝若以真龙自居,又怎会为一介妇人,放弃议和的良机?”
高君琰斜眼看着田胜,笑道,“先生好辩才!不知先生在北帝帐下身居何职?”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中军司马。我们北卫,才略远胜田某者,不可胜计。我皇圣德,自然贤才景从,多士为辅。”
高君琰脸上现出真挚温厚的笑容,“既然多士为辅,岂能显示先生功德?先生若更择明主,必受重用。真龙亦要借以云雨方能兴之,朕视先生为云雨,先生可愿辅佐朕成真龙?”
高君琰这是在巧舌如簧地收买田胜。田胜来自萧辰帐下,必定掌握不少敌方军机,高君琰难以判断萧辰此番意图,便想撬开使者之口。
岂料田胜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人,当即答道,“田某受我皇知遇之恩,此生无以为报。楚帝若一定要逼问或者强留,田某只好效徐庶之高义。”
说完这句,田胜再不发一言。
他所说的徐庶是三国名士,本是刘备的谋士,后来被曹操骗去,却身在曹营心在汉,终生不为曹操出一谋划一策。
高君琰见他说到这份上,也就不再勉强。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高君琰让田胜回去,他要思考几天,再派使者过江,答复萧辰。
田胜离开后,高君琰遣退所有人,再次展开萧辰的亲笔纸条,在烛光下看着。
纸上写着:“把她还朕,朕与你划江而治。”
看来萧辰已经猜到舒雅在他这里。
难道母亲说的是真的?萧辰真的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了统一大业?
目前萧辰上游的水军捷报频传,正与岸上的大漠骑兵配合着,顺利东下。
再凭借两支吴越国水军渡江,与上游的部队会师,兵围楚国都城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事。
这样的大好形势,一旦放弃,机不再来。
萧辰既然表示大漠骑兵、吴越国水军都可以退师,看来是有诚意的,不像是一个陷阱。
高君琰捏着纸条,往后慢慢地依靠在凭几上。
烛光明明灭灭地映着他的脸,俊美的五官更显轮廓深刻。长眉如剑,高鼻鹰勾,薄唇浮着阴冷的笑意。
一个完美的谋划慢慢浮现在脑海。
随着这个谋划逐渐清晰,各种情绪在高君琰脸上变幻不定,阴狠,毒辣,冷戾……
他再次展开萧辰的亲笔纸条,看着那清遒刚劲的字体。
“划江而治?哼,谁要跟你划江而治?我要的是整个天下,包括你的江山,你的女人!倒霉的是,还有你的孩子,哼……这个孩子,不知道保不保得住。为了媚烟,我不会去害这个孩子,就看它自己的造化吧。”
他把这张纸条藏在怀里,站起身,让小太监去传唤庆生。
对庆生附耳几句,庆生再进来时,手上托着一只洁白的信鸽。
高君琰把写好的纸条卷起来,放进竹筒,系在鸽腿上,然后让庆生去放飞。
这是他和冷百合的联系方式,用的是只有母子俩能看懂的密码。
所以,就算被萧辰的间谍截获,也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