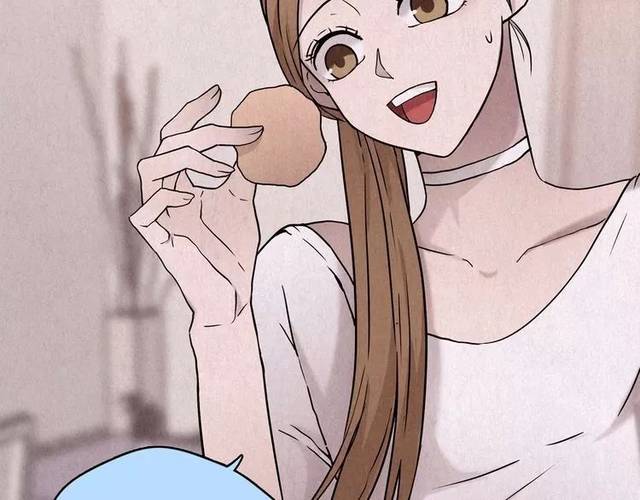被即时打入慎药司的零彻,命运在一晚间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尊主身边的一流侍者,变为现在和奴隶共处一辆笼车。
押送奴隶的笼车在山间峡谷吱呀吱呀前行,奴隶哀嚎声连绵不绝,差役听得烦了便甩出几鞭子,唯有零彻安静抱膝仰头望天,头顶伴她的是一轮明晃晃的月亮。
零彻静静想着···自己要在这慎药司待多久才能回到离恨天呢,这晚少主大发脾气,骇人的可怕···明明任务完成到位,那晚是尊主亲自下达的命令,自己一字不落地听下来···确实是要求杀死吏部尚书家的千金沈清歌,自己是哪里做错了吗?她思来想去想不明白,摸摸发肿的脸···忽然被一鞭子打得皮开肉绽!
“老实点儿!”
只见那脑满肠肥的差役瞪了对鱼眼向零彻身边哭哭啼啼的母子呵斥道!零彻看了眼胳膊上被打的伤口,抬眼盯向他···挪动身子,忽如电掣般伸出手掐住那差役的脖子!将他的头不断磕在笼车上,周围的差役都慌了神···纷纷抽刀作势向零彻手腕砍去,零彻这才松了手,那被掐脖子的差役惊魂未定,不断喘着粗气,最后结结巴巴地说道:
“先!先把她推进慎药司!快!”
于是乎零彻所在的笼车被加快了速度,不一会儿···便进了一个阴森森的山洞,里面幽暗潮湿···传来阵阵**,令人不寒而栗。
“你的!你的好日子就到这儿吧!”那差役龇牙咧嘴地将零彻押下车,执着火把将她带到一处虚掩着的石门前,硬生生推了进去!
零彻站起身,扶起脚下的水壶,她放眼望去···只见这间阔大的石房中央是一高台床帐,石房边种满了奇异药草,山泉水自石房顶流下,汇成瀑布,引成小溪。抬头看,可见星空。一些奴隶蜷缩身子趴在不显眼的角落,发出半死不活的**声。
她还不知道,房内和房外那些奴隶的痛苦已经结束,从此以后将由她来承担了。
“你是离恨天送来试药的杀手,嗯?”
一阵平淡柔和的男声从不远处传来,零彻警惕看去···只见一个身穿黑色长衣的男子用块白布擦拭着手上的血迹向自己缓缓走来,他身后是一张摆满药物的长桌和几具明黄色的药柜,长桌下倒着一具抽搐的奴隶尸体。
“是···”
零彻后退了几步···她现在看清了这慎药司司命的面目,深邃阴郁的双眼竟是异瞳,眼珠一黑一蓝,皮肤由于长久不见天日而变得煞白,长发简单束了,几乎垂到地面。他抿了刻薄的薄唇似乎在笑···零彻不禁发自内心地感到诡异。
“好,有名字吗?”这司命稍稍弯下腰,对零彻伸出骨节分明的手,令人感到自然的亲近···
“我叫零彻。”
零彻配合地将手轻搭在他的手上,虽然她不明白这是在做什么···但猜测着可能是在打招呼吧,就像向尊主行礼一般。
“零彻,很好···我是江肆隐,慎药司的司命,从此以后,你便要听命于我。”
这位江司命收了手,拿了零彻脚下的水壶去给一朵快要枯萎的紫花浇水。零彻忽然感到手心一阵瘙痒,那感觉酥麻不已,一直传到肘尖。
“去把那奴隶扔出去吧。”江肆隐对零彻亲切摆摆手,零彻听话走到尸体旁蹲下身,只看到这奴隶的五脏六腑都被掏空!眼睛却还大睁,像一条死鱼!
她不禁回头看了眼江肆隐,这位司命看起来浇花浇得很悠闲。
江司命,给人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零彻不知不觉咽了口口水···
“扔完了以后过来。”江肆隐戴了手套,取了根银针,在不同的药瓶中蘸取药液···零彻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股莫名的窒息感涌上全身,令她喘不上气来。
终于这异瞳药医拉过零彻的手臂,将银针稳稳扎入显眼的青色血管。刹那间!零彻失了魂一般,只觉千百条毒虫在钻心,四肢渐渐僵硬,貌似不再属于自己,眼前也变得模糊一片,目光呆滞···慢慢地竟晕死过去,脑中发号施令的却是江肆隐的声音。
“向前走。”
零彻的身子懵懵向前移了一步,江肆隐在一个本上画了道,似乎是第一步完成了。
“现在,转身,去杀了那些奴隶。”
零彻依旧照做,只见她飞一般地移动到奴隶堆,以手指穿透奴隶的脖子如戳稀泥,甚至将其颈骨···江肆隐远远地看着这一切!手中的笔不停记录,他惨白的脸上露出渗人的笑!这力度与速度简直如同怪物啊!
然而,不到片刻···零彻便失了药效,她跪倒在地,看着地上瞪大双眼盯着自己的奴隶尸体以及自己沾满鲜血的颤抖双手,受人控制的焦灼感油然而生!与之俱来的还有药效过后的痛苦,她本人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快的速度与强大力量,手指如同废掉一般···心脏剧烈跳动,还有那千百条毒虫慢慢爬出般的痛痒感!零彻已经整个人蜷缩倒在地上,五官扭曲···口水肆意淌下,发出撕心裂肺的**,她顿时只觉想死!然而耳边传来却只是一句不痛不痒的话。
“药效过后···依然痛苦,能力过度支取···仍形成伤势。”
江肆隐蹲在她身旁,漠不关心地做着记录,若是要硬有些别的什么感情···恐怕只能扯出些失望。
越亦淮将她打入慎药司···目前为止对他来说也算是个正确决定,若是他知道零彻如此痛苦,心里应会好受些。
“脉象···完好?”江肆隐把了她的脉倒有些惊讶,试药这么多次,效果最好的一般是在药效成功发作时突然暴毙,像她这样药效过后心脏依然活蹦乱跳的还是头一个。
这倒有点意思了!江肆隐一笑,将她抱起放在药桌上,回身查看从医娘那里偷来的记录药方秘密的羊皮卷。而零彻只能等着痛苦慢慢如潮水般退去,她的双手已经几近废掉,转头看向江肆隐···眼中渐渐起了杀意。
“你还能听到我说话对吧?”
江肆隐点开桌上小灯,翻开零彻眼皮查看瞳孔,那一刻···零彻离他极近,甚至将他湛蓝左眼的星星点点都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想杀一个人的眼神藏不住,江肆隐注意到···早已将手背后,以中指指尖轻掰食指指尖,零彻顿时被电击一般整个身子都弹起,那痛苦如排山倒海般袭来,蚀骨钻心!豆大的汗珠浸湿她的鬓发···她只顾发泄般的喊叫!
这毒是江肆隐与她搭手时下的。
“这是线毒,我研药时的意外发现,至今没有人能熬过。所以,你要好好听命于我,要知道···我也不想让你死,别像其他奴隶一样不争气。”江肆隐将她绑住,拿块布团死死塞了她的嘴,一来是为了让她冷静,二来是怕她自杀。
于是给她双手上了药,撕下段纱带为她包扎伤口。零彻只得两眼无神地望着那群星闪烁的夜空···默默接受自己试药的命运。
“你的手伤明天就可以好,没事的。”江肆隐将她的手包扎完,温柔地解开绳子拿了布团,语气竟有些安慰,“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武功,自然比不了你这来自离恨天的杀手,到时候你杀掉我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呢···毒是定时发作的,你杀掉我,痛苦就会永远持续,明白了吗?”
零彻死死地盯着他,生死···对于杀手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杀不掉江肆隐,自杀还不成?然而江肆隐像是看透了她的心思,只是笑笑,凑近了她···将她的头摆正,与她一同望着慎药司外的美丽星空,发出一声奇妙的赞叹!
“你看啊!那是外面的世界,那是自由,告诉我,你若活下来为我试完药,出去以后想干什么呢,嗯?”
“我···我要回离恨天。”零彻不知不觉的吐出这句话,她看呆了···夜空中的星星仿佛在对她招手。
“那便先要好好活下来,离恨天在等着你回去。”江肆隐语气坚定,从袖中掏出一颗果干喂给她,好像真的要和她一起努力回离恨天似的···
自那以后,零彻真的放弃了自杀念头···只不过日夜处在昏暗的慎药司,每日试药,钻心蚀骨,眼中渐渐失了神采···她时常会坐在哗哗流水的瀑布边抬头看天,那微褐色双眼凹陷下去许多,总不经意流下泪水···
江肆隐除了在她强硬拒绝试药时摔打过一次药瓶,其他时候都是少言温和的模样,然而在零彻看来,他永远是怪异骇人的异瞳药医···每次试药有进展时露出那恐怖恣意的狞笑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其他时候···就算江肆隐给她洗浴,编发,换上干净明丽的衣裙,偶尔为她暖手,说一些动听话儿,她也仍是消极以待,再者···江肆隐这样对她,也不过是为了眼前能够赏心悦目罢了,既然日子一天天长久,他不可能任自己和一个散发恶臭的肮脏杀手生活在一起。
“零彻,我在那瀑布下新种的药带寒气,不要总待在那里了。”
江肆隐一边将离恨天运来的药装斗一边对零彻提醒道,实际上他每天都提醒一遍,但零彻心思早飘到外面的世界,从未听见过···最后江肆隐还不是都要在零彻睡着时把她抱离瀑布。
他将该说的都说尽,便不再管,恰好这日药来得齐全,江肆隐研究那药方入了迷,在高台床帐间铺满了各类试验的药方,写写画画中···忘了去顾零彻,夜渐渐深了···那药开花,散发阵阵苦寒,本就潮湿阴冷的石房一角顿时变为寒冬腊月,趴在岩石边入睡的零彻身子蜷缩成一团,水流汇成的小溪瞬间结冰···岩上凝了一层厚厚白霜,白霜成精一般爬上零彻全身,不知是零彻体内药物作祟还是她本身体质如此,那白霜似是将她整个人冻成一块不会化开的冰,心口处都没了热气儿!
“呲!”
零彻狠狠睁开冰片般的眼皮!苦寒中,她都震惊自己仍然活着,然而星光照耀下,冰霜白闪闪,刺骨剜心般的寒冷不减···零彻支撑着冰块似的身子站起来,逃命似的亦步亦趋···一直到江肆隐的高台床帐下。
“司命!司命!”
沙哑可怖的嗓音将江肆隐从药方中生生拽出!他惊讶地盯着眼前满身白霜的零彻爬向自己,说话时口中竟连哈气都没有!手中毛笔掉落···他连忙张开双臂将她揽进怀里!扯了温热的羽被为她盖上,药方四处飞散掉落,江肆隐全然不管,只一心抱紧她,在她颈边,手上,狠狠呵着热气!
“司命,司命护我····快护我···”
零彻嘴唇打着战,一手扯紧了江肆隐的衣领在他耳边奄奄一息道,好像她握住的不是衣领,而是自己的命。
“司命···”
“伸手。”一向不慌不乱的江肆隐此刻也多少有些发抖,他抓了零彻的腕给她把脉,却惊得倒吸一口气将她整个人松开!
眼前这冰人没有脉搏,却仍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