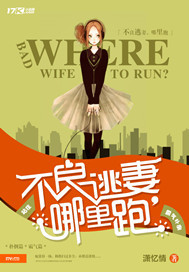阿甘的母亲对阿甘说:“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的。”
当然啦,这句话不太适合我们中国人,毕竟从小到大,我们的巧克力要么一盒一种口味,要么一盒里的所有口味都在外壳上标记的清清楚楚,甚至打开盒子,不同包装纸的颜色都在理直气壮地告诉你:红色的是草莓味、绿色的是抹茶味、黑色的是黑巧克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说到这里,是不是跑题了?也没有,写文章嘛,总要先写点什么东西,然后慢慢引入正题,这大概是每个写手都有点的毛病,创造一点装神弄鬼的氛围然后突然给你讲故事,你还觉得挺有趣,哈哈。
其实故事挺简单的,你大概几岁开始记事?1岁?2岁?5岁?你要问我那个晚上我几岁,我也不大能记得了,我只能精准地告诉你,那时候我还没上幼儿园,具体上幼儿园该是几岁,那就得去查查相关规定了吧。
有时候你会不明白,大脑是怎么决定某一刻的事情你必须记住的,但反正就是这么开始了,我坐在楼梯上,看着下面几个人你来我往地博弈,大人的世界往往挺有趣的,爱和恨有时很分明,有时又不是,反正张牙舞爪地互相叫嚣,渐渐的,从害怕无助变得有些困,然后,一个人就冲出去了,那一瞬间困意消散,支棱起自己的小胳膊小腿地跟着冲,然后世界瞬间在你面前变成了一条单行道,一头是一个人,另一头是另一个人并且手放在了门把手上。
路那头的人只剩下了背影,门边的人眼神里是冷漠的光,举步维艰地前后踟躇,最后冷漠的光熄灭了、门关了,就只能义无反顾地奔向背影,从此开启了没有回头路的人生主线。
……
好了,忘掉初始值的不愉快,时间来到大概1997-98年间,我记得在能够长久定居之前,曾辗转很多个小房子几年之久,第一栋小房子是在拥有水泥楼梯的二楼,我相信很多南方小伙伴一定对这样的建筑富有深刻的记忆:高耸又单调的水泥墙,表面坑坑洼洼的,一道水泥楼梯沿着墙上去,接着一道木门,里面是个大概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子,一个大衣柜、一个五斗橱、一个破电视机、一个挂钟、一张沙发再加一张床,大概这是很多九十年代末一家三口的常见住宅吧,哦,如果可以,还可能会有一个小痰盂。
楼下是房东一家的屋子,那可就大多了,走进去是宽敞的客厅,走进深处有独立的卫生间,还会有两间卧房,一间属于房东夫妻,一间属于人家的孩子。那会儿的自己还是个小屁孩,所以总能够在房东家进进出出,有一次还得到了一只红色的蛋,把自己手指都染红了,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家里有了新生儿发给亲朋好友的喜蛋,不过现在的00后大概很难见到咯。
隔着房子的窄道旁是一个小池塘,那时候还很瘦削的父亲会在秋冬日的午后,在黄昏的太阳下垂钓,站着笔挺的背影,静待着鱼儿愿者上钩,而我无聊地蹲在他的背后吃着各色零食,打发着那些年没有什么娱乐方式的陈旧时光。
那时候的记忆细碎又绵长,猫憎狗厌的年纪可以追着土狗玩一下午,会用那种金属制的勺子?着苹果吃很久也不会腻,细细绵绵的口感比现在的水果糖都来得甜蜜,会无聊的和隔壁邻居家的小哥哥争论为什么男生站着上厕所而女生坐着,回过头是被我们逗的乐个不停的邻居阿姨奶奶们……甚至,还能看到拎着盛满温水的老爷爷,兜头帮他的老伴一根一根地洗头发,一洗可以洗一个下午,滴落下的脸盆内水屋内如墨,我问老爷爷是为什么,老奶奶闭着眼笑着回答你:“是奶奶不爱洗头啊,所以这么脏……”老爷爷笑的一脸慈爱点着头附和着幽默的“谎言”,后来你知道那是因为老奶奶染黑了白发,时代劣质的染黑剂总是遇到水就化开。
欸,你是不是觉得回忆都很美好?其实也不是,那个年代普通人家的父母总是要辛勤地工作才能让日子过的不那么费力,有时候父母披星戴月出去工作,会把我反锁在屋子里。我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是年幼的自己受够了这样的禁锢还是感到了荒谬的孤独,我疯狂地拍着门哭喊着要出去,要爸爸妈妈,却没有人回应我,虽然屋里有灯,我却觉得有魑魅魍魉在我身边,随时要张开嘴巴把我一口吞没。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披着毛巾穿着睡衣的房东阿姨急匆匆地给我开门,被我一脸的泪水惊吓到,搂着我下楼给我好吃的,直到父母回来把我带回家,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能遇到这样的阿姨是何种的幸运呢。
就这样,春去冬来,随手拔下来养在塑料雪碧瓶里的腊梅都凋谢了,在房东阿姨的目光中,我们离开了我记忆里的第一栋小房子,来到了第二处。
随之而来的,是我正式进入了幼儿园,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学龄前儿童!
第二栋房子是一个矮矮的土平房,就是弄堂里最不起眼的那种平方,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电视机、一个水池、一张小桌子就足够一家人住了,只能单向同行的门后依旧是房东一家,有时他们会热情地开门欢迎我去坐坐,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毫无动静,让我都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除了那道门。
那一年,电视机里还在播放吕颂贤版《笑傲江湖》,每当周末的午后,我就坐在床上看着桃谷六仙嘻嘻哈哈地捉弄主角,那时候根本不认识TVB,更不认识港台明星,只知道主人公令狐聪实在很帅气,电视情节精彩纷呈。
幼儿园老师在前两年教会我们刷牙,于是乎心大粗糙的父母会将蘸着刺激薄荷味的成人牙刷放在你面前,辛辣刺激的薄荷味牙膏让你恨死了刷牙这个活动,却又无法控制地羡慕和想象同班小朋友口中草莓味的牙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有时还会觉得说不定是人家骗自己的呢?
据说我小时候打针从不让父母操心,在别的小孩子打针哭的撕心裂肺需要家长按住才能老实挨针的愁云惨雾里,我父母都会让我趴在他们的膝头然后淡定地告诉医生可以了,于是在医生费解地将针扎进我肌肉时,我会紧紧捂住嘴巴防止因为刺激的痒而笑出声,我的行为一度迷惑了很多其他小朋友。
这样的粗神经也影响了我第一次被采指尖血体验,那种针刺的奇妙感令我有点点着迷,于是不懂消毒的我回家小心翼翼地找到床头柜里母亲的针盒,那种老式的圆形针盒,里面被分割成一格格,充斥着不同粗细的绣花针,旋转的塑料套有一个缺口,转到哪一格就可以取哪一格的针。
我将银针捏在手里,就着流动的自来水,将自己的十个小指头扎破,不觉得疼,有一种怪异的刺激感。
或许这冥冥中也决定了未来我职业的选择吧,原来蝴蝶效应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