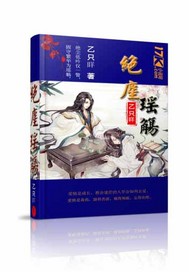我当时想,还就还,你还想吃多少年老子买的热烤麦包你说?十年?
浓缩壮汉还满守信用,下午就把苏裂买回来了,先让摩卡弹了一段给他听,然后挺随意的说了一句不错,就拿出一纸合约给摩卡签。
我问:我们之前不是签了约的吗?浓缩壮汉笑我对合同根本不了解,一看将来就是那被拐卖方。
原来我们之前的合同只是和爱尔兰签了,且没有注明他和摩卡是个组合,如果按那个合同一直操作下去,最后摩卡会一分钱都拿不到。
我吐了吐舌头,我一个在校学生我的确P都不懂,差点儿害摩卡做义工。
浓缩这个人还不算贱,说出来的话总有道理,我虚心接受再教育。
结果到了下午,爱尔兰也被严厉教育了,我就喜欢他和我如此有默契!我过的好他必定要比我过的更好,我倒霉他也必定要比我更倒霉!
浓缩让他必须学会“对观众要有节制的热情。”
这当然不是批评他平时对观众太热情,相反,这哥们一直拿观众当干粮,能不吃就不吃,那是相当的放纵自己。
浓缩出门去谈事情了,我就看见爱尔兰一个人站在空地上,皱着眉头望天发呆。
哥们难得有思考的时候啊!我赶紧的过去瞻仰一下,然后他马上问我什么叫有节制的热情,我想了想,告诉他那还不简单,就是搞暧昧呗。
他顿时觉得浓缩是个大神经病,跟观众搞什么暧昧?况且他向来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界限分明的很。
嗯……这个我能深刻体会,要不然在我们关系还不明朗的时候,他也不至于把事情处理的那么糟糕。(当时好像一直是我在耍暧昧)
我看他纠结,帮他分析一下:“和观众搞暧昧其实很简单,只冲他们点点头,握握手,绝对不说什么我爱你们啊之类废话,应该就可以了。”
他仿佛听明白了,突然眯着眼闷闷的说:“对了,我怎么觉得你和浓缩这么贴心?他想什么你都懂。”
我:“滚!”
然后我转身说要去收白天洗好的衣服(保姆的工作之一),他在后面耍赖:“那我的贴心人在哪里?我的贴心人在哪里?”
于是只好折回去,狠狠的给了他一个贴心吻。
他还不满意,圈着我不放,说:“收什么收,你又不是保姆。”
我说:“那你帮我去收衣服。”
他马上松手:“你快去快回,我在这儿等你!”
我怒道:“你个死乌龟。”
他大笑起来,却没有来追打我,看来被骂的很舒坦。=。=/////
恩,其实被追打也无所谓,他能对我笑就好,因为感觉到爱尔兰有些介意我说自己是保姆,我得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
傍晚时分,浓缩终于带着一身臭汗回来,脸上布满油光和兴奋,活像截被刷了蜜的烤大肠。
他对大家大力拍手道:“今晚上必定要给我卯起来表演!可别辜负我的大工夫。”
临出发,他还不忘叮嘱爱尔兰:“记住!要保持有节制的热情。”
爱尔兰挺老成的说:“知道,就是搞暧昧。”
浓缩瞪大眼睛:“你很聪明的嘛!”
不知道会发生事情,大家满腹疑惑的来到酒吧前,看见那酒吧屋顶竟然竖起了一个巨大的招贴——银色面具巡演风暴。
我被雷的浑身一哆嗦,但不能不说,这宣传太劲,不但手绘!还七彩!不但七彩!还荧光!
不过效果是满分,酒吧门口已经有人进不去了。
今晚的演出更加成功,不只是因为宣传,不只是因为爱尔兰一如往常的迷人演唱,还有摩卡的很大一份力量。
因为晚上表演的时候,浓缩并没有让摩卡单独**尔兰的伴奏,而是让他做了所有人的伴奏。
这让我惊讶,因为浓缩看起来只是很随意的听他弹了一段,竟然就敢让他在舞台的一侧为整场演出做伴奏,而其他两个乐手只是稍微做做合音,这也十分的有胆量。
差不多三个小时的演出,爱尔兰还能有替换下来的休息,摩卡却连站起来走两步的时间都没有,这安排看起来有点儿过分,我只能一厢情愿的告诉自己:他是因为很欣赏摩卡才这样安排的。
不过私下里,我承认我有很多幻想,以为浓缩会给摩卡整一金面具,然后把他和爱尔兰一起推出,弄个华丽组合呢。
但不能不说,我这个主意够蠢的。
表演结束后,大家在车厢里休息,我弄了些清凉薄荷油,不管摩卡的推让,轻轻的按摩他发烫的手指。
我很纠结的问:“疼吗?”
摩卡摇摇头,怕我不相信,又补了一句:“真的,只是好几天没摸弦,有点儿不习惯。”
我说:“骗人!”
唉,就是因为他太温和,我哪怕关心他,也会显得很凶悍。
爱尔兰在旁边默默的抽烟,然后站起来,狠狠的揉了摩卡的头发一把,便走了出去。
我隐约听见他和浓缩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他便回来了,又狠狠的揉了我的头发一把。
头可断血可流啊发型怎能丢啊!
我尖叫着把薄荷油抹在爱尔兰的鼻子上,他鼻子马上红了,眼泪都呛了出来,形象凄惨无比,我大笑:“看看这个委屈的小媳妇。”
他抽着鼻子说:“我的确很委屈。”
我问:“怎么?”
他告诉我他努力的对观众表现了有节制的热情,但怎么好像大家都没有发现。
我也奇怪自己怎么对此毫无记忆。
他说:“我和一个观众握了握手,他八十了,我还特意把手伸老长。”
我竭力冷静的对他说:“干的好。”
“干得好。”摩卡也表扬他,并走过来很友好拍了拍他的脸颊,爱尔兰立刻泪如泉涌。
当然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摩卡手上有更多薄荷油。
结果相当可怕。
第二天,可怜的爱尔兰鼻子塞住了,喉咙也哑了。
主唱失声,浓缩怒不可遮,如果他的职业是妈妈桑,现在就等于他手下的红牌被泼了王水。
丫在停车场暴跳如雷,宛如有人吃了他排队都吃不到的热烤麦包。
他狂风般卷来卷起,卷到每一个人面前大吼:“谁TM能告诉我!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没有人说话,我也呆住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慢慢走上前去说:“我……”
浓缩仿佛舞龙灯的,团子脸一下窜到我面前:“你什么!?”
我竟被吓的往后跳了一步,爱尔兰闪身过来挡在了我的面前,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不知道自己对薄荷油过敏,乱碰了那玩意。”
浓缩竖起粗短的食指,嘴角的肉急速的颤抖着,说:“那你最好永远都不要再靠近那东西!不然我让你全部吃下去!”
很好,丫完全气疯了。
有人小声问:“那今晚的演出怎么办。”
土耳其上前说:“要不今晚我们帮忙撑一场?”
浓缩用力的摆摆手,他气呼呼的转身走向车子,边走还边喊:“很好!正好重新开始!我们马上离开这个镇!把必须浪费的时间都浪费在路上吧!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