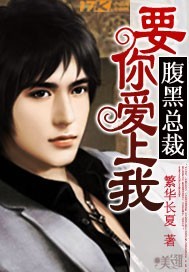直到第二天中午,顾歆舒还觉得恍恍惚惚的。
她不该看那盘录像带的,真的,这真的是个错误的妥协。
女人难道天生是为了受罪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吗?
她果然同情心泛滥到一发不可收拾。同是天涯沦落人,那一瞬间,她心疼了,心软了,再也不想争取什么,痛恨什么——尽管她也从来没打算这样做过。温婉自始至终没有抬起过头来,一开始只是沉默地裹着身体缩成一团,渐渐的,仿佛是屏幕里传过来的声响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努力掩埋了许久的残酷记忆,她开始无声地抽泣。到最后,她绷得紧紧的身体向顾歆舒倒过来,把自己深深埋进她的怀里,骤然爆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哭声。然而这哭声只持续了一会会儿,便突地戛然而止。她以为她不哭了,原来不是。她喉咙里艰难地滚动着哽咽着的奇怪音节,仿佛被巨大而刻骨的悲哀噎住了呼吸,整个身子战栗如风中残叶。
她说:“顾姐,我痛。”
顾歆舒怔了怔,把一只手轻轻搁在她单薄的背上,迟疑了片刻,开始温柔而缓缓地轻拍。
她想起来,纪晓阳曾经把她送给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离开她的身体之后,她也是这样把自己紧紧裹在单薄的被单中,死死扣住嘴唇的齿缝间沁出血红的颜色。起初,她哭不出来,也无法呼吸。吸进去的空气一团一团梗在喉咙里,越团越大。空气原本是无形无味、根本无法称之为障碍的物质,然而那一刻,她喉口的空气渐渐生出尖锐的棱角来,卡紧了血肉,还要强行翻滚扭动。于是那些棱角狠狠刺进血肉中,喉咙里涌上强烈的酸涩,鼻腔间竟然有皮肉腐蚀的味道。那股酸涩就像是硫酸,毫不留情地灼烧着她的喉咙,那疼痛既不钻心,也不腐骨,却像是流动的岩浆,无法控制,无法压抑。她尝试着发出一点声响,剧烈的疼痛立刻吞没她所有的声音,泪水自顾自地冲出眼眶,一片冰凉彻骨。在她就要窒息的当口,窒在嗓子眼的哭泣声终于爆发出来。她哭得心都揪起来了,五脏六腑像被吊着一样疼。然而这样的号啕大哭很快便停止了。她张大嘴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觉得胸口闷得厉害,迫得她弓起身子,风中残焰一般狂抖不止。
她说:“妈妈,我痛。”——对着虚空的黑暗说。
那样刻骨铭心的疼痛和绝望——温婉说得对,只有她能理解。
阳光很好,顾歆舒却觉得眼前白花花的一片,糊得厉害。突然额头撞上什么,她只觉得眼前黑了一下,整个世界重新清晰起来。
对面有两张脸诧异而迷惑地仰视着她,桌子上是一大碗很平常的什锦面。
一只碗,两双筷子,四只含情脉脉的眼眸,十根绞缠在一起的手指。多幸福的一串数字。
她撞上的是一家小面馆的玻璃。
她忽然想起来,今天一早她准时出门去盛文上班,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她既没有去乘轻轨,亦没有坐上地铁或是公交车。她只是恍恍惚惚地在街上走着,像游魂一样穿过人群,经过橱窗,走过湖泊……一个人,像是以整个城市为背景而表演的剪影,轻飘飘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满眼都是人,满眼又都是空落落的一片。
她没有吃早饭,当然到现在来说,午饭也没吃。她不饿,但是她觉得她应该吃一点东西。于是她走进这家小面馆,点了一碗最普通的阳春面。
阳春面,就是酱油汤底、连葱花都几乎看不见的光面。
顾歆舒挑起几根面条来,却怎么也送不进口,整个人像是呆滞了,挂着面条的筷子就这么横在眼前。她专注地看着它们,事实上又不是在看它们。她只是僵直而惯性似地保持着这样的姿势,似乎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
有人说,发呆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她为什么这么难受呢?
她答应了温婉,把何家讯逼回温婉身边去。
不过才过去几个小时,她却记不清自己是怎样答应下来的了。逼回去?一个人的心若真在你身上,那是怎么逼也逼不回去的。她原本是没有丝毫怀疑的,何家讯爱她。但是现在,她动摇了,她越来越不敢确定,为了他的事业,他的心还会种在她身上多深。她原就不指望他们之间会有什么确切的说法,但是她一直清楚他的心意。就像是飞翔在雷电风雨中的风筝,再无助,也记得有那样一只温暖有力的手,紧紧拽着那根线。而现在,那只手越来越不稳了,仿佛稍一迟疑,就会松开线,义无反顾去抓住他的前途。这种担忧不是因为他要和温婉结婚而生的。即便没有温婉,事情发展到此,也已经渐渐显出无可挽回的局面来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谁也说不清楚。若真说得清楚,人生也就不会这么无奈了。
她瞬间明白,她用以寄托勇气和希望的那个人,也许永远就不在了。
她同温婉说好了,她会彻底离开何家讯,她可以帮她把何家讯往回了逼。但是温婉必须尽一切努力帮助何家讯。那些她一直在做的事,那些她以后都不能做的事,温婉必须接下去。
顾歆舒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即使是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甚至令她厌恶的温婉而放下何家讯,她也不会出尔反尔。她把何家讯完全交给温婉,自然包括他放在她身上一切的期望——不管是感情,还是事业。从那一刻开始,她,顾歆舒,不再插手有关何家讯的任何事情。
是谁说,誓言总是很轻易就能说出口?对温婉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她痛得五脏六腑都移了位,牙齿几乎要在嘴里咬碎了。
她不要和他再见,她不要他们的人生从此两不相干!
然而她明白,他的的确确是非娶温婉不可的。他现在最需要的人,是温婉。她也明白,如果她不能够给温婉信心,温婉也是绝对没有信心毫无保留地帮助何家讯的。
她记起调离裕雄那天同何政鸣同车的时候,何政鸣那样无力而悲凉的眼神。那个时候她相信,何政鸣如此对待何家讯一定有他的原因。但是此时此刻她真的很想冲到他面前把那个原因问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到底是怎样天大的秘密让他这样逼迫自己的亲生儿子?
那碗面条顾歆舒一筷子也没动。出了小面馆,她忽然觉得晕眩。她并不认为自己柔弱到少吃两顿就会晕倒的地步。然而走了几步,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摇晃起来,竟然就迈不开步子了,两条腿陡然软塌塌的朝地上瘫下去。
身后突然有一只手托住了她的胳膊,轻而易举地把她扶正,耳边就响起一个悦耳的男声:“顾小姐,你没事吧?”
她恍恍然回过脸去,眼前忽紫忽黑了好一阵才看清眼前的人,勉强牵出一丝笑,轻道:“玉先生,我……”话还没说完,她身子一沉,又往地上坐下去,有晕眩的感觉从脚底涟漪似的一圈一圈晕上来,喉口一咸,几乎要吐出来。然而她只是干呕了一下,根本吐不出东西来。
玉仲启拉住她,蹙眉道:“你是病了吧?来,我送你去医院。”
方才他在堂志锦庄办事,一出来就看见顾歆舒扶着墙跌跌撞撞地往前冲,也不看前面,头直往地上栽。他连忙停了辉腾,下车来扶她。
“不用……我没事的……”顾歆舒摇摇头,想站直了,整个人却完全倚在玉仲启身上,使不出半点力气。
“去哪?我送你一程。”她虽然虚弱,玉仲启还是从她眼睛里看到不容否定的拒绝。这个顾歆舒,还真是有点像阿蔚,都那么倔。
“不用了。”顾歆舒再次拒绝,一努劲自己站正了,脸色比先前好看了一些。
玉仲启只好作罢。当然,他已经打算好拨打闫涛蔚的手机了。他转身离去的时候,顾歆舒忽然又叫住他。
“……玉先生,你能带我去什么地方转一转么?随便什么地儿,只要别在这儿,别在珉茳。其实还是要在珉茳。我知道这样说有一点奇怪——我对珉茳太熟悉了,但是我知道一定有什么地儿我不知道。我想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转一转。有时候熟悉的空气会让人窒息……我这样说你能明白么?我……带我走,我在这儿呆不下去了,我呼吸不过来了!我……”顾歆舒努力使自己的话能够被理解,却依然语无伦次,说到最后,几乎是要哭出来了。
玉仲启静静看着她,面上一贯的闲散终于渐渐凝重沉稳起来。她在他面前近乎卑微地夹着肩膀,低声下气地求他带她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还是先前那个顾歆舒么?那个冷艳妩媚,像一朵饱满而清高的红玫瑰,却又冷漠决绝的顾歆舒?他朝她温和地一笑,柔声道:“上车吧,我带你走。”
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能把她带到哪里去,车子在市区转了几圈之后,他直接把她带回了玉锦山庄名下的玲珑嘉园。玲珑嘉园是一处面积不大的楼盘,玉氏开发玲珑嘉园本意并不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玲珑嘉园处在珉茳最南面的郊区,都是独门独户的小别墅,门楣雅静,全无商业气息。玲珑嘉园原本专供玉氏的VIP顾客度假休闲所用,后来市政府将经济开发区设在城北,经济重心转移,城南逐渐显得落寞荒凉。玉氏在城北新开辟了圣宸花园,玲珑嘉园也就逐渐无人问津了。
玉仲启选择了玲珑嘉园一号别墅作为自己小憩的据点,不过他自己平常也很少来。
“我想你需要静一静。这个地方还不错,没有人会打扰你。”玉仲启安顿好顾歆舒,准备离开。
“因为很久没人住,热水器可能有些阻塞,如果你要洗澡,记得把水先放掉一些。床头那台电话按一号键就可以找到我。你什么时候想要离开,我会派人来接你。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离开。”玉仲启轮廓精致的嘴唇一张一阖,悦耳的男中音在房间里低低地回荡。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这么婆妈。但面对的是弟妹,他也忍不住变得和阿蔚一样,想要把她的一切都照顾得无微不至——阿蔚当然是不会承认的,或者说,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待顾歆舒的态度。
顾歆舒久久不给他回应,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却见她面如死灰,两只眼睛有些骇人地瞪大了,狠狠抠在长柜上立着的一张照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