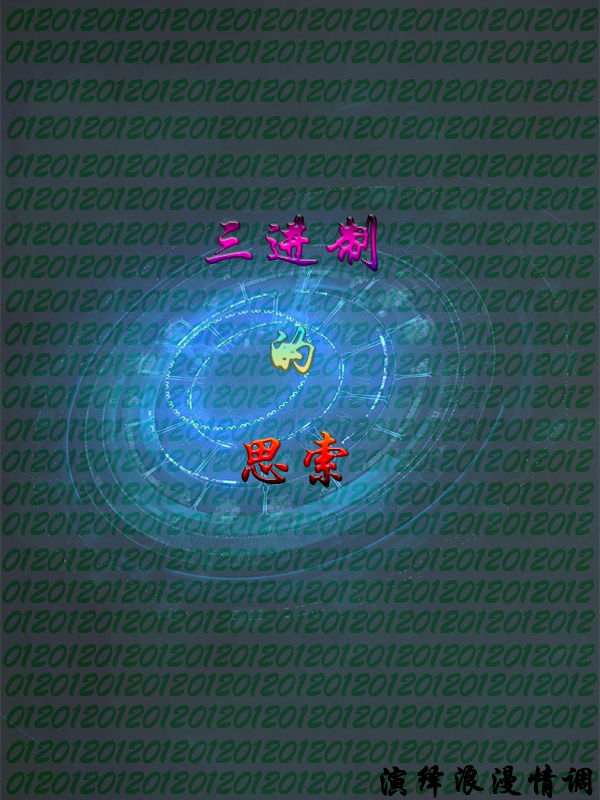她诚然不孝。可这,却是她至死也不能接受的。
她籁籁的抖起来。双肩被捏在宜敏掌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温暖。
而就在这一刻她突然明白,为什么宜敏会回过头来找她。孙宜敏不是没有朋友,而是再也找不到可以裸露心事的人。
她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猎人与猎物,更不是虎与伥。她们是瑟缩在山脚下求生的一对儿可怜虫。只有彼此才能明了各自的手法,路数,乃至阴毒狡计。她与宜敏,不是最终极的占有,却是彼此最最稳妥可靠的依赖。去哪里再找这么一个人,如果男人离弃了我们-----芳晴大惊,用一只手捂住宜敏的嘴,小心的说:“不会的,你会好的。我,也会好。”
宜敏靠在她怀里哭起来。芬芳柔软,却终究不是她所恋慕的男子,她所爱的那一个。芳晴将宜敏推远些,再推远些。她骇笑着对小孙讲:“可不敢让你老公看见。”
“管男人们做什么。”宜敏勇敢的扬起头说:“你若还想要杨志,就不必顾忌我。在他心里,我已形象尽毁。”
她不信,却不会再傻象从前那样掩饰着自欺。芳晴袖手眯了眼紧盯着窗外的树枝,淡淡说:“如果杨志听见你刚才的那一番话会怎样?”
“文字的力量是很骇人的,我笨,说不出来,只能抬了脚往前走。走到眼里视若无物那一日。从前的人也好,事也罢,我再也看不见,记不住,管不了。”这就是她从宜敏这里学到的,可惜苏楷听不见。若是听见了,小苏会怎么想,会轻视她懦弱么?是懦弱,而她一向就只是那个样子。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轻飘飘的将责怪掷在她身上。她从前会负起那些罪责,是因为爱。现在会逃,也是因为爱。是自爱,人若不爱自己,便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这样的教训,她已尝够,唯愿此生再不会有。
“你会好的。”她说。
“那你可会来?三天之后。”宜敏轻声说了个宾馆的名字。
“有钱人哪。”
“还好,他是外科。”
“那上次怎么在内科替你换药?”
“在这之前,他就注意到我了。所以,才托故跑过来。”
“这么浪漫。”
“嗯,他家里人也对我很好。”
是吗?芳晴转身温言道:“宜敏,若真是这样的对白,你不必再找我。你会有很多的朋友,可以聊天,可以调侃。往前走,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她说完冷了脸看宜敏强笑着一步一步向后退。
“我总归会等你。”
这世间的男子无不如此说,可她们都是女人。芳晴低下头,在微微的呼吸声里,是一个人的消失。
从此再不会有黑夜与白昼之分,在她心里,生命如被初雪掩饰的枯枝,是亘古的青灰颜色。如同徽记建筑上覆盖的瓦,在清泠的一声脆响下,是她的青春记忆与欢乐。那些随时会绽破的情绪,会爆发的热情,乃至覆骨的悲哀,此后都与她无缘,万芳晴会以最最合符规矩的方式,以及最最安静的面目走完全程。
谁会晓得她的过往?甚至连她自己也没力气再提。都不是光彩事,这世间的人,只会就事论事,也只能就事论事。因为这是最易明晰的所谓“黑白是非。”而那些个人的情感,一个人为自己的成长所付出的冤孽嗔痴,便如长发上尾掉的岔枝,在刻意的修剪下被除去。人都说只要过去了就会好,人都说只要蜕变了就会更好。可那些好,却是生生的剜下一团血肉敷了面目才整理出的妆容。会痛吧?芳晴一直在抖,自宜敏走后,每一夜,她都是在微微的轻颤中渡过。
冷的不是她的心,是她的人。
倦了疲了厌了,病毒便来了。
只得她自己陪着自己。在医院里,在人来人往的大街。寂寞似一杯水,慢慢的自杯口溢出来。然而,这是她无能为力的事。她帮不了,只能呆滞的看着。看那一杯水如何变大,渐渐将自己没顶。
溺毙的感觉其实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糟,因为肉体永远是超脱在精神之外。当老方从她身边走过,芳晴甚至能清楚的发出一声HI。而他定了定,象是发现了什么珍宝似的冲过来。然后一切皆妥,万芳晴检查打针交费拿药无一不顺。当最后一滴药水输进胳膊,她甚至有力气邀请老方外出用餐。
吃的是火锅,点的都是实在货。两个中年人倚在窗前,就两瓶啤酒,兴致勃勃的谈论时事财经美女八卦。关于过去,他们都闭口不提。光阴如覆水,还有什么比将息自己颐养快乐来得更重要。
所以,当他提出周日去做环保时她便毫不犹豫的应了。
不但应了,还认真打点。为此,她准备了全套装束。背袋球鞋水杯,一件大大的外衫上喷了斗大的“热爱地球”四字。是特意请人做的,喷字的那个小妹,以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芳晴。让她惊觉,原来环保不仅是一项高尚的事业,更是有钱有闲的消遣。
是几时她走到这一步,这个镜中的女子,苍白散漫。那些眼中曾有的热切倔强坚持执着乃至愚蠢,如今都通通让位于“我不在乎”。-----不是真不在乎,而是无所畏惧。还有什么能令她害怕,还有什么能让她心存疑虑。走下去,就只是走下去。带着一股被人剥皮抽筋后的泼辣劲儿,走下去。时光倒流三四年,如果昔年的自己,能有这股精神,那么,有什么不可以得到。不管是令人悸动的爱,还是辉煌成就的事业。即便不能全部拥有,却也绝不会在隔痒搔靴中错失再错失。
真可怜,叹只叹,那些相隔云端,如花美眷,似这般都付于似水流年。
因为这世上有的,并不只是聪明人。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上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也有似她这般蠢材,在刻意与无意之间,总是将时空扭曲,拉开一个距离,心在左,脚在右,神属不一,却茫然不知。也不知要迈过多少荆棘,淌过多少沼泽,越过多少山丘,才能真正看到风景。孤独的,因为曾流过的泪,见过的人,尝过苦,受过的痛,而从此裹足不前。孤独,便永远只能孤独。然而比孤独更让人绝望的,是那一点点懊恼失悔。原来人生完全可以是另外一副模样:只要再多一点点勇敢,多一点点坚强,多一点点自信果决,甚至皮厚,那么,她就不会在困顿于自我中蹉跎。
所以,她是埋怨父母的吧。所以,她不能,也做不到,与宜敏似的,义无反顾为父母倾尽所有。在她的爱里,在她的孝顺里,始终有一点顾虑,有一点迟疑。似一根刺,生生的硬扎在心尖上。不是不想拨出来,她的方式勇猛而热烈。可她傻她愚蠢,她不仅高估了亲情,更对所谓思想准则对现实生活中人精神的精响有着错误的判断。她总是听说,如果不是因为过去时代所造就的荒谬,那么,父母必定也是心地磊落,大方疏朗。正因为这个,老方才会对临终前的父亲说那番话,而宜敏也是因为这个,才能对自己的所为做出种种辩解。而这样的维护,不仅是为了父母,子女之于自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可为什么她不能,为什么全天下的人都能,却偏偏她万芳晴不能。
这是周日,有难得的冬日晴光。芳晴坐在街头小卖部前的长椅上,看碧天如洗,日起云舒。这一日,宜出行宜嫁娶,却独独不宜思考。但或许,哪一日都不宜思考。有道是人生烦恼识字始。那她的烦恼是什么,是这一点点执着的蠢意么?可这世上,是没有什么需要完全的看清楚,就象是验光师手上的眼镜度数,要比精准的测量退一点,才是刚刚好。可她,总是做不到完美的,恰到好处的退步。万芳晴天生出脚鲁莽,踩线过界皆为平常事。
她步履蹯跚的站起来,这是在约定的地点。是她来得早些,太早些。所以,才有机会坐着胡思乱想。想,昨晚发生的事,想,昨晚与万树德通过的电话。
堂哥守不住秘密,到底让买房装修的事泄了底。父母会冲过来和她算帐吗?照昨晚老万言词的激动程度来看,应该是的。
到时他会说什么,她又能应些什么。该说的话,昨晚她早已气极败坏的脱口而出,她对父亲讲:“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因为你太贪婪,不知反省。”
这样忤逆的话,难得万树德没有针峰相对以破口大骂。芳晴听见他在沉默一阵之后,冷静的高声说道:“你经过些什么?你又见过些什么?在我们那个时候,反省,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若死了,还会有你?”
芳晴坐着,把这最末八个字再默念一遍。时间不早了,她决定把这个鸡生蛋,蛋又生鸡的问题先抛至一边。暂时而已,终生却是不能。尽管她不知,究竟在何时,它又会以何种面目出现:夫妻?同事?工作?劳动?财富?分配?------只要她万芳晴依然存活在这些社会关系里,那么,终有一日,那些没有被解决的困惑,仍然会喋喋不止纠缠不休。
人类为了统一某一种价值观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真让人感觉不可思议。自五四起,不,应该比这更早。那些流逝的生命,在一种牺牲的名目下所隐忍的个人感情。才未尽百年,却已不可考。
而这样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
她去过黄花岗,自然晓得在那些苍严肃穆的景象所应激起的情感究竟是什么。可是,她做不到,更流露不出来。彼时,在她心里,所涌出的,唯有怜悯再怜悯。那些墓内的人,可帅?可曾有女孩子喜欢?可曾爱过亦或恨过?或是为自己天真的一点愚蠢而懊恼过?如今,在他们的长眠之处,是否真的愿意,安静的高卧在一道条目之下。如果上苍有灵,他们是否会跳出来大声说:要爱,要行动,要思考。
为了人类的福祉。
多么可笑。
芳晴拧过头,决定永不让父母知晓。
只要他们愿意,就让他们永远活在幻梦里。从此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钱是钱,见不孝便真是不孝。
她不会让他们知道,更不会对他们剖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文关系造就了今日的社会状态。如果走下去,再走下去,那么在未来,她又可能会经历些什么。说起来她不是不怕,可是一想到父母便心生一股孤勇。这难道不是“孝”吗?
她心里蓦地涌上一股杀机。却又在片刻间俱化做轻叹:说起来老万倒真是福气呢:说一种话,做一种事,抠一个理,再过十年二十年便可撒手万事不萦于怀。留下她,也只有她。除去寂寞,便是满腔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
芳晴低下头,身后有声音传来。
是一群男生在看电脑,屏幕上是王佳芝清丽的面容,小巧的嘴,一抹嘟起的嫣红,眼光潋滟,素衣简装,还不晓得,她轻轻一个点头,简单的一个承诺,会给历史带来些什么。其实谁又能真正晓得?走下去,都只是走下去。只当是自己的命运吧。
归根到底,谁比谁更好,谁又比谁更高尚。力量,自普通人里来,又到普通人里去。如站在悬崖顶上所观的海浪,远看无波。
可怜易先生。
她眯了眼,看看时间便连忙转身。而此时,一列婚车,正声色不动的自她身边如游鱼般滑过。芳晴瞥一眼,顺手摘下长椅上的一片树叶,向远远过来的老方挥手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