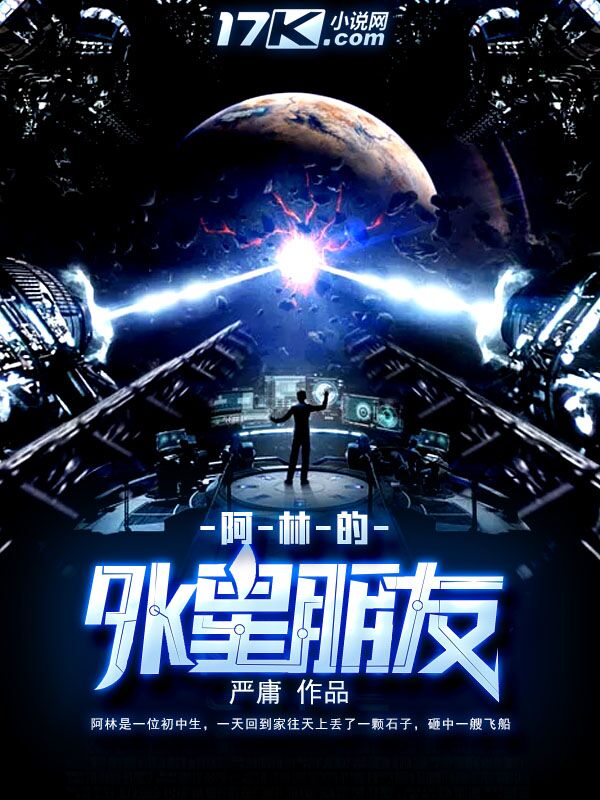从那天开始他们就熟了起来。
是李浩勤与万树德。
芳晴再一次听见小李的名字是在二天之后,她下班回来,一脸倦容,气色是越发的差了。一进屋就随手把包往床上一扔然后问道:“爸呢?”
“和李浩勤吃饭去了。”
芳晴被老左苛责了一天,要大脑闪停再启动之后才能想得出那人是谁。憨厚的国字脸,谦和的表情,可即便如此她也想不出一个老头和这样一个年轻人有甚谈资,她眉头紧拧,语气便差了些:“吃什么饭,爸也真是。”
李明彩反应很快的驳回去:“难道老年人就不应有社会活动啊?”
“谁说的,楼下都有啊。”
“除了麻将馆就是麻将台,你爸哪爱这些,连个阅览室也没有。”
“厂里现在也没这个。”
“从前有的。”李明彩握着只碗坐下来。
那是家曾经牌子响亮的空调厂。其全盛时芳晴还小,却也还记得数十辆载重大卡等在厂子门口拉货时的盛况。三三两两的司机或坐或站一脸倦容的守在磊门口,大孩子们,已颇懂得些矜持,完全明白稳固兴旺的工作单位及家庭经济对他们未来的意义。他们目不斜视面带骄傲的走在厂区里,身后跟的是一群半大的丫头小子。迈着两条短腿流着涎水的芳晴是那群人中年龄最小的那一拨,她完全不知道她所见证的是国家民生,未来,经济,社会及人文风貌的大变迁。对芳晴而言,她不过是工厂党办“万秘书”与工会“小李”的女儿,在她还不及长大细细咀嚼这样一个身份对她的作用之前,人生的背景已倏的一声置换。轰雷阵阵,风雨之后留下的不过是破败的厂房,凋蔽的宿舍,焦虑及痛苦的面容,那时候芳晴已经在中学住校,老万与老李还未满五十,从理论上讲,他们仍然拥有国家退休政策所限定范围之内的劳动能力。可天知道他们还能做些什么,或许是纸上谈兵,或许是闭门造车。在数周一次的家庭团聚日里,这是敏感的不能被触及的话题,除了在给钱的时候,每一次伸手对芳晴而言都是一次凌迟。她彼时尚未成年,却已经有了月经胸部及暧昧难言的眼神,然而贫穷象一张可耻的膏药紧紧贴在她额头,从此她便拥有在这场大变迁中所唯一承继的精神财富:总会在不经意间感觉到恐慌。
此刻也是如此。
万芳晴用手杵着下额,听李明彩一仟零一次讲起从前。
从前的福利,从前的工资,从前的地位------他们能有什么地位啊?不过是被人施舍混一口饭吃。然而这样的话,芳晴照例说不出口,她只是温驯的微笑着附和道:“如果那一年被兼并就好了。”
是外资,都已经来谈了好几次,却因为厂领导架子拉过了头而转投了别家。就这样错失良机而后倒闭。对普通人而言,这也就是他们所能看到的全部了,能提供稳定收入的厂家以及个人,至于资本背后所持有含义和对未来的影响,这不是高手才干的活吗?身为普通人,她(他)所能做的不过是为三餐一宿顺势应命。
可为什么这事所带来的后果要由他(她)的子女来承担。
从经济上到心理上。
成年之后的芳晴得孤独的坐在一间廉价屋里,听母亲牢骚以及指责。李明彩刷好碗,敏锐的对芳晴指出问题的最核心部份:
“小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从来不出去交际。”李明彩说。“你不出去交际,不扩大自己社交圈,怎么可能找到更多的机会。你都快二十四了,连个男朋友也没有。我象你这个年纪,”李明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再度把题目转到女儿头上:“当然你在大学里谈过那个不算。”
长夜无聊,芳晴如何肯错过这样的八卦。她兴致盎然的从床上一跃而起,对母亲追问道:“你象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怎样?”
“说你呢,扯到我身上干什么?”
“有多少人追求你?四五个,还是五六个?是三角恋吧,老爸最后是怎么胜出的?唱歌?在你家楼下坚守?有没有写过血书,还是,你追他,呵呵,这个可能要容易些。”
李明彩狠狠的瞪了女儿一眼,说:“哪有你说的这么下流,我们那个时候纯洁得很。”
下流?纯洁?
真正的下流是无视人最基本的情感与生理需要。
人说我要“吃”,它那边回答“赶英超美”;人说我要“住”,它那边回答“拉动内需”;就连爱,原来在母亲这一代人嘴里都有“下流”与“纯洁”之分。芳晴不愿接受荼毒想说实话,或许是因为万树德不在的原因,她今天的话说得格外流利:“妈,不是我不愿意出去交际,是因为我没有钱和人交际。”
“现在外面是什么价格,奶茶至少四块一杯,套餐二十元一份。我出去玩,总不能干坐着让人付帐吧,AA是最起码的。以我的薪水,就算不供楼,我一个月也只能节约的出去玩几次,余下的钱除了吃饭还不够应付伤风感冒。”
芳晴说到这里,把头从李明彩面前挪过去。
母亲的眼睛又大又亮,沉默而轻蔑。
淡淡的,是一种用言语所无法描述的表情,唯有轻蔑如同汤里的花椒,麻麻酥酥的刺激着人的神经,向人证实它的存在。
这是芳晴自成年来第一次开口诉苦。
倒象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曝不得光的亏心事。
她感觉到些微的恐慌,象是感冒前夕灼在人咽喉的一口痰气,痒痒的只想咳出来。
果然咳了。
气浮脸肿。
李明彩用力拍打着,为芳晴倒水递茶送毛巾,母亲的慈爱仿佛一如从前,连唠叨的字句也是从那些岁月里一字不拉的漂流过来:爱惜自己,注意身体。那些被絮语包裹着的时光昏黄且脆弱的在芳晴脑海里跳动催眠。她慢慢睡过去,睡得再沉,身体有某处却仍被结实有力的敲打着不放:如今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责任了。
我能承担得起吗?
她能靠得住吗?
万树德深夜回家,看见的就是这孤单夜守的一幕。
李明彩委屈得象个三四岁的孩子,一把扑到老公怀里。“怎么办呢?”她问。“晴儿她太小,担不起啊。”
“我晓得,我都晓得。”万树德安慰道。
做父亲的还有什么不明白。
灯光下,万芳晴身体弱弱小小的在行军床上蜷成一团。眉心紧蹙,双手握成拳头放在枕上。她的表情说不上痛苦也谈不上有什么愉快,只是睡着,倒象是没有了心。想起这一生的坎坷和女儿未知的命运,万树德不由得心如刀绞。他放下帘子走到窗前,也不过就七八步,而他们夫妻就用草席在窗下搭了张地铺。地湿潮冷,李明彩把老伴扶过来坐着,一点一点为他揉搓风湿药。看老万脸色还好,她便试探着问道:“那个小李怎么样?配得上咱们小晴不?”
万树德借着老伴的手劲轻轻的哼了一声,过一久才说:“一般吧,他家里的情况我已经摸清了,跟咱们也差不多。所以把钱看得很重。没想到吧,吃这餐饭,居然还真是我付的钱。”
“真的?”李明彩不信却又不得不信。
现在的年轻人哪,真是一点礼数也不懂。
“多少钱啊?”她啧啧问道。
“就一佰多,不过,这小子还算懂事,没吃完的通通打包,他还想让我带走,我哪肯要啊。带回来,岂不是丢了小晴的脸,将来小晴在他面前就不好处了。”
所以,就算是倒贴也得付。
父爱如山。
万树德用眼神把李明彩脸上的心疼逼回去,他切切叮嘱道:“咱们也不能在一棵权上吊死,得多选,最好是海选。王婶的闺女的表哥那事你可要抓紧了,争取下周让孩子和那人见个面。至于小李,我们可仟万不能采取主动。”
“那这餐饭岂不是白请了?”
这怎么可能,万树德瞅了老伴一眼,悠悠闲闲的倒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着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