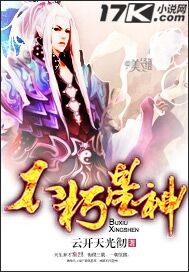以善之名行恶,与恶无异。
……
……
夜色如墨,掩护着无数罪恶。
破旧的屋里只有父女俩。
十九寸的彩色电视机在播报二十二点的整点新闻:今年的狮子座流星雨如期而至;绣城大学天文台再次观测到宇宙射线异常;本市连环杀手最新案情追踪;某小学路口发生一起九车追尾的恶**通事故……
那个半醉的父亲打了个酒嗝,斜眼看向如花似玉的女儿,嘴角浮起淫邪的笑意。他习惯性的抓向酒瓶,却抓了个空,扭头看时,他的女儿乘机逃出了家门,没有半点犹豫。
“死丫头,早晚都得给人骑,就不能让你老子先骑几天?”
他骂骂咧咧的起身把往里灌风的门关紧,摇晃着回到了床上。
逃出家门的女孩走在昏暗的楼群间,脸上挂满泪,不停的风干不停的流淌。这个城市的夜依旧繁华,行人如织,但却愈发令女孩感到孤独,她不知道该去哪里,茫然的绝望。
停下脚步时,女孩发现自己到了绣城公园。
绣城公园其实是座山,没有围墙,山上林木茂盛,小路曲折穿插,因为种植了大量耐寒植物,所以即使冬天也无法一眼看到顶。绣城市的年轻恋人们都喜欢在草木深处做一些不太需要光亮的液体交流的事情,因此绣城公园也被人称作‘情人角’。但是最近绣城公园却门可罗雀,因为绣城市出现了一名连环杀手,专杀不喜欢光亮的情侣,在小巷中,在地下车库,甚至在电影院里。所以绣城公园几乎成了禁地,虽然绣城公园并未发生一起血案。
女孩抹了把泪,仰望天空,一颗流星正寂寞划过,在天边一闪便消失了。女孩努力缓了口气,胸口仍旧压抑的难以忍受,她犹豫片刻,决定上山。
山间的碎石小路倾斜向上,女孩几次停住,可心头有种奇异的惊悸,冥冥中仿佛听到了命运的召唤,她的眼睛亮了起来。或许有奇迹在前方等待着她,神仙或穿越,再不济是一箱钞票或白马王子,哪一样都比回到那个冰冷无情的家要好。因此她只能向着山顶前进,却不想失望后再向哪里去。
女孩的额头冒出晶莹的汗珠,在这寒冷的冬季。
山顶的空地边有一个人影,隐在黑暗中。
女孩的幻想刹那破碎了,她清醒过来,想到了新闻中刚播报的连环杀手,还有同学间流传的那些打印出的被害者残缺尸体的画面,血液里瞬间填充满不安,此刻女孩的心中只剩下恐惧。
那个人影呆立不动,似乎并没发现女孩的存在。
或许只是个等待爱人的寂寞的人,不必害怕,毕竟在那样暗的地方甚至连是男是女都看不清。
女孩这样想,并悄然后退。因为要看下山的路,女孩回头看了眼,再转过来时,那个人影不见了,女孩顿时紧张起来,惊恐的四处张望。
“你在找我吗?”
一个没有任何语调的男声在女孩背后响起,嗓音并不响亮,却令女孩几乎跳起来。她回过身看去,月光下站着个清秀的姑娘,一身深色灰蓝校服,俏皮的短发,颈间还挂着根断掉的上吊绳,脸上却有淡淡的笑意,一双眼睛明亮的仿佛月光。
“呵呵,你在找我吗?”
女孩向后跌倒,惊恐的盯着眼前的姑娘,手脚并用的爬离。
那个姑娘依旧在微笑,而她的声音也依旧是没有任何语调的男声。
“咳咳,你在找我吗?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不过你就糟糕了,真遗憾,你还这么年轻就要死了。或许,我该告诉你我的名字,如果有地狱,记得去告我一状吧!我叫王艳秀。”
王艳秀的声音变回了女人特有的嗓音,透着妩媚娇柔,勾人魂魄。
女孩的眼被泪水蒙住,她从未如此害怕过,甚至被父亲**时也没有过这样的恐惧,心跳的手脚酸软,无法站立。眼前明明是个比她还小的女学生,但却给她一种死亡临近的威胁感,连逃跑的勇气都消失了。
“我不认识你,为什么……”
在她不停放大的瞳孔中,王艳秀清秀的笑脸靠了过来。
绣城公园不染血的纯洁史成为了过去。
这个夜晚注定不太平。
绣城市轻工学院。
柯明又被403宿舍的人欺负了,而且欺负的很惨,他被塞进教学楼阴暗的地下室,就是那个传说闹鬼的地下室。
“我说杯子,这小子会不会吓傻了?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
“靠!你倒把嘴堵上说句话来试试?”
外号叫杯子是403室的舍长,本名戴佐丰,副班长,和他说话的叫张文宝,是语文课代表,两个人都是以欺负弱小为乐的人。
隔着厚重的实木门,五个不良少年放肆的大笑,门的这边,黑暗中寂静无声,没有哭泣或求饶,死一般的静谧。而黑暗中有一个欢乐的身影,他在无声的舞蹈,如飞天,又如夜魔,忘我的舞着。
“死了没有?”
或许是太过安静,戴佐丰不安的拍打门板。
门的另一面,舞者以一种怪异的姿势停住,缓慢的扭头盯向门外,仿佛厚实的门板并不存在。
戴佐丰正要再拍门时,突然莫名的心悸,就像被猛兽盯上了,耳边还似乎听到一阵铃声,哗哗的围绕在他四周。戴佐丰的手虚悬在门板上颤抖,拍不下去了。
“杯子,你没事吧?”
张文宝察觉到戴佐丰的异常,踢了门一脚,刺耳的声响把戴佐丰吓了一跳。
“靠,你有毛病啊?想吓死几个!”
戴佐丰说,身体却悄然后退。张文宝不解的靠到门上,听里面的响动。
门的另一面,舞者机械的扭动腰肢,以非人的动作移向门口,只刹那就到了门前,他停下,身躯如蛇,轻轻的将耳朵贴到门上。门内门外,两个人的耳朵隔着一层木板,贴到了一起。
“这孙子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张文宝说着,并将耳朵贴的更紧了。
就在这时,门里响起轻微的一声拍门声,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一声比一声响,到最后仿佛门里的人在用铁锤砸门。
张文宝连退几步,和戴佐丰等人站在了一起,面如土色的看着晃动抖落尘埃的门,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在几个不良少年准备逃走时,砸门声却停了。
“妈的,肯定是柯明这孙子在装神弄鬼!”
戴佐丰声音发虚的说,犹豫的向前迈了一步,他在试图挽回作为老大的尊严。可他的第二步还没迈出,一声巨响,地下室的门被整个砸飞,把戴佐丰撞出七八米,倒在地上**不止。
张文宝胆战心惊的扭回头,看见柯明单足站立,侧着身子,耳朵似乎贴在什么东西上,一只手停在头顶,另一只手手心向上摆在腰后。那模样仿佛泰国的舞者,又仿佛刚从黑暗中孕育出的妖魔。
柯明的脸慢慢转正,一双漆黑的眼睛好奇的望向眼前的几个不良少年,嘴角似乎浮起笑意。
“人类,美味。”
当毫无语调的声音从柯明嘴中发出后,张文宝崩紧的神经终于断掉了,他和身后的三人尖叫着转身就逃,在跑过刚爬起来的戴佐丰时,他犹豫刹那,抓住旁边的人上前架起戴佐丰,五个人惊慌失措的逃出了教学楼。
柯明站在原地,扭动腰肢,退回到黑暗中,不停的舞着。
“人类,美味。”
柯明再次重复这句话,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钟寿从教师宿舍出来时,看到本应在值周的几个学生从教学楼里跑出来,神色慌张。他看了下手表,现在是晚上二十二点十九分,这些学生大概又在值班室看鬼片,然后把自己吓个半死。
像是许多年前,钟寿在警校时也干过这种事。
钟寿一笑,回头看向教师宿舍那盏孤亮的灯,心头涌起无奈的酸楚。
钟寿的妻子万芳媛是轻工学院的教师,而他今天来是谈判的,他们正准备离婚,在划定财产归属问题。两个人都不想要房子,却对家中的那四只猫情有独钟,一只名叫大王的暹罗猫,一只叫听听的折耳猫,一只叫摸摸的虎斑猫,一只叫掏掏的临清狮子猫。
谈判是咬牙切齿的,唾沫横飞的,指舞如魔的,毫无美感的。
如果没有电话打断,钟寿与妻子万芳媛的谈判仍会演变成全武行,而背动挨打的人也仍会是人高马大的钟寿。
钟寿是一名人民警察,时任刑警队长,脾气火爆,但对妻子万芳媛从来都是柔风细雨。万芳媛不孕,因此婆媳关系十分恶劣,钟寿整天忙着化解矛盾,受着无穷尽的夹板气。可即使如此,他们的婚姻仍走到了头。钟寿想不明白,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又或者是哪里做过了头。
同事们总说钟寿对妻子好过了头,偶尔也该强硬些,女人就是喜欢受虐的动物,喜欢被所爱的人从肉体到精神一齐征服,不然就没有安全感。钟寿一直认为这是扯淡,新时代了,女性应该得到平等尊重,是半边天了,不能所有事都由男人做主。但事实是他的同事们婚姻美满家庭幸福,而他这个五好男人,却要离婚了。
“难道要我来一次婚内**?”
钟寿的头隐隐痛起来,他走向自己的车,思维转回到连环杀手的案子上。
刚接到的电话中,同事杨杰兴奋的说抓到那个凶手了,是在犯案现场。听到犯案现场四个字,钟寿的头当时就痛了,这意味着今晚又没觉睡了,虽然杨杰说抓到了凶手,但钟寿对此不报多大希望。
一个每隔九天杀两人,连杀八人却一点线索没留下的凶手,可能在犯案现场被抓住吗?
钟寿发动汽车,带着难堪的心境离开轻工学院,驶进黑夜。
钟寿回到局里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多,路上给同事们买了夜宵,顺便调整心态。同事们都知道他今晚和老婆摊牌,如果灰头土脸的回去,那也太没面子了。
尊严啊!男人的尊严啊!
钟寿对自己说,对着后视镜练了半天虚假自信的微笑,终于下了车。
出乎意料的是,局里只有值班的人在,其他人都去了案发现场。
“钟队,你怎么才来啊?他们带着那个豆腐王子去指认现场了。你没瞅见,真是绝了,这孙子怎么说也有四十了,结果杨杰刚拍了一下桌子就吓得什么都招了。顺带招了其他几起案子,埋尸地点。这下好了,一下子能并结好几起悬案,年终奖算有着落了。我说钟队,怎么又是传说中的咸猪手?我现在一看见这东西就反胃,您留着自己啃吧!”
值班的周贺军接过钟寿买的夜宵,一脸兴奋的说,其他几个值班的都聚过来翻看钟寿买了什么好吃的,然后一哄而散。
“嘿!还挑食!要不是看你们几个都饿瘦成这德行了,我能买咸猪手吗?呸呸,都是让你带的,什么咸猪手?还变态色魔呢!于晓慧,一会把完成的口供送我桌上。”
钟寿正准备去厕所,刑警队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仿佛传说中的预感,钟寿皱着眉头停住,回身看周贺军接电话。
周贺军抓起电话,片刻后他的脸色暗了下去,越来越差,一连说了几个什么?最后连表情都忽略了,只剩下混合着惊诧悲伤愤怒到极点的木然。他试图将电话交给钟寿,但手指却越来越用力的抓住电话,似乎要把那灰黑色的塑料壳捏碎。
办公室里的气氛顿时变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那还握在周贺军手中的电话上。
钟寿心中不祥的预感清晰了,甚至要跃出胸口。他从周贺军手里夺过电话,沉声问出了什么事。
电话那头是断断续续的喘息声,仿佛随时会断气。
“钟队,我们上当了……刘雅是凶手……都死了……我对不起……大家……”
钟寿听出来,那个绝望的声音是杨杰。
“混小子,给我撑住了!你们在什么地方?我去接……”
钟寿的话顿住,因为电话那头的喘息声被骨头破碎的碾裂声响取代,最后的惨叫根本没有发出,一个如兽般狰狞的笑声在不远处响起,嚣张至极。钟寿站在那里不动,只觉得血液都凉了,分不清是因为愤怒还恐惧。
“你是谁?”
钟寿大喊,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发出这一声怒吼几乎用尽了他全部的力量。
“我是谁?我也很想知道,你能给我那个答案吗?渺小的人类,或者是另一个……”
那个兽般的声音贴近了已跌落在地的手机,忽然间有些落寞,孤独的令人心伤。只是语调分不出是男是女,诡异莫名。
“我……你以为你是谁?玩具的主人吗?我要宰了你!”
钟寿不等那人说完就歇斯底里的大叫着将电话丢出去,但手仍在不停的抖。他不会想到,无意中说出的无理性的话有多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