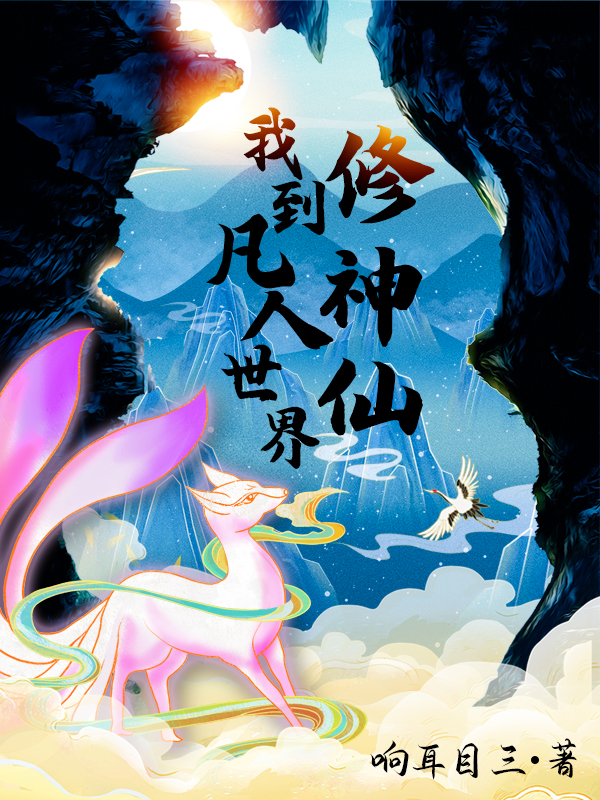开门后,她先伸手摸开门边的电灯开关,清晰的一声“啪嗒”响,房内顿时洒满了橙黄柔亮的光。
她一只手扶着门框换拖鞋,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地上,不好意思地笑道:“你就直接踩进来好了,我这里没有男式的大拖鞋。”
他睁大困倦的眼扫视了一遍屋内,简单的一室一厅,不大,却是干净,整洁,地上铺了明黄色的木地板,赤脚踩上去的话,应该不会太冷。
而他现在,也只想快点走到房间正中的那张绒沙发前,坐上去,好好阖一阖眼。
于是他脱下鞋子,只是穿着袜子踩上地板,有点凉,不过并不冷。
她正关了半掩的窗子回来,一看到他赤脚的样子,不由低声叫道:“你已经感冒了,这样会更严重的……”
可也知道自己拗不过他,只好快步走进卧室找拖鞋,找来找去,也只有一双毛绒的套头暖拖鞋看着大一点,她拿出来想要给他换上,却是看到,他已经坐在沙发上,蜷着身子睡着了。
她的脚步顿时轻了下来。
“文景,文景,”她轻轻走到他身旁,俯下身,低声唤道,“去床上睡吧?”
他真是睡着了,几绺墨黑的发落下来虚虚遮住了眼,隐约看得眉头微微拧着,鼻息因为感冒不太通畅,显得有些微地滞重。
她的心,登时就柔软下来了。
她轻手轻脚进房间,抱了被子出来,仔仔细细给他盖上,丝绵被子够大够软,不但包住他的脚,连肩颈处也掖得严实。
然后,她蹲下身来,屏着呼吸,静静看他的面庞。
已经五年……不曾细细看过的面庞。
他们还没毕业的时候,周末有时候会去爬山或是去校外玩,临近考试了,她就带了复习资料,一整天都窝在教学楼里复习。
他也带了课本来看,可因为脑子太好使,功课都不用多费心费力,于是狠命看狠命记的人只是她,他就坐在旁边看小说看杂志,看久了看困了,身子一俯,就势枕在课桌上小憩。
她看书看累了,刚想打个呵欠,目光一转就看到他正枕在旁边睡。
平日里冷傲的一双眼已经全然看不到了,墨黑的发轻轻落在英挺的面庞上,眉似远山,鼻高且挺,薄唇轻微阖着,是极健康漂亮的粉红色。
他真是能吸引别人的目光,经过旁边的女生会脸红心跳地望他,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艳羡地看她。
她看得久了,玩心大起,就把纸巾撕成小条去挠他的鼻孔。
他努力闭着眼装睡,先是眉头轻轻跳,终于是忍不住了,骤然睁眼,一把抓住她的手,呵着气挠她痒痒!
……她想着眼眸微弯,轻轻笑起。
那时的她和他,就是这么近的,近得能感觉到相互之间的绵长鼻息。
不过,现在,他是真的睡着了,即便再近,却也不会在她的凝视之下,骤然睁眼来吓她。
以前的他,还是个大孩子;现在的他,已经成熟内敛。
默叹一口气,她揉揉有些酸涨的膝盖起身。
她抬头看一眼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晚上六点多,肚子早就饿了呢。
他吃了药睡下,一会儿醒来,应该也是饿的吧,那么,也要准备一下晚餐了。
她轻轻抿起一个笑来,想了一下,拿了手袋和钥匙,轻手轻脚走到门口换鞋,再熄灭灯,关上房门下楼。
一出楼道,她马上小跑起来,微薄的路灯光下,依稀能看到自口中不断轻喘而出的白色雾气。冬天的夜那么冷,可她的心里却是高兴着,快乐着,有一股说不出的力量源源不断地供给她温暖,让她小跑在这一片老旧的住宅楼前,听得脚步“哒哒”,手中的一小串钥匙“哗哗”,还有散落的黑发在外套上一甩一甩地轻声“啪”响。
很快就跑到刚才的超市,她在门口停下喘了口气,又小跑着进去,快速拣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再小跑到前台结帐。
恰好也是在刚才的结算台,超市的服务生认得她,看到又是她,不由轻轻“咦”了一声。
服务生大概在奇怪,这个小姐才来买过菜,怎么现在又跑来了?
“刚才买的东西不够,”她因为小跑而微微涨红了脸,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家里……现在多了一个人。”
服务生没有多问,了然地冲她一笑,动作麻利地帮她点算物品。
提了袋子,她又开始小跑着往回,东西重了一点,可心依然是轻快,涨满了隐隐的欢喜。
到楼道口时,她停下,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路灯下停着的那辆银灰色的车子,觉得真是好看,在橙黄的灯光下,静静闪烁着细碎的银色光芒。
一切都是在静悄悄中进行的。
她蹑手蹑脚地进屋换拖鞋,再蹑手蹑脚地进厨房,开始动手准备晚餐。
一室一厅的房子太简易,她有些懊悔之前没在厨房和客厅之间安一道隔门,于是只好动作一轻再轻。
她先淘米,以前听老人家说,米不能淘洗得太厉害,不然就缺失了营养,于是她细细洗了一遍,再粗粗淘两遍,最后小心倒入电饭锅里煮。
袋子里的黑鱼不安地挣扎了几下,她怔了一下,把黑鱼自袋中倒到水槽内,开了水喉想清洗,可黑鱼却是愈发地动弹起来,她有些惊慌地探出身子看了一眼客厅,见他依然酣睡,这才松一口气,回过头来,举了菜刀,一手按在刀背上,狠了狠心,一刀重重切了下去!
幸好刀子没有打滑,她费了很大的力,才把时不时挣扎一下的黑鱼切成了两半,手上沾满了鱼鳞和黏液,还有一丝一丝的猩红的血,现场很是惨不忍睹。
从来不曾这样杀过一条鱼,以前也是要用刀背拍晕后再下手,这次弄得这么狼狈,就是只怕声音太响惊吵了他。
对于睡在客厅沙发上的他,她的心头,忽然就泛起了温柔的海潮。
接下来就好办多了,她细心地刷鱼鳞,清洗鱼身鱼肚,水喉始终流着一条细细的水柱,灯光下清澈通透。
片鱼肉的时候,刀子却是开始打滑了,时不时就碰到了自己的手指,她举起来在灯光下一看,好像只是一条细细的白痕,一点都不疼,于是,低下头,继续操刀片鱼肉。
然后准备虾仁,葱段,姜丝,还有切得细碎的碧绿的芫荽。
这时,电饭锅里的米粥开始“咕噜噜”冒泡了,她再等了一会儿,关上电饭锅,将粥盛到锅子上,多放水,开火熬煮。
差不多火候了,放入姜丝、虾仁,还有厚薄适中的黑鱼片,加入调料,小火慢慢熬。
头顶排油烟机的灯光静静洒落下来,是黄晕的光,铺洒在雪白的粥面上,仿佛洒落了一层细密的金粉,不是很闪耀,可却温暖而动人。
她就拿了一把勺子缓缓搅拌,轻轻的一圈,两圈,三圈……搅得那一层金粉流成了一条蜿蜒的河,河面上是夕阳金子般的碎光,有柔和的花香和青草香,清甜中隐藏了温柔的诱惑。
粥里或隐或现的鱼肉已经雪白,虾仁也同样,白里还带了淡淡的粉红。
她舀了一点粥尝味道,再放一点调料,最后撒上碧绿的葱丝和芫荽碎。
她笑了一下,很好看。
忽然听到客厅里有动静,她忙跑了出去,见他正掀开被子坐正,眼睛已经睁开,可尚有一丝未清醒的混沌。
“你醒了吗?”她微笑着,轻声问道,“觉得好一点了吗?”
他轻轻阖一阖眼,再睁开,眼里已经是澄澈的清明。
“现在几点?”他的声音微哑,手下是松软的丝绵被,触手温暖柔软,他发觉自己竟然十分留恋,以至于舍不得完全推开被子站起。
她抬头看一眼墙上的挂钟,“快七点了,”她又看向他,“你饿了吧,我做了粥,要不在……”
放在一旁桌上的手机却是突然响起,她抱歉地冲他一笑,快走几步去接,心里其实还在庆幸他睡着的时候没有电话。
“嘉心,”手机另一边是林南风的声音,带了一丝愉快的笑意,“你吃饭了吗?没有的话我们一起去外面吃,好吗?”
“呃……我是还没吃,不过……”她迅速抬眼望了他一眼,他依旧坐在沙发上,半掩着被子,低着头,大概在翻看手机。
“南风,要不下次吧,”她捂了手机低声道,“……我晚上有点事,走不开……”虽然知道林南风在手机的另一头根本看不见,可她还是红了脸,声音也有些微的颤。
这样的撒谎,她觉得很愧疚。
可她不得不如此。
“那好吧,下次就下次,”林南风的声音稍显失落,不过还是轻快道,“最近天冷,如果外出多穿一点,不要着凉了。”
她心里更愧疚了,匆匆和他道别,然后挂断。
转过身来,却是发现他起身好似要离开。
她有些着急了,上前几步就道:“你……你要走吗?”
“是,”他阖上手机,静静看她,“晚上有点事,现在已经七点,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她蓦然失落,可他说有事就一定是有事的,于是她勉强笑了笑,低声道:“那好,我送你出去。”
“不用,我自己下去就可以,”他穿着袜子,踩着地板快步走到门边,穿上鞋子后,抬头看她又加了一句,“外面太冷,出去的话容易着凉。”
“哦。”她讷讷点头,双手背在身后,轻轻的,又狠狠地绞着。
看他开门,她低声加了一句,“那你走好。”
他轻一点头,背影很快消失在楼道的拐角处,她呆怔了一会儿,忽然想到要给他感冒茶的,忙跑到房里找了出来,也顾不得换鞋子,趿着拖鞋就追了出去。
她住在五楼,追下楼梯的时候,刚想喊住他,却是听到下层楼道传来他的说话声。
“我就过来了,车上有些东西是要带给你爸妈的……”他温声道,“常忆,你怎么又跟我客气?”
那个声音略显一点沙哑,可却是清晰而执拗地钻入她耳中,硬生生地将她还未出口的话全都逼了回去!
她呆呆站了一会儿,然后,捧着大包的感冒茶,趿着拖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回到五楼,推开来不及关上的门,进屋去。
昏黄的灯光下,正中的沙发上还有他刚才盖过的丝绵被,她走过去,伸手一探,还有一点余热。
从窗口望出,刚好可以看到路灯下他的车子,片刻之后,那辆银灰色的车子缓缓动了起来,很快就开走了。
她回头,望到依然开着排油烟机上的小灯的厨房,灯下那锅还冒着一点袅白热气的鱼片粥,眼眶和鼻翼终于涨得酸痛。
可她没有哭。
她只是关了灯,走到窗边打开窗子,任肃冷的寒风汩汩涌入房内。
然后,她微微低头,看到有晶亮的水滴一样的东西,无声地落下,又在冷风里,被快速地吹干。
不清楚心里的酸痛到底是因为什么,可她忽然地,就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