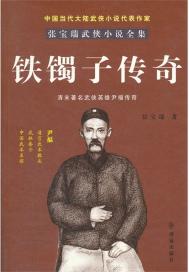看着展昭很谨慎地将赛凤凰五花大绑,白玉堂却很怀疑她跑不跑得动。不管怎么看,眼前的山贼头子都是一脸咳两声就会倒地断气的状态。
义妹啊……白玉堂仰天长叹,义奶奶也绰绰有余了吧。难怪取个外号也这么落伍,这年头早不兴什么凤啊龙的了。
展昭利索地给赛凤凰套上一个黑布袋,口袋上挖了两个洞,透出一双怨恨的眼睛。
“哦,你们开封府还真体恤犯人的颜面啊。”白玉堂叹息。开封府对犯人的福利就是好啊。
“我体恤的是咱们俩的颜面,两个大男人押个老太婆上街明天起早就谣言满天飞了。”展昭白了他一眼。
白玉堂咕哝了几句猫你很细心嘛。两人押着赛凤凰缓慢回到了开封府。
包拯托着下巴仔细端详着赛凤凰的满脸皱纹,良久,终于忍不住双手按在她脸上大力一扯,松垮的脸皮顿时拉成蝙蝠展翅状。
“这是真脸……”她口齿不清地说。
“失礼,失礼。”包拯尴尬地摸摸脸,忽然发觉自己的皮肤紧致有弹性,年轻真可爱啊,“老人家这么大年纪还做山贼,真有生活情趣。”
“……”
“好了,废话不说,你可以把骗来的钱都吐出来了。”包拯目露凶光,嘴角有不和谐的阴笑。
“被骗的人是我!”赛凤凰眼睛一瞪,吼了出来。
展昭和白玉堂对望一眼,读到了对方严重的冲击和疑虑。包拯转头想跟公孙策也来个默契地对视,发现公孙悠闲地抿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道:“很明显啊,不然她为什么要来告状呢。”
“公孙,你知道又不早说。”包拯有点哀怨。
“我也是刚刚才想到。买卖是合伙的,陈金一定是卷款潜逃,赛凤凰你,才想利用我们找到他,到时候,可以拿回你的本钱,是吧。”
“是也不是。”赛凤凰摇了摇满头银发,白玉堂忽然觉得心里有点抽。
“陈金是半山诸葛亮的表兄弟,新年拜年的时候打了个照面。我带着萝卜下山卖的时候遇上他,你们也知道,一个老婆子做买卖是很不方便的,何况我也很久没下过山了,不知道山下行情如何。于是陈金说可以帮我卖,谁知道他拿了萝卜出去骗人,骗来了钱就一走了之。于是我就来告状了……”
包拯点头:“你们各执一词。似乎都能自圆其说,很难分辨。”
“那就先关起来吧。”展昭提议,“关起来慢慢审……嘿嘿,公孙,大宋酷刑典放哪儿了?”活动活动手指,笑得一脸灿烂。
“这个……不能轻易打开,一开必要见血。”公孙摇摇扇子。
“太狠了吧,上次那个江洋大盗才第五刑就受不了全招了。”包拯惊讶地喔圆了嘴。
赛凤凰脸一青,两眼翻白,昏了过去。
“太不禁吓了。”包拯戳了戳她,向屋外招呼,“来人,把她押进大牢……”
“陈金隔壁。”展昭不等包拯说完接上一句。
公孙策赞许地微笑点头。
白玉堂目瞪口呆地看着奸诈对笑的三人,第一次发觉到,开封府简直比奸臣还奸,强盗还黑。
开封府大牢,风凉水清三餐保障,实在是避难度假的不二选择。赛凤凰躺在草堆里悠悠转醒,侧边高处有个声音喊她:“你醒啦,赛凤凰。”
她斜眼一看,一张充满了个人风格的大毛脸。“陈金!”跌跌撞撞地踉跄过去,抓着铁栏双眼怒火逼人。
“你怎么一把年纪还那么大火。”陈金退后几步,
“把我的钱还来!”
“什么钱?”
“你?骗?我?的?钱!”赛凤凰咬牙切齿地说。
“萝卜是你从我诸葛表弟那儿抢来的,要还钱也是还给他啊。”陈金掏了掏鼻孔,一颗鼻“咻~”弹在赛凤凰脸上。
“陈金,我好歹是五里坡凤凰寨大当家,你别当我老太婆好欺负!”
“大当家叫得倒是挺好听,我就是私吞了你的钱,你又能怎么着。哇哈哈哈哈~”陈金笑得全身毛发如波浪汹涌,一波又一波。
大牢角落里,四颗脑袋叠罗汉似的一颗压一颗正在偷窥。
“很明显了吧。”被压在最下面的公孙策脸挤成一团。
“可以定案了。总算水落石出。”被白玉堂压着的展昭有种强烈的感觉,想一拳打飞自己上面的脑袋。
“想不到这只熊看起来没脑子还挺狡猾。”白玉堂安心地把全部重量放在展昭身上,软乎乎的还真不错。
“钱啊,各位好汉。重点是钱。”包拯压低了嗓子说。
……可怕的安静……四颗脑袋散了开来……没错,重点不是抓到谁,谁是主谋,谁在说谎,而是——
钱在哪里!
四个人排排坐在大牢前的台阶上活动脖子。
“陈金肯定不会说实话。”转到第二个圈,包拯觉得有点眼花,瞟着身边两位大侠转陀螺似的扭动自己的头颈,一阵心惊肉跳。
“要不用酷刑吧,夹手指,钉指甲,老虎凳。”白玉堂兴奋地提议道。他其实很想见识一下所谓大宋酷刑典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其余三人极有默契地摇了摇头,三脸大义凛然地说道开封府不能做这种事情云云。靠,刚才说得那么热闹。白玉堂在心里小小鄙视了一下。
“我个有办法。”公孙策用他一贯不上不下,清凉淡定的语调飘出一句。
包拯激动地一扭脖子,喀喇,飙泪,僵硬,一气呵成。
包拯歪着脖子痛苦地无罪释放了陈金,并将凤凰寨一干人等全部捉拿归案。
月明星稀的晚上,风以特别清幽的姿态滑过,星光下的菜地里已经冒出了嫩绿的叶苗,展昭一边抚摸着嫩苗,一边教着水。耳边随风传来包拯引人遐思的**。
“嗯……啊……轻,轻点。”
展昭不想去理会包拯那颗漆黑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白痴事才会发出这种淫靡的声音,忽然天空传来“咻”的一声轻响,抬头,幽蓝夜空里一颗纯白光亮的烟火炸了开来,在他的瞳仁里转出一朵雪白的小花。
“死老鼠弄个讯号也那么花俏,天生败家。”顺口啰嗦了两句,放下灌水壶,提剑越过墙头,化作夜色里一抹浅灰影子。
包拯端坐在雕花圆凳上,公孙策浸满药油的手在烛光里亮闪闪的,在他身后用力地拿捏着包拯的歪脖子。
“公孙,你行不行啊……”包拯不安地看着桌上摊着的一本推拿按摩医术,额头冒出两滴冷汗。
公孙一边探头查看书册的指示一边捏着,心不在焉地答:“推拿也是岐黄,我看看书就行了,你不是老夸我聪明嘛。”
“哦,小心啊,你要知道,理论和实践,还是有差距的。万一我的脖子和标准脖子不同,你要知道变通啊。”包拯战战兢兢地说。
“知道了,你怎么那么啰嗦。”公孙策不耐烦地狠狠挤了一把。
包拯半声狼叫停在半空,他觉得从窗外吹来的风,实在清凉有劲,好冷。
街边铺子大多已经早早打烊,只有酒馆与客栈的迎客灯还慢悠悠地摇着,秦楼楚馆里一如往常的热闹喧天,鬓影衣香映着虚空黑色里成了一片刺眼的艳丽红色。展昭正赶往白玉堂所在的地方,无暇留恋周边诱人景致。
转眼来到一座小院落,墙根边一棵几人高的老榆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阴影里隐约透出一点月白色。展昭一跃上树。白玉堂转过脸来,龇牙咧嘴的。
“你怎么这德性……”展昭怪道。自己不过回头浇了两棵菜迟了一会儿么,白老鼠不至于给他脸色看吧,要造反了?!还想不想吃饭了!
“你踩着我脚了……”
“……”忙缩脚,“换班了,你可以回去了。”
“不忙,我还不困。”白玉堂换了个姿势躺在粗枝上。
“什么情况?”展昭斜刺里望去,纸窗大开,里面点着十几支红烛,照得一片通明。
“走来走去,吃饭,笑,走来走去,吃饭,笑……循环往复。”这只熊做的事很没意思。
展昭低头不语,满脸黑线。按照公孙策计划里的流程,他现在应该开始把钱拿出来然后准备远走高飞,而不是走来走去……
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万一他耐着性子不拿钱跑路,难道还要陪他耗下去了不成。
“白老鼠,你蒙上面去诈一诈他。”展昭推了白玉堂一把。
白玉堂懒洋洋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不去?”
“强盗是你本行,当然你去啊。”说得很理所当然。
“靠,展小猫你比强盗还强盗,怎么不是你去。”白玉堂愤恨地回了一句。
“你明天别想吃饭了,给我滚回陷空岛。”
寂静半晌。叶子在风里沙沙响。
“算你狠!”白玉堂愤怒地从一脸黑线的展昭下摆袍上扯下一大片布蒙在脸上,在布下面闷闷地说,“扯烂你衣服我也开心!”
这白老鼠还真无聊,记你账上,迟早要你还!等着吧。
于是一个蒙面大盗从天而降,长剑一亮,冷飕飕让人胆寒。
陈金吓软了腿瘫在地上,颤巍巍地道:“你,你是太师派来的?”
白玉堂在心里打了个问号,顺水推舟点点头,嘶哑着嗓子恶狠狠地说:“钱。”
“不行,不行。那是我的命根子,太师也不差这千八百两银子的。”
白玉堂忍不住眯起了眼睛,这到死还爱钱的德性真有展昭的风范。于是一抬剑打昏了眼前的陈金,挥起剑鞘弄乱屋里摆设,吹熄了蜡烛。
在窗根底下猫着腰,对树上的展昭招了招手,展昭跳了下来,蹲到他的身边。
他皱着眉对展昭低语:“这事儿好像还牵扯着庞籍那个老小子。”
“庞籍?庞太师?跟他有什么关系。”
开封城里人人都知道,庞籍跟包拯的关系,就好比冬天腊月里跳下护城河里光着身子洗澡还忘了带衣服那么囧和痛苦。他们从见面的第一眼开始就互相仇恨到现在,只要找到半点机会,他们就会动用自己所有的智慧来恶心对方。
白玉堂把刚才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展昭,“提醒老包注意点儿。”
“老包虽然不着调儿,对付庞籍还是有一手的,朝政的事他心里有谱。倒不用担心。”展昭沉思,包拯在对付庞籍的时候,总能发挥出超越自我极限的潜力。
屋内的烛火又虚虚地亮了起来,两人探头向里面望进去,陈金见到屋里七颠八倒的惨状一脸恐慌,忙挪开柜子,又挪开衣箱,墙上出现了一块不同颜色的泥墙,刮开泥墙,里面贴着一封油纸包,再揭开油纸包,里面好端端躺着一张交子。原来他早已经把银两都换成了交子。白玉堂想冲进去,被展昭拦住了:“回去通知老包,点齐人马再来,我在这儿看着。”
半柱香的时间过去,包拯和白玉堂领着一队兵丁赶来,人赃并获,一举拿下。
接着审案,判罪,陈金被罚坐监与劳役,赛凤凰一干人抢萝卜事件因为诸葛亮并不打算上告,于是开释。一件小案扰攘多时,终于到此为止。白玉堂狠狠教训了赛凤凰一番,衬托着夕阳背景给她讲了一番做贼的道理。打家劫舍也好,坑蒙拐骗也好,堂堂正正。比如他,堂堂正正地赖在开封府蹭饭,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听得展昭想把他立刻丢进大牢老死在里面。
开封府又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四人齐声高唱,病树前头万木春?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最后的最后,阳光太美好,白老鼠在晒太阳,他无视展昭唠唠叨叨地骂他不事生产毫无贡献,他无所谓。因为阳光太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