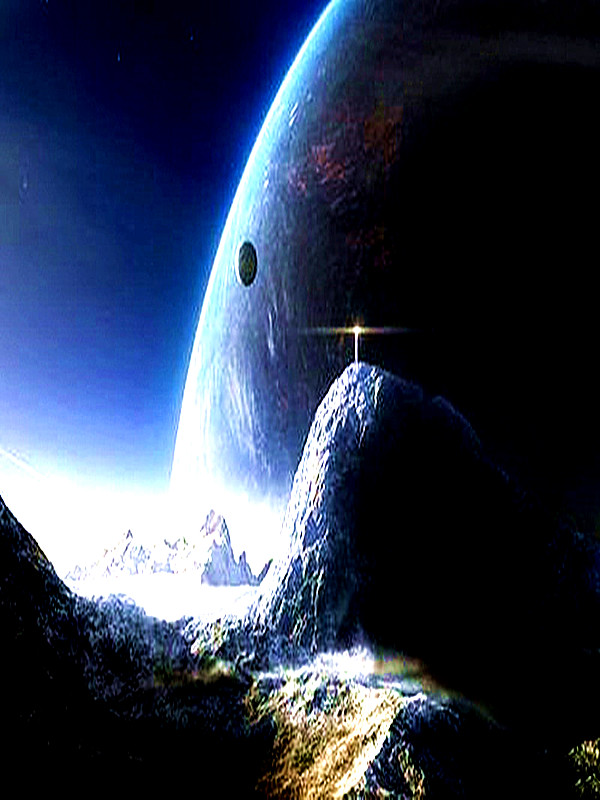“都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将近一个星期了,她怎么还不醒?”
“病人颈上伤口位置过于危险,又有那么多处骨折及内脏挫伤,只差一点便救不回来了。抢救了那么多次,如今生命体征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能维持这个样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虽说是溱港的医生,经历丰富一些,但这种情况,我从医这么多年来也是第一次见到。”
“要不是这把微型匕首恰好浸过那种烈性麻醉剂,要不是在跌落的过程中那把微型匕首滑脱刺伤她,要不是……”
“唉,说来也真是巧,可能还正是因着那烈性麻醉剂暂时把她的生理状况保持在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给我们赢得了抢救时间。
“否则,她恐怕根本撑不到来医院。”
……
好吵。
耳畔人声鼎沸,嗡嗡作响。身边好像围着很多人,好像有很多人在我身边来来去去。我想要睁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眼皮却像是灌了铅一样,连一条缝都睁不开。我想要动一动身体,整个身体仿佛都已经不再属于我了,根本指挥不了。
“好了,不要再讨论了。她现在虚弱的很,需要静养。”
一个与众不同、甚是悦耳的声音响起。他所说的内容也甚合我意。这还真是个贴心的大好人。
他说完这几句话后,房间里的人也都纷纷噤声,听着脚步声,仿佛是一个个的离开了。我心中默默长吁一口气,心想这个世界终于是安静了。
谁知原来那些人倒是都走了,他却搬了把椅子坐到了我的床边。“一天探视时间只准半个小时,有好多话到了嘴边,又怕吵到你,只好忍住不说了。”他低声说道。我的小心肝跟着一颤。
“楚有仪,你说你跳楼跳的那么急做什么?我说过能护住你救下你,你怎么就是不信?”
“你知道吗?自从进入溱港,哪怕遇到再难的事情,我也感到一切尽在掌握。可在你坠楼的那一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束手无策手足无措的滋味。”
“你睡着,这些话才说与你听。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要求你从此面对危险畏缩不前。可我真心希望,下一次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不必那般勇敢,不必凡事都冲在最前头。”
“我想,其实你,至少是可以躲在我的身后。”
“对了,有仪,你从来没有拖过任何人的后腿。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搭档,没有之一。”
“所以,你不必同我,同任何人道歉。”
“楚有仪,我喜欢和你合作。我想同你……永远合作下去。”
最后六个字,声音已是压的极低。躺在病床上的我虽身不能动,口不能言,陆栎说的话却一字不差都入了耳。我有点想哭,身体却不听使唤,竟是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我拼命想要挣脱这种不受控制的感觉,想和他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还不够好,不值得他这般倾心相待。
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只化作了一声呜咽。
听到这声呜咽,我能感到陆栎身体似是一僵,旋即仿佛是难以置信一样,试探着问我:“有仪,是你么?”
我拼命挣扎,大概火候也差不多了,三魂七魄“刷”的一下突然归位。我猛地开口说话:“是我。我回来了,陆栎。”许是许久不曾开口,我的声音有些费力,有些嘶哑。
听了我的回答,陆栎好像愣住了一般,只怔怔地盯着我,像是怕我突然消失不见。
“我听到了,陆栎。你说的,我都听到了……”
“有一句话没来的及说。死了一次才明白过来,有的话,该说还是要说的。早晚都是要说的;晚了,可能就来不及说了。”
“你听好了!这句话就是,我喜欢你,陆栎。”
说出了这句话,心中盘旋了很久的情绪也终于是明晰了起来。
原来,这就是心悦一人、喜欢一人的感觉啊。
原来,真心悦爱一人,情感不需要来来回回的徘徊不定,反反复复的思索确认。
爱,从来不是一种负担。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喜欢,真正的爱。
世间万般颜色好,不及眼前心上人。
连叫医生都顾不得了。听了我说的这句话,陆栎像是想紧紧地拥住我。终是在看到我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儿后,强行止住。
我们就这样看着彼此,仿佛能从对方的眸中看到地老天荒。
良久,陆栎才回过神来。“我去找医生。”
“哦,好。”大抵是我自作多情了吧,没来由还把陆栎吓了一跳。我微不可查地叹了一口气。
人还没走出重症监护室的门,陆栎又折了回来:“楚有仪,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因为神志不清还是真心实意说出这句话。”
“可既然你说出了这句话,我便还是那句话。”
“哪句话?”
“同天横对峙时说的那句话,‘你说的对’。”陆栎看着我,一字一句说道:“我在乎你,楚有仪。过去,现在,未来,我一直都在乎着你。”
“若你被劫持,我绝对无法不管不顾地开枪。”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像是全世界的花都开了。
不得不说,这个表白恐怕算是最单纯、最青涩的表白了。可正是这样一处不算怎么合适的场所,这样一场纯粹却认真的表白,这样一个一贯遇事成熟稳重、听到表白时却有些慌乱无措的大男孩,给了我最好的爱情。
……
“我说吧?到底是在一起了!”转入普通病房许多天后的一个大清早,萧涣前来慰问我这个伤员。谁知这这厮一推门,正好碰到了陆栎给胳膊上吊着绷带的我细细擦脸的场景,于是便有了如此哀嚎。
“怎么?你有意见?”陆栎挑眉。
“没,没有啊!您们二位开心就好,我怎敢有意见呢?我祝二位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哈!哈,哈哈。”萧涣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微笑。
“我这几日躺的都要发霉了,外面的事情知道的也不多。萧涣你不如说说看天横他们最后到底怎么样了啊?”我悠悠叉开话题。
“噢,天横啊,他倒是没你这般好运气,捞上来时已经断气了。”
“说来也怪也可笑,天横人虽死了,手中那把刀却紧紧抱在怀里,颇有楚小姐当初的神韵,任谁都取不下。”
“所以后来呢?”我十分好奇。
“后来?后来只好连人带刀归置到了一处去。”
我唏嘘不已。
“谁能想到呢?这夜天横好歹也算是个一时风光无两的人,到头来竟是被楚有仪你给杀了。”
一听到“杀”字,陆栎皱了皱眉,一记眼刀飞给了萧涣,萧涣见此连忙改了措辞:“不,不是杀了,怎么能用这么暴力的词呢?是除掉了,除掉了。”
我无奈看看这俩人:“我没那么脆弱,还不至于跟我说句话,连用词都要反复谨慎斟酌。”
“这件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了,楚有仪你先好好养伤,后续扫尾的工作我们来做就好……”说话间萧涣拖起陆栎就要走。
“我说你这么一个大忙人怎么还有时间来看望我?原来探病是假,来我这儿拐人是真。”
“楚小姐,楚奶奶!你不知道,我那边已经是忙的脚不沾地了!陆栎要是再不回去帮我,我可就要累到因公殉职了!”一边说着,萧涣一边就要拉着陆栎向门口走。
“好好休息,等我回来。”陆栎轻声说道。我笑笑:“你也是放不下那边的吧?我现在帮不了你们什么,你们要是在我这儿耗的时间久了耽误了正事,我可就再没脸见人了。”
目送二人匆匆离去,我眯起眼打算再睡个回笼觉。谁知萧涣中途又折了回来:“嗐,忘了说,待会儿有人来陪你,你也不会无聊的。”
等见到这个人时,我震惊到差点没从病床上掉下来。
“小哑巴……呃,你怎么来了?”
这姑娘默默走近床边,双手比划着什么。我看的出来,是G式手语,一种国际通用的手语。
从前刚到M国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为了消磨课余时间,我曾随便参加过P大的一个社团式活动组织。
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巧就巧在,这个社团正好教过G式手语。
依着残存的记忆,我勉强读懂了这姑娘想表达的意思。
她就是萧涣找来陪我的人。
我无语了。
谁能告诉我,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这姑娘,小哑巴,不是一直跟在天横身边的么?
“等等,姑娘,你到底是谁?”
罗纾儿。
小哑巴在我手心写下这三个字。
小哑巴,原名竟是罗纾儿。
罗纾儿何许人也?乃是罗冼养女。名取“纾”字,寓意纾灾纾难。
之前我只听闻其名,却从未见其人。说来这位罗所长也是个神人。终身未婚,却收养了两个孩子。
一个是罗纾儿。
另一个则是,萧涣。
传言萧涣之父萧书昀遇害后,其母秦嫃亦殉情而死,只留下年仅七岁的萧涣孤身一人。因着萧书昀是为敌方所害,为保护萧涣免受牵连报复,罗冼收养了他。只是这萧涣却是个怎么都养不熟的,从来不认自己的这个养父,罗冼也不勉强他,只是听之任之。
“那萧涣……岂不是你哥哥?”
纾儿低下头,眸光暗淡了下去。良久,她比划着“说”道:“我把他当哥哥。”
见提到萧涣后,纾儿神色黯然,我连忙转移话题。
“这么说来,这些年你一直被安插在天横身边?”
纾儿点头。
“这么说来,溱港很早就开始关注天横了?”
纾儿又点头。
“我一直很好奇。”我调整了一下说话的姿势,“自清河一别后,这些年,云落在哪里?”
这次纾儿没有继续点头或者摇头。她递给我一样东西。
是云落的记忆。
我原以为它早就被陆栎丢到了清河里,没想到还能有缘再见。我接过它,手指轻轻抚过它光洁的表面,半晌不语。
纾儿见我没有下一步动作,以为我不知道该如何用它,便示意我用右手将其握住,合眼屏息凝神。我照着她示意的做,在闭上眼睛的一瞬,“半盏月”地下室里误打误撞发生的一幕重新上演。
我,看到了云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