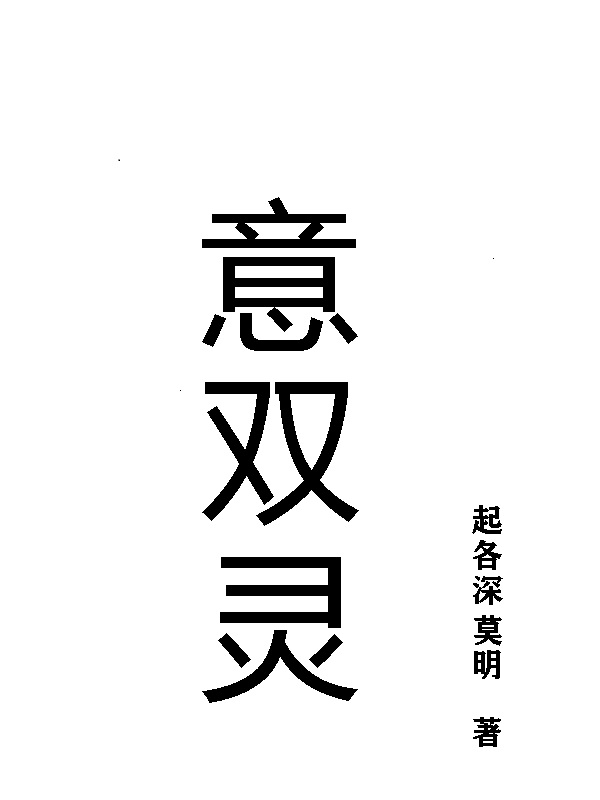当然,这两人在大街上并没有僵持太久。因为他们迎面遇到了一个人。
准确的说,是一名女子。
而且,貌似是一名我认识的女子。
“小……小哑巴!”在看清这个姑娘的脸后,我惊讶地发现,她竟然就是那个时不时来给我换换药打打针的姑娘。我虽与她只有“一面之缘”,但她的长相很有特点:薄唇,眼睛细长,右眼外眼角下有一颗小巧的泪痣。总之是一副凉薄之相。
所以,我绝对不会把她认错。
可是她怎么会在这里?我想不通。
深夜,M国的街道,冷冷清清。可她仿佛是感觉不到危险与恐惧一般,面无表情,旁若无人地在街道上行走。她如同一个幽灵,在黑暗中漫无目的地游荡,只为游荡而游荡。
这种行为,实在是很扎眼。
不止是我,云落和天横也注意到了她。云落先是冲她吹了个口哨,像所有小混混调戏良家妇女一样,对着她用M国语言说了一句下流话。而她丝毫不为所动,依旧是面无表情地向他们走来。“听不懂M国话吗?”云落开始有些戒备,见她一副C国人的面孔,又用C国语言质问了她一句。
但她还是不加以理会,自顾自地与云落擦肩而过。
这可是就有点挑衅的感觉了。
云落本来就因为天横不顾他的形象、把他硬拖出来而有些不爽;现下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了,他更加不爽了,一跃挡在了小哑巴的面前。
“你,是哪一位啊?”
云落一脸的嚣张,只是这嚣张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天横打断了:“不过是一个小姑娘,你又想做什么?”
“天横,你问我做什么?你怎么不问她是做什么的?深夜游荡、举止反常,还这么恰巧地出现在咱俩面前……依我看,她一定是有问题!”
谁知小哑巴听了云落的话,突然转身。她也不看云落,只是向天横伸出手。天横一愣,小哑巴索性拉起他的手,将什么东西递到了他的手上。
街旁路灯忽明忽暗闪烁,时不时发出轻微的“嘶啦”声。我看不清她到底是把什么物品交到了天横手上。云落见她向天横递不明物体,正想要阻拦,却是慢了一步。
天横已经打开了手中的小物件,只一眼,便是满眼震惊;目光牢牢定于其上,竟是一寸也不能移开。或许是因为太过于激动,他拿着东西的那只手都有些许颤抖。
云落看他这样,也有些紧张。不等云落开口,天横就一脸难以置信询问道:“这个东西,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小哑巴只是默默地摇摇头。也是,要哑巴开口答话也有点太强人所难了吧!此时天横和云落恐怕都还不知道她不会说话。见小哑巴不开口,天横抓住她的肩膀,焦灼地催问:“说,快说,这件东西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被人突然触碰,小哑巴像是条件反射一般猛地抬手打落天横的手。一旁的云落早已将手按在枪上多时,见此,迅速拔枪瞄准开枪,整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住手!”天横像是早就预料到了云落的动作一样,几乎是同一瞬间将小哑巴向自己身后一拽,同时厉声制止云落。云落只觉着这个姑娘突然出手威胁甚大,想要先发制人,却没有想到天横会救她。
措手不及间,云落已经扣动了扳机。他自是不能让子弹停住,只好硬生生地将枪口转向另一侧。
而另一侧,是一面坚硬的石墙。
会用枪的人都知道,对着坚硬的物体开枪,很有可能会导致子弹崩回误伤自己。云落不是不知道这个常识,只因这时,他已别无选择。
昏暗中,只听一声枪响。云落身形一动,微不可查。
不出所料地,枪响过后,天横和小哑巴都没有受伤。“她不能死。”天横冷冷对云落说。云落没有说话,持枪的手缓缓垂下。许久,才听见云落满不在乎地搭话:“随你。”天横听后,冲云落微微颔首:“我先带她离开。”
言外之意就是,云落你自己回去吧。
“呵。”见天横一脸急切,云落淡淡一笑。不知为何,我能够明显感到 他的笑中充斥着失望和难过。看着天横和那个神秘姑娘的背影远了,云落才如同彻底脱力一般,猛地一下靠到墙上,弯腰用手捂住侧腹。
此时我才发现,云落背后衣服上洇开的一片濡湿并非是因紧张而流出的汗水,而是实实在在的鲜血。不过是因为光线昏暗外加他的衣服深色而不易被察觉。
其实刚才云落就算不改变枪口方向,也不一定会打到天横。毕竟他瞄准的是小哑巴的位置,又不是天横所站的位置。小哑巴被拽向天横的身后,子弹最多是擦着天横而过,并不会打伤天横。
可若是向着石墙开枪,以云落与石墙间这么近的距离,崩飞的子弹十有八九会打到自己的身上。
但是天横一动,云落就慌了。他不能让天横有任何一点受伤的可能。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自己绝不能伤到天横。
所以,受伤的必须是他自己,也只能是他自己。
而天横,这个他一心着想的人,这个同样深知他这一枪会带来什么风险的人,什么都没有发现,什么都没有察觉。哪怕一句最简单的关心,都没有给予云落。
不是不能,是不为也。
从前我以为云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都要天横护着。可我错了,这世上又哪里会有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呢?
因为,没有人能永远护你一辈子啊。
从前种种都摆在那儿,云落明白,天横对自己并非不是真心;今日天横所为,不过是一时的无心之失而已。
可是何为“无心”?也不过是指,这颗心,已经不在这个人身上了。
现在看来,看了小哑巴给出的物件后,天横一定是找到了什么对他而言更重要的东西。作为天横最亲近的人,云落也替他感到高兴,是真的替他高兴。
只是这伤口,这代价,实在是太痛了。痛到他感觉自己的五腑六脏仿佛都紧紧地收缩成了一团。
一笑,便是痛彻心扉。
云落缓了一会,默默起身离去。他的背影仿佛是隐入了浓雾里一般,渐渐消失。周围的景物也渐渐模糊,像流沙风逝,从我的指间缕缕消散。我努力握起拳,想将这一切留于掌中,却是无论怎样都握不拢整只手。
我有些无措,用力一握,没握住光影流转,倒像是握住了一个人的手。我的手很凉,这只手却很暖,是一种干干爽爽的温暖。手指修长,指腹并没有什么肉,手掌上能摸到薄茧。整只手并不柔软,但让人单单握着就感觉十分踏实。
而且,看这大小,仿佛是一只男人的手。
等等,男人的手?我一个激灵,大脑受到刺激,猛地睁眼。“摸够了?”熟悉的声音传来,我定睛一看,是好久不见的陆栎。
我有点懵,刚醒来的脑子像一锅糨糊,乱糟糟的。“你告诉我,这是梦,还是现实?”我有点茫然。
毕竟无论是谁,在幻境与现实之间来来回回穿了这么多次,都不敢十分确定此时此刻的世界是真是假。
“摸够了就松开。”陆栎在一旁凉凉补刀。我呆呆看看这张熟悉的脸,又看看我正在牢牢握着他右手的左手,终于恍然大悟,马不停蹄干脆利落地,呃,松手。
“真有这么害羞?整只耳朵都红了。”陆栎倒像是发现了什么值得研究的新鲜事物一样,专心致志地观察。
此刻我确然十分羞愤。想要起身,右手刚一撑床,就有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
“嗷!”一声惊呼后,我华华丽丽地跌回床上。举起右手,上面已缠满了绷带。“这是?”我举起右手,向陆栎晃晃。
“噢,看这只手受伤了,就给你包起来了。”陆栎答到。
“包起来正好,省的某人又用这只手自杀。”人未到声先至,来者正是同样好久不见的萧涣。
一见面就开损,还真是不负其名。
“其实我觉着吧,你也别叫什么‘鬼舌’了,干脆叫‘毒舌’算了。”我悻悻回嘴。
“对了,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问他。”萧涣向陆栎一努嘴。
“我们赶到的时候,夜天横他们已经走了,云落的尸体也不见了,大概是被夜天横一起转移走了。”顿了一顿,陆栎继续说道:“我们在地下室里发现了你。”
“得了吧,哪儿就这么简单了?”萧涣忍不住打断了陆栎的陈述。“我们发现你的时候,你倒在地上,右手紧紧握着云落的记忆存储器,整只手鲜血淋漓的,也不知你哪来这么大的力气,怎么掰都掰不开。”
瞟了一眼陆栎,萧涣说道:“那时你整个人像是着了魔一样,谁叫都不醒。还是陆栎果断,直接上手把你抱了出来。你倒好,直接赖上了人家,抱上就不松手了,弄得我们又是一顿手忙脚乱。最后还是陆栎哄着让你松了手,又给你包扎好了右手。啧啧,那只手啊,再握的紧一分、时间长一点,恐怕就彻底废了。”
“而且呀……”萧涣故意提高了声音,“你可是要对人家陆栎负责啊。”
我瞬间惊悚:“我我我……我对陆栎做了什么?”
“不必听他乱说。”陆栎及时开口。
“哎哎哎,我怎么就成了乱说了?你不知道,你握的太用力,那个存储器整一个嵌到了你手里。医生从你手中抠出来它的时候,陆栎正帮医生按着你。你倒好,许是疼急了,恩将仇报,扭头一口就咬在了人家胳膊上。”
“陆栎也是个傻的,被咬了也不知道躲,只说‘让她咬’……你看看,你看看,这条胳膊还有块儿好地方吗?瞧瞧,瞧瞧,这些个咬痕。不是我说,楚有仪同志,恕我眼拙,竟没看出您原来是某种犬科动物。”
说话间萧涣不由分说地拖出陆栎的那条胳膊,一把将他的袖子撸了上去。顺着萧涣的动作看去,陆栎的小臂上分布着斑斑点点红红紫紫的齿痕。虽然没有萧涣说的那么夸张,看去却也是触目惊心。
看着这条胳膊,我蓦然感到有些心痛。那时的我还是不懂,只是单纯把这种感觉的原因归咎于内疚。正当我觉着自己下一刻就要摸上去的时候,陆栎迅速抽回胳膊,把袖子放下。“对不起啊,你……疼吗?”我弱弱问了一句。
“不比楚小姐,不必挂心。”瞧,这是一位多么善解人意的小哥哥啊!
可惜小哥哥的下一句话就不那么善解人意了。
“只要楚小姐少出点事,我大概就能少疼几回了。”
陆栎,你让我多感动一会儿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