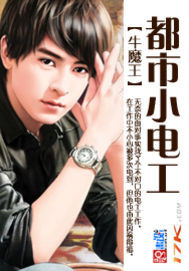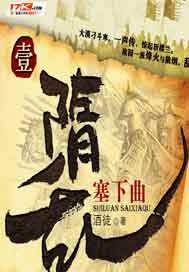正值夏日,天气燥热。
雪雁两步并作一步,一步当作半步,在长长的回廊上行走,阳光直直的照在她小巧的身上,将她的影子拉的冗长,末了,消失在拐角处。
“小姐,咱们何时出门逛逛啊!”她高声叫嚷,词如炮珠。
屋里,素秋正手持绣花线,在绣花绷上细细的绣着手绢,眉目清明,面色红润了许多,佯装恼怒,她眼角撇了雪雁一下,还是那么没大没小。
“小姐”雪雁讨好的凑到她身边,扯着她的衣裳心虚道,“自打你醒来,就只是整日待在这院里,闷不闷啊!”
素秋懒懒绣着的指停顿住,倾了倾身靠在桌沿上,那环坐着的桌子被纳入眼底,桌上放满了各色绣花布,一个褐色竹编萝斜摆着,里面是七彩的绣线和几个绣包,那绣包上扎着银针。这些是少明怕她休憩在床,太过无趣,让她打发时间用的。
“小姐……”雪雁见她不言不语,愁眉难舒的模样,很是心疼,语气里竟有些哭腔,“您是不是还在为惹恼了夫人,回不了柳家而烦心啊!”
素秋眉目一动,绣着手绢的手不由的停了下来,缓缓的,她抬起眼望向门外,院里的榕树上潜伏的知了,声浪一层盖过一层。
在柳家时,人人都说那柳家二少爷沉迷于女色,没日没夜的留宿青楼,其实不然,他是没有住在柳家,但也决非烂在青楼,只是在柳家之外,置办了住处。
在这里的几日,素秋开始只是奇怪诧异,与他相处许久,日子积得越多,越是积累成不安。那柳少明根本就不是愚钝轻浮之人,反倒是一言一行沉着稳重,有条不紊,虽说日出晚归行踪甚为神秘,却是神采奕奕,即便偶有倦意,也决不是常年留恋烟花之地该有的神色。专心回想,那日在青楼遇见时,他身边的男子,也是神色正直,丝毫不见萎靡,他们出现在哪,只怕是寻个出人意料之地,密谋什么。
素秋目光流转,飘远的眼神慢慢积聚,默默的流出忧伤。
她记得,她都记得,虽然那时她是昏睡的,却也听得明白。
他说,你已经忘了我,这样还不够吗?
他说,我回来了,你就想睡了,你就这样想逃开我吗?
他还说,我是为了见谁才回来的,你不知道吗?
那些柔情似水的话,那些情意绵绵的话,如甘如露叫她痴迷,却又如风如雾叫她抓不住。
阿难说,他愿化身石桥,受那五百年风吹,五百年日晒,五百年雨淋,只求他心爱的女子从桥上经过。
素秋苦笑,柳少明,于你,终究受尽造化之苦。可我,终究不曾记得你。
“小姐……”雪雁径自坐上旁边的空板凳,将胳膊肘放在桌沿,直起手支脸,疑惑不已,自顾自道,“这儿,有什么不好。”
心中怅然,素秋无奈的摇摇头,是啊,这有什么不好,不是很好,是太好,可是,即便再好,也不是她姚素秋—柳家大少奶奶该待的地方。
可是,此时此刻,她是回不去的.
素秋收到柳少卿的信,羊白宣纸,清秀字体—"静心休养,家好勿念"。简简单单的两行字,墨迹还没有干,她却小心翼翼的读着,忐忑不安的咀嚼着,似是要把它们镶进骨头里,竟是用了一世的时间才读完。 她是明白柳少卿的,只言片语的淡然交代,隐藏的信息清清楚楚,母亲的气还没消,她不可以回去。蓦然间,她觉得自己成了孤舟一枚,行至尽头,没了路,也断了退路。
“哎呀。”只听雪雁惊叫了一声,扑到桌上,欢喜的举起绣花绷,举得高高的,迎着太阳。
素秋一脸的慌乱,伸手就要去夺那绣花绷,白皙的手伸到一半,又顿了下来,为什么这么在乎,为什么会不舍得。
雪雁傻乎乎的问,"小姐,你怎么紧张干嘛。"
她眉头一皱,镇定的收回手,口不对心,“没有,我没有。”
雪雁嘟囔着小嘴,瞪大眼,盯着绢上的图案,绣花绢上七彩的绣线描绘着两个精致小人,依稀可以分辨出,一男一女的幼齿孩童,他们嬉戏欢腾,眉开眼笑,栩栩如生,可爱极了,好奇地,她问,“这两人小人是谁啊。”
“没有的人,随便绣的。”她轻轻地接过那绣绢,爱惜的摩挲着,眸里荡漾着不舍,却生硬的伸出手,把它递到雪雁的面前,嘴角一扯,淡淡道,“你喜欢,送给你吧。”
低头的瞬间,她想:不属于自己的,满心欢喜的占有,全心全意的倾注,一旦失去,只怕会更加难受。
如若这样,不如,不曾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