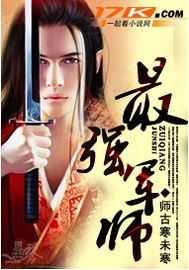杨涟本来是来调查地方辅政机构做事为什么不能像中央监政院那样得力,谁知道说着说着就说到出宫的宫女身上了,世间无论男人女人都有探听秘密的兴趣,只不过有的人藏得深有的人对自己的兴趣不加掩饰而已。杨涟也不例外,他也对这些大龄宫女的事感兴趣,当然他还有个任务就是调查百姓需不需要朝廷继续放权的问题,这些权利主要指知情权和参与权,决定权还有否决权朝廷暂时还不想给普通百姓,因为他们就算有这个权利也不知道怎么用得好。
对一个国家来说主要应该考虑如何保持稳定和如何持续发展,无论是稳定还是发展都需要规定好允许一个人做什么或者不准其做什么,在允许和不准之间就产生各种各样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就可以享受这些权利。虽然国家规定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权利,但除了财权、人权和否决权比较受人喜爱外,其它的权利也就那么回事喜欢的不多,没见谁在知道自己有交税的权利时欣喜若狂的。
天启的意思是地方辅政机构中缺少代表现在人的群体,准备在其中增加一些如乡老一类的人物,就算这些人什么都不懂对当地的治理拿不出什么好意见,至少他们有名望能够像庙里的菩萨那样镇住场面。杨涟这次的目的就是调查一下这么做的可行性,看当地官员和百姓是不是愿意增加这么一些人,既能给官员以帮助又能为百姓说上话,使不经意出现的矛盾及时消除,避免其逐渐激化最后不可收拾。
杨涟开始听卢县令介绍了一下两月前事情的来龙去脉,本来想找个机会问一下在辅政机构中增加点当地人是否合适,见卢县令说到宫女出宫后在家乡任女官的事,一时好奇也问道:“听说这些宫女是在宫中学习了技艺的,东湖县回来这两位学得怎么样?在县里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据你所说有一个嫁人还有一个要嫁到邻县去,真这样会不会出现做事做一半最后无疾而终的事?”
卢县令说:“她们两位一个是学的医术另外一个学的织绣,据她们自己说在宫中学习了一年多,其技艺只能说过得去谈不上精通。依下官看来她们的作用更多表现在召集人互相学习集体做事上面,以前很多女子讳疾忌医小病拖成大病最后不治身亡,自从宫女医官回来后召集了很多女医生替女子治病,生意好还被很多人赞扬。假如她真嫁到邻县去女医馆也不会关门,好多有生意头脑的人都准备接手,下官也正跟人商量是让私人做还是继续向上面要人。”
杨涟摇了摇头说:“估计上面也派不出来人,你们最好先让私人做起来加强监管就好,以后人多了再慢慢收回来或者另外新开医馆也可以。宫里要放宫女出来还得等年底看,反正我听说皇上的意思每年都会从宫中放一批人出来,同时收一批人进去,相当于宫里在替各地培训人才,你们应该感谢皇恩才是。”
卢县令一听忙说:“皇上恩德天高地厚,我们做臣子的确实应该时时刻刻感念皇恩。”
杨涟想了下问:“你说要嫁到邻县的是学医的?那已经嫁人的是不是学习织绣的人?她嫁了人还抛头露面来县里管事有没有人反对?而且你说她丈夫是做生意的,她当着官家里又有生意有没有人说长道短?”
卢县令说:“大人目光如炬明见万里,她确实是一边在县里管事一边照顾家中生意,县里给她配了两名女捕快专门保护她,她丈夫都没反对估计也没什么人说什么。最开始确实也有两三家认为受到不公平竞争派人上门闹事,后来东厂出面弹压这几家人才不敢再乱来,当然这宫女也宣布她家不再做跟纺织有关的生意,如此一来大家也才没话说。”
刘侨诧异地问道:“难道这宫女还跟魏忠贤有旧?怎么东厂替她出头?”
卢县令摇头说:“这个下官就不清楚了,当时闹事的人很多下官只是派人去其夫家保护,并快马向上面禀报此事,具体内情下官就不知道了。”
杨涟仔细一想,知道当时天启正生病,皇后早就说过出去的宫女都由她照管,肯定是皇后让人传令给魏忠贤要他出头。杨涟问这些关于宫女嫁人的陈年旧事并不是因为他有窥探隐私的爱好,而是想到一件事觉得多了解点宫女的情况也许用得上,杨涟的意思是既然这一切的原因是农忙时男人不够用,为什么不组织些女人到织房中做工?宫女能够在一年时间内学成技艺,普通人也许学上几个月就可以边学边做。
这只是杨涟的私下想法还不成熟,需要多问几处多比较判断才能说出来,想到这里杨涟问道:“以前的巡按御史到处巡视其作用并不是很大,我就知道很多地方听说御史要来就尽做表面文章,甚至有御史到处勒索寻求好处。现在朝廷将六品巡按御史都任命为县监,在县里坐镇固定监督变行商为坐贾,卢县令认为这样做是否妥当?两月前贵县出现意外事情县监是否出力?平时他又做了些什么?”
卢县令想了一阵说:“从解决问题这个角度看,现在固定监督肯定比以前走马观花要好得多,就如大人说的那样固定监督就是变行商为坐贾,他至少要对此地负责而不是出了事就置身事外。两月前鄙县出了点纷争,县监知道后立即来询问过下官,下官提的不收割完田里粮食工场不许开工的建议,也是在县监的大力支持下才强行执行。他平时不是很爱管事,只喜欢喝茶和跟人下棋,只是隔一阵才派人来了解下官的处理事务经过,过得很是轻松惬意让人羡慕。”
杨涟听了卢县令的话微微点头,心道这县监本来在平时不该干涉县令做事,只是发生特殊事务了才出来处理,假如平时县监也对县令指手画脚,可能县令就该不满了。不过杨涟也从卢县令的话中听出县监平时很清闲,按道理县监在没事时应该多跟当地百姓对一下话拉一下家常,了解民间的情况方便特殊事务发生后能得到及时处理,同时也可以给自己在百姓中添加点亲民形象。
杨涟想着想着就觉得应该给东湖县的县监提个醒,而且不止是东湖县想必其它县也有这些情况,作为以监督县令公正做事面目出现的县监,得到百姓了解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要让百姓知道县监始终会跟百姓站在一起,不然的话就会两头不讨好。后来转念一想,七品县令都不允许轻易下乡骚扰百姓,六品县监也不方便三天两头找百姓问话,加上要这些书生脱下长袍在田间地头跟种田的农夫打成一片也不现实,还是要在当地选一些代表百姓的人物出来才对。
杨涟想了一会儿对卢县令说:“经过对你开始的话的分析,我认为应该在辅政机构里增加一些当地人,一是当地人跟当地人沟通要方便一些,也容易探听到百姓的真话,二来也可以对县里的事务多点帮助,卢县令你以为如何?”
卢县令眨了眨眼睛说:“下官平时处理事务起来也觉得缺少点什么,总是认为百姓的话不好理解,他们的情绪也不好控制,明明是占理的事说不清楚只知道嚷,女的呢也只会掩面哭泣,想来是没有人能真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或者说他们有话但说不出来。假如真能选出一些人代表百姓那肯定好,不过就怕一些不怀好意之人会从中渔利,而且是这些不怀好意之人得了好处却要县里来挨骂。”
杨涟诧异地问:“卢县令何出此言?”
卢县令说:“这还是上一任的真人真事,说曾经有个衙役专做包揽词讼这一行,说他专作不法之事吧好像又不是,只能说是他巧妙地欺上瞒下从中获利。这个衙役在县令审案时会事先根据具体情况和县令的风格作出判断,假如他发现有人会胜诉而这人本人又不知道,他就悄悄到这个人那里去索要好处并说是县令要好处可以包打赢官司。本来时间一长就会败露,但这人机关做得好让人觉察不了,他甚至可以带人去看自己跟县令的交涉过程。”
杨涟奇怪道:“既然是欺上瞒下怎么又会让人看他跟县令的交涉过程?难道这县令真有问题?”
卢县令说:“不是这样的,这个衙役做的事下官的前任根本不知道,比如说衙役把事主叫到堂外,悄悄问事主想胜诉愿意出多少银子。事主说一个数后衙役就进去问县令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点心,县令摇头他就出来对事主说县令嫌少要加价,等事主加了一些衙役又进去问县令需不需要换杯茶,等县令同意后衙役就出来对事主说县令同意他这个数要他交钱过两天升堂官司必然赢,事主亲眼从堂外看见里面的县令摇头点头哪有不信的?你们说衙役狡猾不狡猾?”
杨涟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这个衙役因为知道县令什么时候吃点心什么时候想换杯茶,利用信息优势欺骗事主给钱,其实事主不出钱官司也能胜,看来上一任县令是个认理不认钱的好官,只是被手下蒙蔽欺骗了。”
卢县令说:“是啊,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官清如水,吏滑如油’,官员需要接受经济审察制度但小吏不需要,他们捞起银子来那是一点顾忌都没有。前任县令本是清官结果被百姓暗中骂成贪官伪君子,久而久之被上司知道后给了个差评,三年任满吏部考核时又有人说小话只得黯然回乡,好在朝廷缺人去年又复出被朝廷召去外地做事,据说因为有能力还升了品级,也算是好人有好报。”
杨涟点头说:“人善人欺天不欺这话是有道理的,能不能找到不狡猾的人谁也不敢保证,不过我想加强监管措施和惩罚力度应该也没有问题,我只想问你一句话,假如真找到人每个人就要你县里出一份银钱,县里银钱方面是否充足?”
卢县令说:“自从朝廷留了一半税收后,留下来这一半的一半留在县里,除了正常的支出外每年还有节余,给几个人开支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杨涟说:“好!明天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四处走走,怕人说你骚扰百姓就换上便服,就算今后有人对你说三道四本官替你挡下来就是。”
卢县令一听大喜道:“大人有命下官当然遵从,只是不知道大人究竟是谁?”
杨涟微微一笑说:“本官乃都察院左都御史杨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