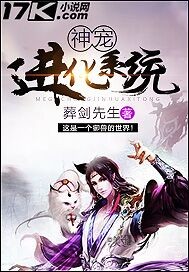秋沫在进门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聂情飞没在这里,但是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她总觉得这屋子的空气里浮动着他的味道,那是一种很难言喻的感觉,就如人与人之间的磁场和吸引一般,说不清道不明。
你还在想着他么?别傻了。
秋沫自嘲地笑笑,轻轻摇了摇头。
“嗯,你病了?”秋沫还记得五刚才说过的话,他说有人需要她治疗,如果不是聂情飞,那就是眼前的云纤了。
“是的,你进来替我瞧瞧吧。”
秋沫没有多说什么,她静静地走上前去,在云纤的示意下坐到了她的旁边。云纤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她看秋沫的眼神却是复杂的,秋沫无惧,抬头用目光回视她。
两个人就这样用眼神较量着,屋子里静极了。秋沫从云纤的眼中看出了嘲讽还有一丝憎恶,而云纤却只能从秋沫眼睛里看到平淡。
对于这一点,云纤无疑是失败的,因为真正有实力的人是不会看轻或是嘲讽任何一个对手,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否保留了实力,会随时转败为胜。
“我近几日总恶心想吐,想吃酸的,嗜睡,而且…我癸水已有段日子没来了。”云纤淡淡地说着,然后她淡然地将自己手放在了桌上,轻轻伸到秋沫面前,握住了她的手,然后紧了紧,眼神示意了一下屋子的另一边,那里放着一架很高的屏风。
秋沫微微转眼看过去,虽然她什么也看不见,她是她就是觉得那后面有一个人,而且是她很期待见到的那个人。
心跳骤然加快,手微微颤抖着,摊开掌心,里面安静地躺着一枚银质的耳环,上面还嵌着一粒圆润光泽的珍珠。
她认识这耳环,这是秋离常戴的,而且那粒珍珠还是她在西熵的村子里时亲自找到的。
秋沫缓缓收紧手掌,目光带着几分狠戾地看向云纤。
她又在威胁她!这次的事情又是那个男人计划的么?他到底想怎样?
云纤依旧微笑着,声音是柔软而甜美的,但是她脸上的表情却是那样得意,她用眼神警告着秋沫,让她配合她,“姐姐,你说我这是怎么了?不会是病了吧?”
秋沫强自平静下自己心中的怒气和无奈,咬牙切齿地说:“没事,好着呢,而且我应该恭喜你,因为你就快要做娘亲了!”
“呀!真的呀!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我就要做母亲了吗?”云纤故作惊讶地捂住了嘴唇,声音不大不小,正好可以让屏风后面的人听到,然后她带着几分惊喜急切地问道:“那胎像可稳?我需要做些什么吗?”
秋沫只觉胸口闷闷地疼着,她真的不想再欺骗聂情飞的,但是如今的她还有选择吗?如果有一天她不能活着从聂府走出去,但是她至少不想在她还活着的日子里让她在乎的亲人受到伤害,所以,她选择再一次欺骗聂情飞。
“你放心,胎像很稳,头三个月要注意,容易滑胎,不过只需要喝两副安胎药就会没事的。”秋沫的话很冷,她还特意将“滑胎”两字咬得重些了,虽然她知道云纤根本就没有怀孕,但是她只是想借此警告她,凡事不要做得太过分,只要撒一个谎,就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的。
她不知道云纤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也许真的如她猜测的那样,她只是想留在聂情飞身边,而没有其他不轨的企图,当然,这只是她乐观的想法,因为她真的不希望聂情飞再受到任何伤害。
“好了,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秋沫不想再待在这压抑的气氛中,因为她知道聂情飞就在这屋子里,她怕自己会控制不住情绪。
“等等!”云纤在她还没起身之前就按住了她的手,紧紧地盯着她。
秋沫冷冷地瞥了她一眼,问道:“还有事么?”
云纤眉眼带笑,但是她的声音却是楚楚可怜的,只听她近似哀求地说道:“姐姐,虽然我知道你做了对不起情飞和聂府的事情,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你,我们也请不到别的大夫了,而且,你知道的…在聂府转危为安之前,我和情飞都不希望这个孩子被众人所知,所以,我希望你留下来。只要你能确保我的孩子平安降生,我想情飞他一定会原谅你的所作所为,饶你不死的!”
她说得情真意切,但秋沫却听得心中震怒不已,不知为何,秋沫总觉得她笑得太过诡异,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她根本就没有怀孕,又何来“孩子平安降生”?
你到底想怎样?
秋沫用口型对她说道,美目危险地眯起。云纤也同时用口型回到:我要怎样你到时就知道了,不过为了你母亲的安全,你只要照做就行!
秋沫闭了闭眼,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然后对着她点了点头。
“好,我答应你!”
不管怎样,现在她和聂情飞之间的仇恨和裂痕已经横亘在那儿了,一切都回不去了,所以不管云纤还要做什么,她觉得自己都可以承受,不就是破罐子破摔么?
“那最好不过了。”云纤笑的狡黠而得意,她的目的终于达成了。
秋沫走出屋子的时候,只觉胸口疼痛得厉害,她忍不住微微弯了要,撑在门框上等自己缓过一口气来。这个间隙,她微微侧头,余光瞟见了那座屏风,她能想象,此时那双眸子一定注视着她的方向,突然,她觉得好难过。
不再回头,她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蹋在楼梯上,她一个不慎便摔了下去,疼痛从四面八方袭来,严严实实地将她包裹。在昏迷前,她隐隐觉得有一个白色的衣角从眼前飘过,熟悉的味道若有似无地萦绕在鼻尖。
她突然想,聂情飞,如果我有一天死掉了,你会不会开心?会不会原谅我的所作所为?
聂情飞是从屋子里飞奔出来的,因为他听到了那一声轻微的闷响。她是坚强的,所以在摔得头破血流的时候都没有叫出声来。当看到躺在楼下昏迷不醒的她时,聂情飞只觉胸口一紧,一种伤痛感在那一瞬间盖过了他对她所有的怨怼和愤恨,恐慌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几乎要让他窒息。
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她就要永远地离开他了,带着他给的恨,从他的世界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