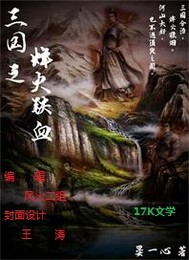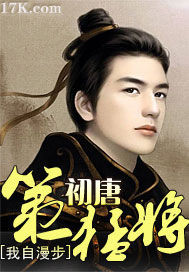我们这些人,自己解开自己的裤子,两个时辰,足够我们积蓄起一点尿液,一点也不保留,尿湿了自己的布带子,嘻嘻哈哈地蒙在自己的口鼻之上,有人笑着说,“我头一次,这尿闻起来这样好的味道。”
大风如期而至。
一开始,他还能坚持,皱着鼻子,痛苦不堪的样子,后来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脸涨得紫色。
这次的大风比上次更烈,把乳白色的湖水刮起来,溅到我们的身上,摸上去滑滑的,孟将军指着自己裤裆的位置对我们说,“回去以后,我老婆还指不定怎么审问我呢,‘说!干什么好事去了?裤子上怎么这么多儿子!’”我们哈哈大笑,笑声在尿片的后边有些含糊。
俘虏的状态很不好,后来咳成了不断线,鼻涕眼泪一大把,我们不理他,后来,他的裤裆里忽然一片精湿,他已经失禁了。
不能再等了,我走过去,抽出鱼肠剑,捏住他裤裆提了起来,把剑伸过去。
他“唔唔”地反抗着,以这我要给他做手术,可是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了。
剑很锋利,他的裤裆立刻就破了,这小子没穿内裤,一条肉虫子无力地耷拉在那里,有气无力的样子。
我把从他裤子上割下来已经让他尿湿的布条,仔细地蒙在他的口鼻之上,然后坐下来,静等大风过去。
他的咳嗽立刻停止下来,脸色也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坐在那里,浑身瘫软,一点一点地恢复着体力。
半个时辰过后,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我们不能再无止无休地在这里与他纠缠,这小子再不带路,我就把他扔在牛奶湖里。
我们没有留下食物,连水都没有,时间,我们耗不起。
他第一个从地上站立起来,看我们的神色也缓和了很多,他不说话,在前边慢慢地走路,我们紧紧地跟上。
他选择了红湖与蓝湖之间的那条窄窄的堤坝,从中间走了过去。有大风的时候,这里是绝对不能行人的,会被冲到湖里去的,他走得很急。
堤坝长约四五里地,我们很快到了尽头,这三片湖水原来是在山顶上的,是三个大火山口,我相信。但是三个火山口挨得这样紧,却不贯通,却是我没有想到的,走过去以后,是下山的路,在山坡下的右边,一股蒸腾的热气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脓一样的黄烟。
那一定是硫磺。
他没看那里,带着我们向左一拐,树色葱绿了起来,我们一点一点往山下走,感觉呼吸也顺畅了起来,大家扔掉了尿布,话语也渐多。
在一处三岔路口,他站在那里不动,像是在分辨方向,姬将军说,“但愿田王没有走这条路,”这个地方这样诡异,我理解他的心情,田王久经杀场都没有事情,这次估计不会有事的。
人们也纷纷地说着话,猜测这个万喇国的风物人情是个什么样子,有人说,到了以后一定先找个地方饱饱地吃上一顿,如果有地方的个女人,那再好不过了。
人们说笑着,像这样老婆们不在身边监督的活动,细想起来,对我们来说竟然是这样的珍贵,从女人国出来,我们这里再也没有光棍儿,对于女人的滋味,大家心照不宣。
姬达飞快地抽出腰间的弓箭,向着远处一箭射出!
离我们二十步远的地方,那个原来老老实实的俘虏抱着一棵大树一动也不敢动,脸帖在树干上。
再看,姬将军射出的那支箭正插在他的两腿间,箭杆犹在嗡嗡地颤动。离着他的小便只有半分的距离。
这小子想跑,估计这一箭非把他吓阳萎了不可。
“你娘的,也没吱一声就想溜,下次不会这么客气!”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翻过了婆罗洲中部最高的山峰,再往下走景色越发像是江南的模样。万喇人老实了许多,开始与我们讨好地说话,他顺身指着我们刚刚越过和山峰对我们说:“拉亚艾”。
大概此山叫拉亚山,那个艾字,就是山的意思罢,果然,我们又走了百十里,他又指着另一座山对我们说,“南阿克芒艾”。
在南阿克芒山的东麓,一一片望不到边的城市出现在我们的眼底。它掩映在雾障之下,充满着一种神秘的感觉。俘虏的脸上出现了如释重负的神色,我知道大概是到了地方了。
在城市的外围,我们停下脚步,下边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我们的田王,他到底在哪里,两下汇合,再研究下一步的打算。
另外我想问一下,田王留给我的悬念,为什么这样长途跋涉到这么个地方来。
我有点想画她们了,不知道她们现在是什么情形,有些担心,但是一想有徐氏三姐妹、还有六角和小月她们照顾,她应该不会有事的。
找了一处山腰地带,我让三位将军在此地暂留,而我自己带了三名军士,悄悄地下山来,接近城市。
看得出这里的生活富裕得很,天黑下来了,可是这里居然有夜生活,每一处地方都是灯火通明,酒馆儿、妓院一家挨着一家,我们四人的眼睛都看直了,怀疑是回到了华夏的洛阳城中,几个人的装束与当地人不同,但是这不影响我们挤进一家酒馆,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我们早就饿了,有做事情,得先填饱了肚子再说。
然后再慢慢打算。
四个人在靠街的一扇窗子跟前坐下来,一张竹桌,上边是简单的餐具,这边也有跑堂的,一个年轻的小伙,他见我们几个陌生人进来,立刻上来招呼,大意是问我们要点什么,我们怕他听不懂,于是指指旁边桌子上的东西,他立刻会意,应了一声就走进后间,不一会,端来的酒菜,我们边吃边打量里面的情况。
这是一间不大的临街酒馆,里面旋转了六张竹桌,两个伙计,里面人都坐满了,大家边吃边在同一件事情,不时有人插进话来。他们说的什么,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听他们讲得很是热烈。
正吃着,就见街上一阵喧哗,有人跑出去,不一会进来,指着隔壁说了句什么,人们一下子冲出去。
我向三位随从使了个眼色,他们吃得已经差不多了,我们起身到外边观看。
一群狼狈不堪的军人从远处赶来,他们围在隔壁的大门前,吵嚷着,有人身上还沾着血迹。
一个中年的***在大门口,正在好言相劝这些人,但是他们不为所动,看来是执意想进到隔壁这家去。
“将军,他们是刚刚与我们交战过的那些人,”一个人对我悄悄说。我早就认出了他们,心里纳闷,这些人出洞的时候是一齐的,只是回来的时候却是一拨一拨的,完全没有章法。
隔壁这家院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从外边一点也看不出来。我对他们说,“你们赶紧回去,吃饱了回去送信,我去看看。”
他们低头回到酒馆,匆匆吃完,与我打声招呼,身子一转消失在夜色之中。
酒馆中吃饭的人都在大门外看热闹,没有人注意到我,我从酒馆的旁边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胡同钻进去,看看前后无人,纵身一跃,双手扒住了墙头,把头探了出来。
这是一处宽大的院子,里面曲曲折折的小路,被绿油油的树木遮掩着,但是在光线黑暗的角落里,我发现了十几个手拿木棒的年轻男子,正蓄势待发,也许他们的东家在门外讲理讲不能的话,他们就要奋起反抗了。
有两个打扮艳丽的女子从一间大房子的窗口,推开了窗子看了一下,飞快地头去,关了窗子。
在这一眨眼的功夫,我却在那间屋子里面看到了一个人影子,很是眼熟,一时却想不起来她是谁。她是谁呢?
我只看到她坐在屋中,一张桌子的旁边,那个身材明明就在我的心里触动了一下,却不能明晰,她是谁呢?不可能我在这里还能见到熟人。
可是我只能按捺住心中的好奇,现在我根本没有机会接近那里。
我悄声跃上墙头,那里被一片院内伸出的茂密树枝遮挡,我蹲着身子,轻拨开 树枝,顺着围墙,到了后院。后院的光线才是真正好,一拉溜的两排房间,每间房的前边都挂着灯笼。但是相对的比较安静。与前院的喧哗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是什么地方呢?有一个穿着丝绸衣服的男子匆匆地从一间房子中开门走出来,外边的喧闹可能打扰了他,他不是这里的人,一边系着衣服一边从后门走了。
看看左右无人,我轻轻一纵,跳到院中,径直朝刚刚那名男子离开的那间房子走去,里面静悄悄的。往身后看了看,前院的争吵似乎更厉害了,但是没有人往这边来。
我轻轻地摔倒开虚掩的房门,这是两扇木门,没有窗户,开门无声,一阵香气扑面而来,钻入了我的鼻孔。
随手把门带上,外边的喧哗一下子被关在了门外。
里面是有人的,听到的我进来的动静,从帘子后边转出身来。那是一个面色姣好的女子,看不出具体的年龄,脸上带着倦容,一看到我,却是很兴奋的样子,嘴里低语着迎接上来。
她的手很软,走上来扶住我的胳膊,脚下趿拉着一双拖鞋,香气更浓了。
莫不是撞进了一家青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