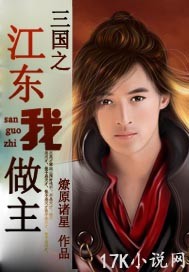“呃……嗯……哦……埋嘎的。”我嘴里含乎不清地说,让我说什么呢?谁知道我该说什么呢。
老头吃惊地看着我,我满脸的血迹,根本看不出本来那张英俊的脸,他只看到了我脸上装出来的恐惧和无奈。
我是无奈,这些人这次该从右边的树林里试试了,不能让姬将军他们太无聊。
他们坐在那里,很久都没有动,几个人坐在那里嘀嘀咕咕的,在讨论接下来的行动,我真担心他们就此打道回府,爷爷还没玩够呢。
过了不久,那个老头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挥手,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我们这才看清,也吓了一跳,那些原本我们以为只一截烂木头的了动,站起身来,我们的身前身后竟然有数不清的人。别的不说,组织纪律性还真不赖,令行禁止做得不错,这么多人,幸亏他们没有识破我们,不然的话,往我们身上一压,多大的本事也得被抓。
孟将军坐在地上,他脸上还装出无比痛苦的样子,可是已经没有人再注意我们了,他脸上还是那个样子,让我有点好笑,就差提醒他了。因为这些人恐怕已经改变了主意,直接冲击。
与其这样添油,十个十个地往里搭人,不如直接来一次对决。而且从初次的交手来看,这些人以为我们已经识破了他们的战术。可是远处的人又明明告诉他们,那里的守军对此一无所知。
这次的队形与白天大不一样,人形密集。他们快速地集结起来,也不说话,端着武器向着我们岸边的堡垒冲去。二百步的距离,要是堡垒里的最为机警的人从梦中被脚步声惊醒,他们也只能有时间从躺卧的地上站起身来。
“啊——”这一声极像了乌鸦的叫声是从孟将军的踊里发出来的,敌人惊愕地纷纷扭转头来看着我们两个。只见他弯着腰,咧着嘴,痛苦不堪地一手扶住了自己的一条腿,只有我知道那条腿一点伤都没有,我有些好笑,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给我们的人报信,敌人来了。
可是这些人又挑不出他的毛病,一个身负重伤,仍然试图站起身来随队冲锋的士兵,又有什么错误呢?
我们相视一笑,把彼此的刀剑握在手中,孟将军的长刀早就让我给削去了三分之一,我们敏捷地跟在他们的身后,向着自己的阵地冲去。
孟将军的大叫已经让放哨的人有了防备,那呼位原本站在堡垒外边的军士一转眼就跳进了圆木堡垒,一个人也看不到了。他们在静静地等待着敌人到达弓箭的最佳射击位置。
然后所有的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偷袭变成了明目的进攻。
在百步远的地方,堡垒中开始有箭射了出来。
我和孟将军一对眼色,大干。我们挥起手中的武器,也不吭声,把离我们最近的人从背后下手,糊里糊涂地送他们去了幸福的世界。也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两个潜伏在他们身后的敌军将领,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正面,我们的行为有些令自己感到不耻,不过,战无常形,能消灭对方的方法,谁又会谴责我们呢?只有猛然发现身遭暗算的人会谴责我们。
下面的铁箭飞入敌群,惨叫声立刻发出,可是他们的冲击一点没受到阻滞,我们正面的人太少了,只有十二个人,分散在四只堡垒里。
埋伏在河谷右侧的那只奇兵突然发难,姬将军他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射出的箭从这些人的侧面飞将出来,人数虽然也不多,但是造成的扰乱却不容忽视,有人中箭扑倒,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仍然有一大半的人冲到了我们的圆木堡垒近前。里面的弓箭失去了作用。军士们借着圆木的保护做着最后的抵抗,那是些无畏的士兵,他们从堡垒中站起身来,刚刚来得及把弓拉满,人已经到了堡垒前,于是一支支铁箭近距离当胸射入对方的胸膛。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地下作业了,孟将军终于大声地吼叫出来,在战斗中,他不吼上两嗓子会不开心的,“嘿,傻子们,爷爷在这里!”
那些人一开始匆忙寻声来找,他们看到了两个浑身是血的人,正挥着刀剑对他们的人大砍特砍,冲击队伍的后边一阵大乱,两头受敌还倒好说,但是姬将军他们也叫喊着,从树丛中冲了出来。
人不在多少,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突然从不同的方向出现了威胁,再说,在夜里谁又知道我们侠义有多少人呢?
我们只有二十四个人,但是动静可不像是这些,堡垒中的军士也挥着刀从里面跳出来,三股力量搅进敌群,闭着眼睛乱砍下去,肯定是敌人。
他们很快败退下去。在返身逃命的过程中,一片箭支又尾随着他们,从后脑的方向上飞落。
“别追别追,清点人数,看看少了谁。”我提醒着大家。
“我在呢!”
“我也在呢!”
“将军,我们没事。”一个人也不少。“但是我们的箭几乎射光了。”
“为什么不追?”问话的人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该问,停住了话头。
天亮之前,我们拆下了圆木,几个人扶住一根,从河水的这边泅到对岸。夜晚是我们最好的掩护,天一亮,我们的把戏就自然被拆穿了。不能干吃亏的买卖。
我们躲进了对岸的树林,开始想想田王的行动,不知道怎么样了。
隔河而望,敌人又回来一次,纠结了更多的人,他们在河岸边大声地叫骂,却找不到一个人的影子。
他们往这边望了好一会,然后转身离开了。为什么不过河搜索呢?
我们等了一会,抱着圆木,又泅回这边,拣箭。
我们把插在那些死伤者身上的箭支一根根地拔下来收入箭壶中,然后飞快地向着田王走的方向追了下去。
他们一开始是沿着河岸前进的,我们这些人很容易就能在河岸边看到他们的足迹,走了一个上午,前边没有路了。
一条从东南方来的支流横亘在我们的面前,它的水势平缓,把大量的水注入主流,我们判断田王是从这里往东南去了,因为都没有看到有过河的痕迹。
宋奎不在身边,他跟随着田王的队伍,所以这条河和它的支流叫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与主流不同的是,支流是从一条山谷中冲出来的,两岸奇峰对峙,将它夹在很深的山谷中,有军士仔细地沿岸寻找他们经过的痕迹,偶尔在河边有了发现,就跑来报告我们。这样找找走走,前进的速度慢了下来。
田王这样长途跋涉,去万喇国的原因我已经清楚了。孟将军说是去解救什么人。是什么人呢?
他们在马辰港曾经救了一批人,可是马辰港是在婆罗洲的正南方,从我们经过的路线、方位来看,这个万喇国却是在大陆的腹地,是什么人会被从马辰港羁押到这么远的地方呢?
下午的时候,支流也往正东方一拐,我们走入了山地,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田王的踪迹,只有凭着感觉往前走了,早上被我们打跑的那些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对这里的地势和环境,我们不如他们这些当地人熟悉,但是他们却没有来纠缠我们,一路上我总有这样的担心,二十几个人钻进了深山又没有向导,只有领队的人才会考虑这些问题,而军士们更多的是被沿途的奇异景色吸引,行军倒不显得枯燥。
我们爬上一处山巅的时候,就看到了三个相临的湖泊,它们紧紧靠在一起,中间相隔的陆地倒像是人工砌成的堤坝,窄窄的,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过,令人奇怪的是,这三个湖的颜色。
一个湖的湖水是鲜红的,远远看上去如同草莓汁,另一个湖的湖水是乳白色的,如同牛奶,第三个湖的湖水是蓝色的。
正当午后时分,三个湖面上一层薄薄的云雾,孟将军大声叫道,“呵呵,知道我们饿了,准备了这么丰盛的东西,又是牛奶、又是果汁、又是酒的。只是怎么没有准备一些干货呢,哪怕上一些窝头也好。”
军士个都站在湖边,对着湖面指指点点的,大为惊奇。我知道这三个湖的成因,这里在很久以前一定是三个相临的火山口,火山停歇下来以后,山口积存了自然的雨水,成了现在的湖泊。
“那你倒说说看,为什么会有三种不同的颜色呢?”苏将军问道。
“红色的湖水,是因为里面含有铁质,而白色和蓝色的湖水中一定含有不同成色的硫磺。”
他们只能听个大概,要想详细地给他们讲这些,恐怕我得专门坐下来给他们开一堂课。孟将军就把手中的铁刀插到了白色的湖水里,试验一下他的铁刀能不能融于湖水中。
我们在此地流连了半晌,谁都不说走,我在湖边让人找找看,有没有人经过的痕迹,大家分头找了一遍,失望地回来报告。田王并没有从这里经过,我们走了不同的两条路。
下午的时候,一片阴森的云雾从湖面上升起,明朗的太阳也失去了光芒,我们像是身处在傍晚,大家有些惊慌,不久湖泊的上空突然刮起了狂风,黑云压顶,在这样开阔的地方,所有的人都站立不稳,不由自主地坐在地上,相互牵手抵抗着狂风。
一股辛辣的味道被狂风裹挟过来,有人在大声地咳嗽,无力地样子,姬将军他们咳出了眼泪,坐在地上看着我,我想到了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