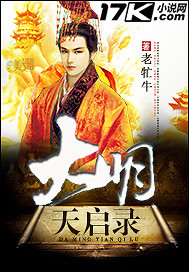兵过一万,无边无沿。今天,看着林隙间黑压压的“尼格利陀”人,那只不过三百来人,胆子小的恐怕也堆了。我对孟将军道,“今天重在脱身,不在杀敌。而且敌众我寡,刚才的套路不能再用了。”
“还没杀过瘾呢。”孟将军眼望林外说道。但是他还是挥挥手,我们向着林子深处退去。
林子并不大,方圆二里,但是我们这些人隐于其中,要想很快找到我们,也有点难。但置身林内,还能听到林子外面的动静,我们寻找着敌方的破绽,伺机脱身。
他们真把我们当面野兽了,林外动静挺大,原来只有十来个人,躲在石头后边敲着手中的家伙,嘴里呐喊不断。而身后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但那里保准有大批人马,张着口袋在等着我们。
我和孟将军相视一笑,这也未免太小儿科了,不要说这么简单的包围,十面埋伏的阵仗我们也早过去些许年头,离着慌不择路还早着呢。
他们虚张声势的结果,就是我们突然冲了出去一阵大砍,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惨叫声引来了更多的“尼格利陀”人,他们的竹箭没头没脑地飞过来,一位军士哎哟一声,大腿上中了一箭。我赶紧把他扶住,一伸手,将他腿上的箭拔了出来往地上一丢。
我们架着他踏着十几个“尼格利陀”人的尸首冲上了小道。疾步向着马卡地方向行进。不久,身后和身前都出现了动静。
我们迎面碰到了匆匆而来的一队人马,他们的行装与我们在马卡地看到的人还不尽相同。身材比“尼格利陀”人略高,体形也略微魁梧,没有弓箭手,但是每人身背着三、五支投枪,这些人我们虽然不认识,但是我老远就看到了宋奎在队伍中指手划脚。
我们的“援兵”到了,“尼格利陀”人从马卡地的撤离,起缘于内讧,因而他们现在的军事行动,自然而然地被视做了挑衅和有目的的无理取闹。再加上宋奎的挑拨,双方碰面后更不答话,直接就搅斗在了一起。
我们趁此机会,丢下他们就走。宋奎不知道什么时候追上了我们,孟将军对他言道,“怎么,宋首领也不指挥战斗么?”他一笑道,“现在不走,更待何时?让他们狗咬狗去。”
我们丢下身后的纷乱嘶杀,很快就到了中午选美的地方,但是那里现在乱糟糟的,一小队的装精良的驴颂人正往甲米地方向开拔。
原先看到的人山人海的局面早不见了,我们伏在一片窝棚区,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看样子现在这里也很乱。我问宋奎:
“你带去接应我们的是什么人?怎么我一点都没有印象?”
“告诉你吧,那是另一个小国的军队,叫做蚂蚁国,他们的地盘就在这里往南,有个大岛,叫民都撸岛。”
“这名字起得妙,怪不得一人背三杆枪呢。”孟将军道。
其实,后来那处岛被叫做了“民都洛”,打个比方吧,如果驴颂岛是一个窥探黄岩岛的人脑袋的话,民都撸岛就是这颗人脑袋上快要掉下来的下巴。
蚂蚁国,古国名,一译麻逸。故地就在驴颂的民都撸岛,公元九八二年,该国正式与华夏有往来贸易,应该是宋朝的太平兴国年间。其后商船往来不绝,但那已经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了。
蚂蚁国那个地方,我们马上就要去到,也就是从这时起,蚂蚁国对华夏有了第一次的认识。
那里与这里隔了一条民都撸海峡,这些人也被驴颂人给征用来了。但是让我不耻的是,这些驴颂人也够老道的,直到现在,我也没见到他们的本部人马。
一个小队,约有五六个人,急匆匆地迎着我们赶了过来,我一使眼色,孟将军和十来个人迎接上前。
面对突然出现,走上来的“阿基奴卫队”,他们显露出了惊慌。纷纷去拽身上的刀,被孟将军人等一顿拳脚摞趴在地,押到了我们面前。
那位小头领昂首挺胸,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宋奎问话他也不答,刚才中箭的那名军士一瘸一拐地上前,“啪啪”两个大嘴吧,那人吐了一口血,总算开始说话。
原来,宋奎领着蚂蚁国的援兵走后,立刻有人上来问询总祭司,他端坐在没棚子的驴车上,一方不发,两个亲兵也换成了美貌的女子,齐雪和徐林更是听不懂,干脆突然打驴往甲米地方向飞跑。
看到总祭司被挟持,这会儿就该动用驴颂的精锐了,一大队人马都去追驴车了。而他们五人,是前去后方,制止那场“尼格利陀”人和蚂蚁国人的械斗。
这个消息让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外边,要知道,驴车上还有我和孟将军的夫人呢,一架驴车怎么跑得过一群野驴?
我们当即决定,立刻兜着他们的身后冲上去,趁乱摸鱼,以解燃眉之急。
我们起身就起,身后有人对我和孟将军问道,“他们怎么办?”
“这好办,”我返身回去,一一点了他们的昏睡穴,几个人上去,抬起来往草窠里一丢。怎么说他们也算是俘虏,不能杀的,但是又不能让他们前去报信,只有用这个方法。
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一人负伤,冲锋应该没有问题,我只问了一下那个腿上中箭的军士,“你叫什么名字?”
“回将军,我姓苏,叫苏禄。”
“能行吗?”我是指他的腿。
“应该没事,以前也负过此类伤,不都没事?”但是我看他的腿部中箭的地方,已经肿起老高,伤口处一片黑紫!
“奶奶的,学会耍毒了。”
这个样子绝对不成,过一会他会成为我们的累赘,更重要的是,耽搁的时间久了,恐怕对他性命不利。
磨刀不误砍柴功,虽然我现在是心急如火,但是还是让他坐下来,解下腰间的带子,在他的大腿根处扎紧了,拔出匕首,照着那块淤青就是一下,手腕一旋,鲜红的血流了出来。
“也只能如此了,苏禄。”
他的额头挂了一层汗珠,冲我感激地点点头。
“谁有尿?”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