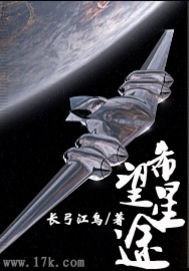“你们想想,不管是太子啊还是秦王,谁登基都会置对方于死地,这个结果,太上皇可是最不愿看见的。”
“所以!”
“依在下之言,不如大家伙将目光一致对外,好先解决了乱王逼京之事再说其他么……”
“毕竟新帝在位,是已经杜绝了几人称王,几人称帝……”
“而且,骨肉相残之事也没有在我大唐出现!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挺好么。”
礼部尚书李道宗不敢大刀阔斧地力保新帝,只求自己别受到那些诸如殃及池鱼之类的祸患。
故此,在太子党和秦王党面前,礼部尚书李道宗已经很刻意地避免了那重此抑彼之言。
所以他在心中早抹杀了那些自认为是【拉仇恨】的词眼后,才开始奉命唯谨地挥舞着臂弯,并于大殿上谨言慎行。
历朝历代,君前奏对本就是他们这些背紫腰金之臣,所忌惮的。
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一套【下坂走丸】之言来潜身远祸。
倘若一不留神,嘴上犯贱,而落下了那持人长短的把柄,那便是得不偿失了。
比如!
像三国时期的廖立。
他便是曾在殿前对丞相诸葛亮发牢骚,而被贬为庶民的。
若如此!
岂不是亏大发了么。
所以谨言慎行的目的便是以免那太子党、秦王党砸下来的焦雷劈中自己。
可即便如此。
礼部尚书李道宗额头上的冷汗还是逐渐汩出。
因为!
当他的眼瞳碰撞着那三省六部二十四司这凶神恶煞的目光时,这肢体上的大开大合,便在他语气声愈来愈小的同时,越来越僵硬,越来越迟缓。
几个意思?
我的话已经很中肯了啊。
至少畅言这一致对外的话头儿,是为了团结啊。
难道!
他们非要咱说出个丁是丁卯是卯么。
这可咋整!
陛下给臣下出的不是送命题么。
话为说完,礼部尚书李道宗早察觉了异样,只得像抛绣球一样,将这个疑难杂症,顺手就扔给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来洽谈。
“长孙哥哥!你说说贝!”
看似一句咸不咸淡不淡的话,早惊悸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的心坎,是够不着底啊!
“……”
不是。
这不是丁香叶子上捧黄连吗?
一味还比一味苦!
太子党不好惹,秦王党也不是吃素的啊。
咋地!
直接顺着他们的意愿,让陛下禅让退位?
这不是胡闹么。
可五十万大军逼近长安!
陛下不退位也不行啊!
半晌,礼部尚书李道宗瞧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怂得不要不要的,忙机灵地微微甩动袖袍,好几次三番地去提醒着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好给自己解围。
“……”
可是,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仍是杵在那立成一杆银枪,只顾自己大口喘息,急口呼气。
不多时!
等干瘪了厚唇,流尽了恐慌之汗后!
貌似……
这大殿上的满朝文武好似还不放过他似的。
——
只见他们这齐刷刷的目光如炬,极像那高山上滚下的石头一般,力道越来越大,还不会回头似的。
“要不抓阄?”
“嗯……”
其他大臣或许没听清。
可礼部尚书李道宗却是直接尿了一地!
“抓阄!”
话音刚落。
礼部尚书李道宗才发现,由于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的话音太过碎小的缘故,这【抓阄】的馊主意倒像是从他的口里迸出来得一样。
“……”
一时间,大殿上的嘈杂之声更吵!
【抓阄】是民间上抽取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方法。
不管是什么道,什么州,什么县,什么乡,什么村!
这在任的地方父母官便是用这种屡试不爽的方法,去杜绝了那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
但是!
这含元殿是什么地方。
是君临天下,一统九州大陆的神圣殿堂。
靠抓阄来决定谁来继承大宝。
不是荒唐吗?
没错!
不滑稽么!
半晌,文武百官没有缓过气。
“这丫的就是怂!”
“他不敢违抗他的新帝,咱们不如跺了他们,跟他们废什么话啊!”
“对啊,现在谁有主动权谁说了算!”
“……”
见含元殿上乱成一锅粥了。
崔宣庆、崔恭礼才懵逼着双瞳,往新帝乔师望这里偷窥着。
但从新帝乔师望的眼里。
可别说……
居然有那么一股子的洋洋得意之劲儿。
他好似很高兴将这矛头都甩在吏部和礼部上一样。
“……”
怎么看陛下都不像是有将大唐天下拱手让人的意思。
倒有几分耍猴的意思!
想到此,崔宣庆、崔恭礼两位兄弟却长吁了一口气,“呼……”,幸亏这矛头没调过来,否则他们就成了炮灰了。
“朕给你们的机会!”
“抓阄就抓阄!”
“也省得你们贼心不死!”
恰在此时,一声饶有趣味的话音,回响在了含元殿上。
久久不散……逡巡不去!
“抓……抓阄……”
喃喃声下,可把崔家俩位兄弟诧异坏了。
冷不丁不防。
却听“砰!”的一声大响。
恰是崔宣庆、崔恭礼二人因太过诧异这【滑天下之大稽】的决断,而瘫软在地。
陛下都成九五之尊了!
怎么还闹着玩……
这君临天下的大事还能用抓阄解决吗?
彼时!
等大殿上那如火如炬的目光俱都瞄去这崔家两位兄弟的身上后,这寂静的景况才在吵闹的尾巴上,失落在地。
“……”
不是!
刚才乔师望说什么?
同意抓阄?
谁他麻跟你抓阄!
你妹的。
你瞧五十万大军逼近长安,是大势已去,可不盼望着抓阄么。
我们又不是没底牌了,谁跟你玩这小孩家的玩意。
“放屁!”
顿时,行军总管李靖便朝着含元殿的高台上臭骂。
“好小子!怪机灵啊。”
“你以为这是干什么?分佃户家的一亩三分地?”
“真是白日做梦!”
“再说了!你要点脸行么。”
“你好歹给史官留些活路!”
“我说的对么,史官魏祁山!”
见行军总管话锋一转,居然调在自己头上。
史官魏祁山,是又瞪出灯笼大的眼睛,十分得不相信!
麻呀!
这一个月咋了?
都两次殃及池鱼了。
我一个小小的史官,就这么得不凑巧么。
想当初不管是什么隋朝啊,还是唐朝……
莫说是一个月听见谁唤一声【史官】,就是他麻的三俩年,也不会有人提议把他们史官当做马呀还是骡的,拉出来遛遛!
可这年头怎么了?
怎么了!
都两回了!
而且次次都跟那砍头之事挂边,次次都跟改朝换代这样的大事件挂钩!
如今当个史官都这么难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