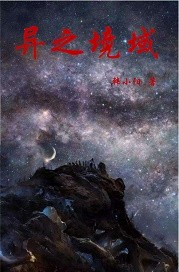裴舒宜打量裴舒窈,看她神色真切,倒不像是作假 ,悬着的心也放下几分。
“深谢阿窈妹妹,我和四妹已经接了恩旨。妹妹处处为我们考虑,姐姐心里实在不安,这些日子我被困在房中,倒想了许多,从前是姐姐鲁莽无知,着了奸人的道,倒累了妹妹们。”
“姐姐何必客气,做妹妹的理应如此,婉姨娘如何了?伤可好些了?”
裴舒宜:“郎中来看过,开了方子,只是些皮外伤,好好将养便能大好,劳妹妹费心了,送了许多名贵药材。若不是妹妹帮忙,只怕姨娘凶多吉少。”
若不是裴舒窈,只怕她和姨娘还被蒙在鼓里,被冤死了无法辩解。如今想起刘氏她都咬牙切齿。
裴舒窈拉着二姐姐的手,“姐姐如今如何准备,外面流言四起,若不提早想好对策,将来怕是无法在京城立足。”
裴舒宜惭愧,“不怕妹妹笑,姐姐愚长妹妹几岁,困在房中想了几日,竟想不出有何对策,还望妹妹不吝赐教。”
“如今京中流言四起,今后无论姐姐嫁往哪处人家,只怕在婆家都会难以立足,如今已成死局。况且女子名声最为重要,怕是日后姐姐在婆家抬不起头。”
裴舒宜:“都怪我一时糊涂,姐姐自做错的事情,无论今后如何,都只怨我自己,不过累极家中声誉,裴家名门望,世代簪缨,我竟成让裴家陷入泥潭,实在惭愧。”
“姐姐何苦作践自己,姐姐心善错信他人,这本不是姐姐的错,都怪奸人轨迹多端,无所不用其极,这与姐姐有何干系?”裴舒窈思虑片刻后劝道,“既然已成死局,姐姐何不跳出这局势,为自己搏一搏。”
“还请妹妹指教。”
“我舅母有一闺中密友,河州段家的主母,贤名在外,二姐姐或许听过她。”
裴舒宜大吃一惊,“段家的主母,治家贤明,声名远播,听说江南各州若是有谁家的女子得她赞赏,不论门楣高低,媒婆都会踏破门槛。”
裴舒窈点头会应,“正是此人,姐姐如若愿意,我去河州段家住上一段时间,待京中风波平息再回来,只不过河州山高水远,远不及京中富丽堂皇,只怕会让姐姐受苦。”
裴舒宜赶忙答应,她如今就像落水之人看见浮木般,不顾一切的想要抓住这唯一的机会。“我愿去。”
“姐姐愿意便好,姐姐大可放心,段家主母与我舅母是手帕交,感情深厚,昨日舅母已修书一封,托段家主母照顾姐姐,想来姐姐在河州也能过的安稳。”
裴舒宜遂即担忧,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姨娘,姨娘被刘氏先前命人打了五十大板,命都没了,半条,如今若是还将姨娘留在京中刘氏必定会加以报复,叫她如何能放心走。
遂担忧问道,“只是我姨娘如何?我若一走,只怕大夫人不会放过我姨娘,她未算计死我,定会将怨恨用在我姨娘身上,我姨娘生我一会,叫我怎丢下她不管,可否让我姨娘同我去河州,也好叫我放下些心。”
裴舒窈本就由此打算“自然好,我会命人准备好姐姐路上的衣食住行,姐姐放心。”
裴舒宜跪下向裴舒窈磕头,“多谢妹妹,姐姐无以为报。”
裴舒窈被吓了一跳,忙去扶她起来,“姐姐莫如此,莫如此,真是折煞我也。”
裴舒宜拉着裴舒窈的手“阿窈,姐姐还有一事相求。”
裴舒窈:“姐姐可是为刘氏?”
“正是,刘氏先前让采桑来和我房里的小女使说,大哥生死未卜妹妹无暇顾及自身,更不可能管我和阿容的亲事,我一个小小庶女,若不能为自己某一个好前程,只能被草草打发,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竟会信了这种胡话。”
裴舒宜抽泣起来,她如今明白了裴舒窈的好,自然是万个感激,“妹妹如此为我着想,我竟这般混蛋,做出如此事情,真真是羞愧。”
“姐姐这般挺铤而走险,不过是想为自己谋得个好前程,让婉姨娘在家中好过。”
裴舒窈不由得感慨,若是双亲还在,家中定是另有一番光景。
裴舒窈感慨道,“父亲母亲早亡,早年,家中由大哥一人撑起,如今,大哥音信全无,家中唯余我们姐妹三人,我们理应同气连枝,不论是为裴家还是为自个儿谋个好前程,咋们身为女子本就艰难,若不依靠母家,如何有资本去另谋一番天地。”
世道多艰,何况女子本就地位低,如今女子地位虽比前朝强数倍,但女子仍有许多规矩要守。
裴舒窈亲自送裴舒宜出门,而后又回房里,裴舒容还在这里等她,她这两个姐妹,虽都是个好的,但二姐姐果敢确鲁莽,而四妹妹看着唯唯诺诺却是个有主意的。
裴舒容先前听完二人的谈话,既为二姐有个好前程高兴,也担忧自个儿,此事裴家女儿声誉受损,裴舒窈是皇后心尖上的人,自是不用担心,而她不过是个小小的庶女,她全然不像二姐起码还有亲娘在身旁,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亲娘几年前因病去了,她当真是一点指靠都没有了。
如今看裴舒窈这般为二姐谋划,相比是个心善的,不像别家嫡女那般仇视庶女,想必也会善待于她。
“听阿窈姐姐一席话,才明白我二人过去的愚蠢,阿窈姐姐如此为裴家谋划,是我们小肚鸡肠, 从前做过许多得罪姐姐的事还望姐姐见谅,今后,姐姐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妹妹绝不推辞。”
裴舒窈颔首,承下这份情。“那先谢过妹妹了,眼下正有一事想求妹妹帮忙。”
裴舒容:“姐姐请讲。”
裴舒窈靠到四妹妹耳边低声开口。
裴舒容思量不多会便重重点头便起身告辞离开了。
裴舒窈把站在屋外的女使婆子都唤进来。
“郡主和容县主说什么了,奴婢们只见她抹着泪出去了。”
“任她哭去。”裴舒窈喝了口茶,像是气的不轻般,“除素衣外都退下罢,我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