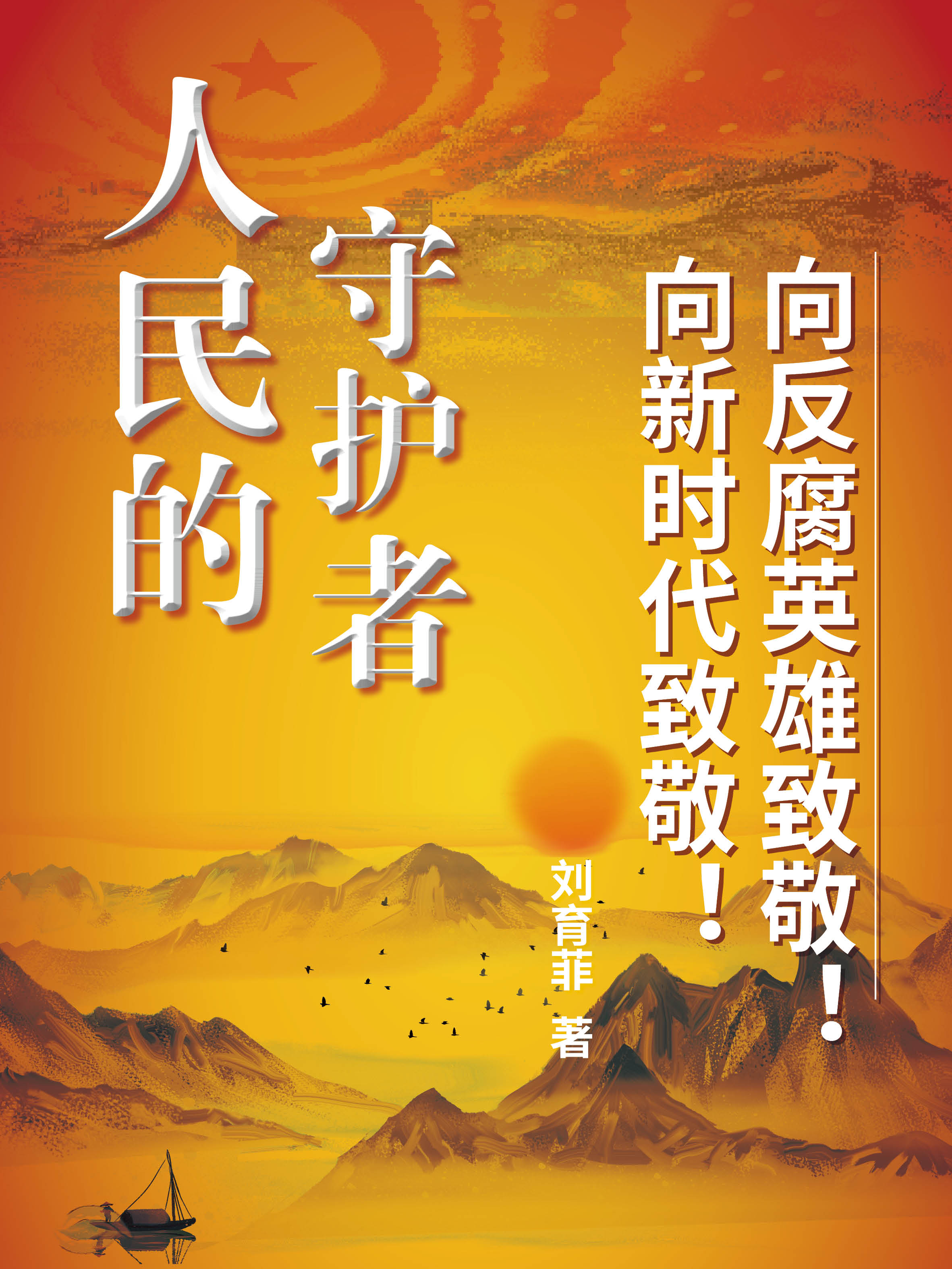二
嫂的丈夫就在工地上开“热特”,他叫蔡福,长得矮胖胖的,一个蒜头鼻子。大家都叫他菜墩儿。菜墩留着两撇儿小胡子,眉毛恰好同胡子的方向相反,朝两边太阳穴箭似的发射出去。这样菜墩儿看上去就不怎么和善,加上他爱喝酒,喝了酒就骂骂咧咧的。什么三八犊子,你这没尿的东西……可花花了。菜墩识字不多,但骂起人来才华横溢的。他八岁从关里来这儿投奔他的舅舅,自小在农场长大。除了会开车、喝酒和打牌,旁无所长。谁也闹不明白他凭啥那么牛气。他出车到镇上办事,遇有个半道招手截车的知青,他便佯作慢腾腾地减速要停车的样子,待知青绕到车后正扒着车厢板往上爬,他却将车猛地发动起来,登登地窜出老远,把那些可怜巴巴的小毛孩子甩在公路上,自个儿驱车扬长而去。好几次差点儿甩出人命。
菜墩儿的心肠真狠。
分场的人都恨他,他混到二十六七岁,农场的姑娘,没有一个愿嫁给他。偏偏他也不是个巴结当官拍上欺下的家伙;连主任也不得意他。于是组建水利队时,便一脚将他踢到工地上来,与我们沦为一类。
那时候他刚刚掏尽多年积攒的腰包,在关里老家娶了个媳妇来。
那媳妇便是二嫂。
二嫂长得不算好看,瘦瘦小小的个头,两根乌亮的辫子柔顺地搭到腰上。黑红的腮上,一边一个浅浅的酒窝。从那泉眼似的酒窝里,泊泊地漫出无忧无虑的笑声。她爱笑,凡是她没听说过的事儿词儿话儿,她都会没头没脑地笑起来。笑够了,一句话没有了抿着嘴悄悄走开去干活,一脸的心满意足。
二嫂的老家穷。吃不饱饭。嫁到这白面柴禾管够的国营农场,有菜墩儿旱涝保收的工资,还有那些说话做事都时时令她惊异好奇的知识青年,二嫂的日子真是开心。她干起活来从不吝惜自己的力气,偌大的一缸白面叫她搓揉起来就好像洗块手绢儿似的轻巧。从她来到工地以后,包子啦发糕啦烙饼啦三天两头地换花样。还有一分钱两分钱就买得的用水萝卜缨子韭菜花大头菜便于老黄瓜生香瓜子液的小咸菜,拌上点儿辣椒末求和熟豆油,又下饭又爽口。
都说菜墩子没积下德倒撞了大运,娶了这么个又巧又勤快的媳妇,说话的人,多半有点儿眼热,又有点儿不服。不服不行。恨死了菜墩儿的人,也恨不起二嫂。嘴上不说,心里也都叹着二嫂的好处。
春天,二嫂还没有娃。吃了晚饭,手里便拿着一副鞋底儿,到我们住的帐篷里来。连队开会,本没有她的份儿,她却不走,缩在角落里,两只日渐圆浑起来的胳膊,一动不动地支着下巴沿,一门心思地睁大了眼连个哈欠都不打。那神情明明是个依着奶奶时听故事的孩子。有几次我从一边偷偷地注视她,竟然觉得她那坦诚无邪的眼睛里流泻出一种淡淡的哀怨和饥渴,瞳仁里两朵跳跃的烛光,藏匿在一层若有若无的迷茫中……往往报纸念完了许久,她还托腮坐在那里发呆。
“二嫂,有人说你在老家是个团支书呢!”
“二嫂,他们说你会唱歌儿……”
“二嫂,你会写信,起码念到六年级吧……”
我们爱同她打趣。帐篷里清一色的知青是很乏味的。况且你问什么,她从不恼。垂下头,脸涨得红红,用她那个清脆的山东口音嘟哝一句:“快别说了,都要羞死俺了。给俺讲讲你老家那个西湖吧,是有个白蛇传不是……”我猜她一定是会唱歌儿的。在没人听见的大草甸的苇丛里,在她家里那小屋子的板铺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小声儿地哼给她丈夫听……
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那个菜墩儿,他也配?别提那个菜墩儿了,有一天大清早二嫂来生火做饭,眼睛红得像个熟李子,问她怎么了,死活不吭气。半天问急了,终于哇地一声哭,扑在我肩上。
她说他赌输了钱,便喝酒,喝上了劲,整夜不让她睡觉……她不愿意,他便揍。揍完了,又跪在地上求她……
她撩开衣衫,便露出一块块紫的青的伤痕。她把脸埋在掌心里,哭了好久。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她哭。
这么说,二嫂过得并不快活。我早该想到的。我不知该怎么安慰她。从道理说,菜墩儿不是她的恩公吗?谁能对她进行忘恩负义的启蒙教育?
就在那时候,小廖从南方探亲回来了、他一回来,收工后河堤上便响起了他的手风琴声。
从二嫂听见那琴声的第一天起,她就有一点儿失魂落魄的样子,那会儿她正在发第二天蒸馒头的面,沾满面粉的手一把扳住了我的手腕。
那是啥?是个啥?听声儿像个口琴,有这么大的口琴?咋就在胳肢窝底下出声儿?
我告诉她那是手风琴。要用很有力气的胳膊鼓起风来才能奏出音乐。
就像大灶上的鼓风机,她恍然大悟,哈哈地乐了。我一看倒像那个红灯记。啥伴唱来?钢、钢琴,我在画片儿上见过。像是把个钢琴挂在脖子上了,吊着那排大马牙!
我们哈哈大笑,二嫂笑得把面盆都扣了。那会儿她可真高兴。她说她让蔡福给她在镇上买支口琴来,蔡福说“那玩艺顶啥?等你生了娃,回分场住,给你买炕琴。”
炕琴是炕上的柜子,同口琴风马牛不相干。
伶俐曾有过一支口琴,在水渠边吹了一支《花儿为么这样红》,又在连队国庆联欢时吹了一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便让连长没收了。从此再没提起。
伶俐去找连长要口琴,连长说:
“吹口琴不渴么?渴了喝啥?”
“喝水呗。”
“在家也喝水?”
“喝——喝茶。”伶俐恍然大悟。下半年回家探亲,给连长带了两铁盒子茶叶。那盒子是四两装的。
连长说:“喂鸟哪!”
伶俐便把留给自己喝的那罐子也给了连长。
连长说:“你超假了,这车票不能报销。”
伶俐便把她妈从箱底里挖出来给她的一条旧的真丝被面给了连长老婆。想想还少点,又加了一袋奶粉和一双袜子。
连长把那条被面反反正正看了老半天,咧嘴,乐了,将那袋奶粉扔还给她,说;“留你自个儿喝吧!”
伶俐对我说:“连长喜欢不易怀的东西。”
伶俐后来上了工农兵大学。临走时偷偷告诉我,她给了连长一块上海表,是夹在一斤毛线里给的。
我说:“这有什么稀奇。”
她说;“稀奇呢,我去连长家,从不见他用这些东西。”
我说:“他是怕别人知道嘛。”
她摇摇头:“他连茶叶也不喝,喝白水。好多回都这样。大概把茶叶孝敬场长了。有人说他想调回山东老家去。”
连长是转业兵,在这里十七八年了。他也想家?
伶俐走时,连长老婆给她包了一顿饺子,还给煮了十个鸡蛋路上吃。
以后只要那手风琴声一响,二嫂就扬起脖子眯起眼,痴痴地望河堤出神。夕阳下,小廖的影子拉得老长,两只胳膊一开一合的,像两只扇动的翅膀。
手风琴真好听。二嫂每回总要叹口气,好像责怪自己至今才知道世上有这样一种乐器和声音,俺在老家时,就光听过二胡和笛……
说实话,小廖的手风琴拉得不怎么样,总像漏风似的,下乡四年多了也没有大长进。否则他早就进了场部宣传队。但他爱拉,一拉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他拉琴时身子总冲着我们女生的帐篷。我们都明白他盼望着有个人会成为他的知音。可世上遗憾的事太多,总没有人在月光下走出帐篷迎着他的琴声走去。他说话略有一点结巴,嘴巴瘪瘪的像个老太婆。干活有气无力,只有眼睛不闲着,总骨碌骨碌地往女生这边扫。
他如果知道他如今真有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听众,他会怎么样?他如果知道了他的知音竟是菜墩儿的老婆二嫂,他又作何感想?
看着二嫂日日这样眼巴巴地寻他的琴声,望他的身影,甚至卖饭时趁人不备塞给他几个专为他包的大馅儿的包子可他竟全然不觉,我有些不忍了。
一个雨天的中午,他不知怎的竟坐在我们食堂门前的嫂子堆上来拉琴,我纳闷儿一会儿,才明白原来女生们都来食堂的棚子里帮我们义务摘菜准备包饺子。
“小廖,过来!”我叫他“二嫂要看看你的琴漏气不漏。”
他不大情愿地走过来,眼睛瞟着另一边。
二嫂却已慌了神,拼命在围裙上擦她的手。待小廖走到跟前,她已满脸通红。嗫嚅半天,说出一句话:“你拉得真好!”
二嫂的嗓门大,声音传进了棚子里去。姑娘们都探头出来。小廖顿时容光焕发。那时二嫂正用一根食指小心翼翼地摸着琴键,怯怯地问:“难吗?”
“不难,难什么?谁想学,我包教。”小廖一挺胸脯,一炮打天下的架势。当然她的慷慨不是为了二嫂,二嫂无意成了他的鱼饵。
竟无人响应,一个个脑袋都缩回去了。谁都明白这个玩艺儿不是通向城市的钥匙。一天累得贼死,敢有这份闲心?再说钱呢,谁有几百块钱买得这么个不能吃不能用的东西?就算有钱又上哪儿去买呢?任何文化都只有在适应它生长的土地里才能发出芽来。差不多在下乡的第二年,知青们就已懂得求实了。
只有二嫂没走。死盯住那琴,怔怔地发一番呆,突然说:“你教我吧!”
小廖也愣了愣,回头瞅瞅那笑声盈耳的大棚,使劲咽一口唾沫,说了声行。
二嫂有点站立不稳,傻怪地笑着,伸手抱起那琴来。手微微颤抖着,不知往哪里伸。小廖忙上前托住,帮她把宽厚的皮背带套在肩上,她还手足无措地呆立着,小廖抓过她的手,一只按在键上,一只塞进琴左侧的把手带,大声说:看好了,就这样。左手往外拽,再往里一压,就出声儿了!
二嫂憋足劲,全力以赴。先是一无动静,她便急了像揉面那样双手使劲往里一扭,突然,琴键上爆发出嘎的一声,惊天动地,惊心动魄——
“哎呀哎呀,吓死俺了。”她一步跳开去,鼻尖上冒出粒粒汗珠。“俺还以为哪儿来了只大鹅哩。”
她脖子上吊着那琴,笑得琴声直颤。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就这样,真真假假的,二嫂跟着小廖学上了手风琴。
小廖似乎是为了气气那些有眼无珠有心没肺的姑娘,竟对二嫂教得十分认真耐心。每当菜墩儿傍晚出车去打夜班了,二嫂就让我去叫小廖到食堂门前的样子堆这儿来,趁着天将黑没黑的那点晚霞的余光,咕咕嘎嘎地开张。当然二嫂是不识五线谱的,小廖也决无意让她从那豆芽菜学起。他教她学琴,充其量只是教她拉个歌儿罢了。不过从那时我确信了二嫂是会唱歌的,因为没过多久,我从那上气不接下气的断断续续的琴声中听出,她居然拉出了《花儿与少年》的头几句。
她学得可真快。
她拉琴时,我多半坐在一边看我的书。她说我在旁边她的胆子就大些。她总是事先割好些艾蒿,逆着风燃点上,好让那些浓浓的烟等把蚊子赶跑。有时小风倏忽换了方向,烟呛得我眼泪鼻涕直淌。我从那淡蓝的雾气中跑出来,却见她全无知觉地坐在那里,泪光盈盈的眼睛里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金色火苗,又有一排洁白如玉的琴键,如修葺一新的石阶,从她的眼底里伸展到远方去……我想她有生以来也许是第一次,陶醉在用自己的手弹奏创造出的、笨拙杂乱然而是赤诚朴实的音响中了……
她开始帮小廖洗衣服,补衣服。有时开饭小廖来晚了些,她便从厨房里拿出不知藏在哪儿的事先留好的菜或是几个煮鸡蛋,笑眯眯地看着小廖舔嘴抹舌,吞下去。小廖受之无愧,吃得理所应当,没过多久,干脆连被单褥单和几年没洗一回的油黑锃亮的破棉袄旧毛衣,都一股脑儿捧来让二嫂替地拆洗,二嫂自然有求必应,洗净了衣服,还把自己家留着的一包新棉花拿出来给他絮添上。脱了线的毛衣袖子也重新织了一遍。她的琴一日日有着缓慢然而不可否认的进步。她似乎终于能把《花儿与少年》结结巴巴地从头到尾拉下来了。
二嫂的眼里终日喜气洋洋。
小廖说我,那个……那个叫啥……叫啥乐感,说我乐感好。
小廖说我假如生在城里,同她们一样聪明。
小廖说就先学这支歌。学会了,学得滚瓜烂熟了,再学新的。他说这样不易忘记。
小廖咋还没女朋友呢?多好个人……他自个儿对我说的呗……
变化就这样悄悄发生,在二嫂的手指上和心里。她不大爱笑了,眼睛里时常熟过幽怨迷离的云。没事便一个人静静地呆坐一边。望着远远的地平线出神,她蒸出的馒头不是碱少了就是碱多了,还烘出了一锅夹生饭,我隐隐地感到不安。
现在小廖已经不需我去请了。只要菜墩儿一走,他便主动背琴而来。常常是他拉一段,二嫂拉一段,一段、一段地示范指点,给二嫂吃上了小灶,居然不厌其烦。这一日傍晚,我在木墩子上坐了一会儿,觉得腿上有蚊子咬,嫌那艾蒿烧得不好。站起来想去拨火,无意抬头,见小廖的两只手都落在二嫂的手上,捏得紧紧。二嫂并没有恼。钢琴声,似是中止了,四野静寂,只听见两人的鼻息。
我进退两难,终于悄悄走了。
连队里开始有人在背后嚼舌。说二嫂与小廖如何如何。百十号人,就在这几顶帐篷几间破房下住,谁能瞒过谁呢?况且除了吃饭干活也没有别的事可做。那一日送饭去工地,竟有人当着小廖面开起玩笑来,玩笑开得放肆。小廖却满不在乎,嘿嘿一乐,答道:“这有啥?二嫂跟她老头说说,以后咱们坐车都方便啦!”
众人哄笑。我恨不得给他一嘴巴。
收工后,我到他的帐篷门口把他叫了出来:“小廖,你得为二嫂想想,她有丈夫。”我的声音发抖。
他冷笑一声。“她愿意,你管呢。”他说,“现在她胆子大了,以后你也不用来陪她了,省得碍事。”
说完便蹿上几步,走开去。
我追上他,对他说,人的感情不是手风琴,你得对二嫂负责。他竟不睬,一副鬼迷心窍刀枪不入的样子。
那以后,假如菜墩儿白天出车,小廖便堂而皇之地请起病假来。他不知用什么法子贿赂了连长,连长眼开眼闭。而菜墩儿当然是什么也不会知道的,他人缘不好,没人给他通风报信。他开春时挨着机库那堵破墙,自己一块坯一块坯脱出来搭成的小土房,现在公然变成“琴房”。
不过从那儿传出琴声的时候很少。那扇小门悄悄闩上时,世界都沉默了。
二嫂变得恍恍惚惚的。她总似有难言的隐衷,欲言又止。她躲避我的目光,有时做着饭,无意回头,见她满面泪痕。
“你倒是咋了?丢了魂似的。”我问。
她摇摇头,叹口气,不答。半晌,突然说:“假如这满甸子的苇子割了能卖钱,该多好。”
“你想家了?没钱回家?”
“不。”她缓缓说。“我想要是有钱买个琴,就不用再借小廖的了。”
“小廖不是顶愿意借给你使的么?”
“不,你不知道……”
似有什么触了她的痛处,她背过脸去。
她仍然只会拉那《花儿与少年》,不过,终于是一日日有腔有调有节奏的了。
我仍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能也不敢告诉她。假如她和小廖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她和小廖各自付出的代价决不会是一样的。
苇子渐渐发黄,蒲棒一日日泛白。大雁快要南飞。等下了霜上了大冻,水利队就该暂时撤回分场,全体放假三个月了。也许到那时候,该死的《花儿与少年》就会永远地结束和消失。许多事情当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的时候,就只好祈盼它早日终止。我早已看透了小廖,他用他那架破琴在换二嫂那颗完整的心。虽然他本来要的只是一个女人。
偏有几日又回暖,竟又闷热起来。似乎是为了犒劳水利队一夏天的辛苦,场部派来了放映队。那天晚上,就在河堤上支起了银幕放电影。全队几乎都去了,是个什么片子,早已记不得了,只记得电影演到一半时,从机库那里传来一阵阵粗声粗气的辱骂声,又听一会儿,那叫骂声越发大了。我心一紧,赶忙悄悄地溜了出来,往机库那边跑。天已黑尽,借一片月色,竟看见莱墩儿把二嫂按在她家门前的地上,手里操一根皮带,发疯似的抽她,一嘴白沫,也听不清骂些什么。二嫂只是咬着嘴唇,不哭不闹,一句话没有,任凭皮带没头没脑落在她肩上身上,辫子散开了,羽毛似的飞起。我一把将菜墩儿拦腰抱住,叫二嫂快跑。菜墩儿一伸胳膊,将我推个趔趄,回身举起皮带又要抽。我抬头,见二嫂已从地上翻身爬起,却不跑,迎面朝地上的一个什么东西扑了过去,将它死死抱住,继而,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看清了,是那架手风琴,它中间的风箱被撕裂了,大口似的张着。
二嫂抱住它,半跪在地上,眼泪如雹子似的砸下来。她弓缩着身子,哭得昏天黑地,似乎这时候菜墩儿的皮带再抽下来把她抽死,她也不会知道。这情形倒叫菜墩儿愣住了,悬在空中的手垂下来,半晌,猛地吼道:
“你还有脸哭,我叫你这辈子再摸不上这琴!”
说着就一脚踢过来,琴再一次落地,发出一声鬼哭狼嚎似的怪叫。二嫂默默地走过去,她已经不再哭了。她抱起琴,像抱起自己的孩子。忽然回过头,冲着菜墩儿一字一字地说出一句话;
“不过了,我走!”
这一夜她同我睡在一起。一宿无话。她没有向我说明菜墩儿发作的起因。我也不便多问。料想是有难以出口的经历。可她睡得很香,很沉。好像终于把许多天来的重负卸去了,又好像她说出那几个字,是早已深思熟虑的事。可是她真要同菜墩儿离婚,以后的路怎么走呢?小廖决不会……哦,刚才菜墩儿毒打二嫂的时候,小廖根本就连影子都不见。
那以后拖了些时日,他们终于是双方去了总场,拿回来各奔东西的证明。于是偏僻冷落的水利队,热闹了一阵子,纷纷传说着放电影那晚上的情形。我差不多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原来那天菜墩儿穿着一双布鞋去看电影,看了一半,觉着脚下蚊子咬得凶,便回家找靴子穿。这儿的人夏天在外看电影都穿高统雨靴,省得挨咬。他敲门,门插上了。二嫂半天才来开门,说是头痛先回了。菜墩儿找靴子半天没找着,想起来在板铺下,伸手去摸,却摸着只脚,吓得他蹦到门外,却见一条人影从床下蹿出,夺路而逃。
看电影的人散时,二嫂已被我领走,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丑闻。至于后来传说得这么有声有色,当然是菜墩儿为了让人同情他而到处散布的。他每每讲完了,总还要补上一句:“那臭娘们还想跟我离婚?离就离,看我不出两月再找个黄花闺女!你当小廖会娶她,做梦去吧。他敢回来,揍不死他!”
小廖果然一连几个月没露面。听说是回家避风去了。来年开春,他回来办关系,还没忘了把琴拾掇一遍,卖给别人了。而菜墩儿为了赌气,果真在两个月内娶了邻近屯子的一个姑娘,调到九分场开车去了。
第二年开江化冻之后,水利队又回到原来的龙王庙!旧址安营扎寨,我也从南方探亲回来,我发现二嫂已把自己的行李搬到那个小房。一冬的风雪侵袭,小房已有些摇摇欲坠。二嫂用破油毡纸苫了屋顶,钉严了门窗,似乎要在那里头住一辈子。
“你还是同我们住一块儿吧。”我说。
“不,”她的头垂得很低,“我想拉琴,怕吵了别人……”
仅仅一个冬天,她过去那油黑乌亮的辫子变成了一堆蓬松萎黄的干草。腮上的酒窝让两道细细的皱纹横穿而过。一夏天,她都用那只伤风漏气的琴,在拉一支我从未听到过的新歌。她再没有拉过《花儿与少年》,虽然她已拉得很好听了呢。
那年夏末,我调到场部去工作,离开了水利队。她没有来送我,在“热特”的引擎声中,我隐隐听得从小屋那儿传来一种单调的琴声。听起来它已不大像是手风琴了。它一直在那里重复回旋,只有一句,始终听不出来那是首什么曲子。
这阵子上街,总闻着一种叫人垂涎欲滴的香味,从街面旮旯里冒出来。那香味儿好怪,绝不是什么油炸臭豆腐或是烤羊肉率之类,直钻鼻腔的,颇有刺激性的浓烈香气,也不是韭菜炒鸡蛋、桂花藕粉那样平常日日可以闻见的沁肺爽气的清香。这香味似曾相识,又从极遥远的异地传来,像一股地心的热气,将你团团围住,立时就挣脱不得,浑身热辣辣地烧得难受,也没觉得怎么呼吸,那腥辣的香味儿便弥漫了五脏六腑,钻透骨髓,头顶脚底地乱窜。若是深吸几口,初时只觉血脉沉重,四肢雷击似的瘫软,昏昏欲睡;继而便感到通体灼烈,热血沸腾,筋络颤抖,不知不觉地生出了气力和精神来。这绝不是那种供人消遣逗人食欲的香味,而是一种生命的祭礼,一种灵魂的补充……
我沿香味飘来的方向寻去。我自知我是极熟悉这个气味的。只可惜它仿佛名称就在嘴边,我却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它说出来。我明明知道它是什么,但我却忘了它是什么,我的鼻眼嘴同时敞开,我恨不能将那香味放在舌上嚼一嚼,它却踪影全无。
踏破铁鞋。
昏黄的暮色中,我望见街边的一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下,有几只矮矮的小方桌,矮得同凳子一样。说它是桌子因为它的四边还有几只更矮的小矮凳。每只小桌子上放着一只炭火熊熊的小炉子。有只桌子旁边已围上了人,那小小的炉子上便有一只硕大的砂锅,锅里爆出毕毕剥剥的响声。那叫人的肠肚翻江倒海卷巨澜的奇异香味,正从那砂锅里传出来。
我在靠边的一只小桌子旁边坐下来。店主走过来招呼。“是夜市吗?”我问,“是夜市。”他回答。“来一份。”“好罗——”
拉美那年冬天死在场部医院里。
我过了好久才听说这个消息。
我似乎并没有怎样的震惊,我甚至暗暗松了口气,他是罪有应得。我居然闪过这样的念头,否则,他这样的人,不死也终归会进监狱,判个无期什么的。
我竟会变得这样残忍。真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其实拉美活着的时候同我关系还不错,因为我曾帮他写过几份检讨。拉美只念到小学毕业便遇到大风大浪,后来糊里糊涂跟着巷子里的“头儿”们来了北大荒。他出身挺好,三代血统工人。如果不误入歧途,满可以入团入党走一条阳光大道、但在城里闲散游逛的三年养成了他好吃懒做的习性,他到农场的第三天就逃跑了。以后不知被何方遣送回来,从此就写检讨度日。一份检讨写了半个月还只有两个字。据说连队的哥们儿都被他求退了,才咬咬牙在铲地时接了我的垅。我同他会会时锄头钩在一起,抬起头一看是他不由大吃一惊。谁都知道他抱一条垅铲个头便往垅沟一躺打起呼噜,待一觉睡醒拖着锄板顺垅沟追上去,还能恰好赶到垅尾。北大荒的大豆地,一条垅够铲上一天的。在拉美手下,一夏天多少条垅就白白扔了。
没人敢管他。起先有个不知好歹的排长,让他从头返工,结果晚上一掀被,抖出只死耗子。
拉美便是这么个无赖。对他来说,接受再教育倒是非常必要偏偏就是他这样的人,倒常常教育旁人。
“你说,对同志不是要像春天般温暖吗?”他站在地中央,斜睨着眼涎笑,“都说你墨水好,你给老弟写份检讨怎么样?老弟不会亏待你的。”
我望着他让烈日暴晒成肝酱色的脸上那双眯起的肿眼泡,目光虽然汹汹却分明胆虚,口气虽然强硬无理却分明心怯。一个混世魔王不到了走投无路的分上,不会来求我们这些素日从不在眼里的女生。这么说他也够可怜的了,那一瞬间我竟痛痛快快点了点头,我觉得让他那么个家伙同我纠缠不清实在有点令人难堪。
“答应了?”他一拍大腿,“你可说话算数。”他当即掏出两条生黄瓜来,扔在我脚边,“以后要什么,尽管开口。”
我从那两条黄瓜上跨了过去。我不想理他。尽管我似乎闻到了黄瓜的清香,我轻轻咽了口唾沫。顶花带刺儿的新鲜黄瓜,又从分场的菜园子里偷来。
他似乎在我身后愣怔了一会儿。我听见他用脚把黄瓜踩得稀烂。
但我坐在街头的矮桌矮凳上闻到的越来越浓烈的香味,却决不是黄瓜。那香味渐渐朝我走近,一阵风飘来,又飘去。
拉美死在场部医院那年,才十九岁零三个月。
拉美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他有一个怪斯文的学名,但谁也不记得了,都叫他拉美。因为他的皮肤是一种铁锈般的赭红色,连头发也有些发红,又是高颧骨,都说他像印第安人,便叫他拉丁美洲,后来简化了,就叫拉美。
拉美的身体很壮,天热时脱了汗衫,胸脯上露出两块空子肉。他不下地劳动,却常锻炼爬墙钻洞什么的,三天两头请病假,有足够的时间去寻觅食物。
根据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他寻觅的主要对象是邻人的菜园或鸡舍鹅棚。当然都是公家的。他自有一套类似劫富济贫的理论。他寻觅食物的技巧不算高明,但总有收获。若让人抓住了,就写检讨。
他帮我接垅的第二天,我把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字条扔给他,他当即给我作了个揖。第三天看见我,嬉皮笑脸地说;“哎,连长表扬我了,说我的检讨从来没有写得这样认真。他说,噢,他说我对错误认识很深刻,嘻嘻。”
我咳一声,偏过脸说:“就这一次,下次再犯,我可不管了。你这样吊儿郎当的,混到哪一天是个头?”
“看你说的,真想不开,混一天算一天嘛。连你在内,哪个不是在混?”他绕到我面前来,厚颜无耻地挂着脖子里汗泥,“再说,我也没干什么大的坏事,弄只鸡呀鸭呀吃吃,身体健康对国家也有好处的。不是说知青是农场的主吗?主人吃两根黄瓜,不是理所当然吗?农场真要把我们当主人看,为啥随便什么事情也不同我们商量?他们不把我们当主人,就只好我们自己把自己当主人看了,破四旧那辰光……”
“你拉倒吧!”我打断他,“你顶好还是寻寻回城的门路,到自己家里去当主人吧!”
我说完便走开了。其实我也知道他那个三代血统工人的出身,对他回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自己也很明白这点。我惊异的是他竟然还有充足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那个关于主人的宏论我从此念念不忘。坦率地说,我心里岂不也是那样认为的。正因为他偷吃偷拿的都是公家的、农场的东西,我才不自觉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他。我们从来没有把农场同国家连在一起,农场只是同连长主任什么的划等号。在许多人眼里,拉美还是个够哥们儿讲信义的汉子,他利己却不损人。至于损了农场或其他什么,在大家良心的天平上几乎是无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