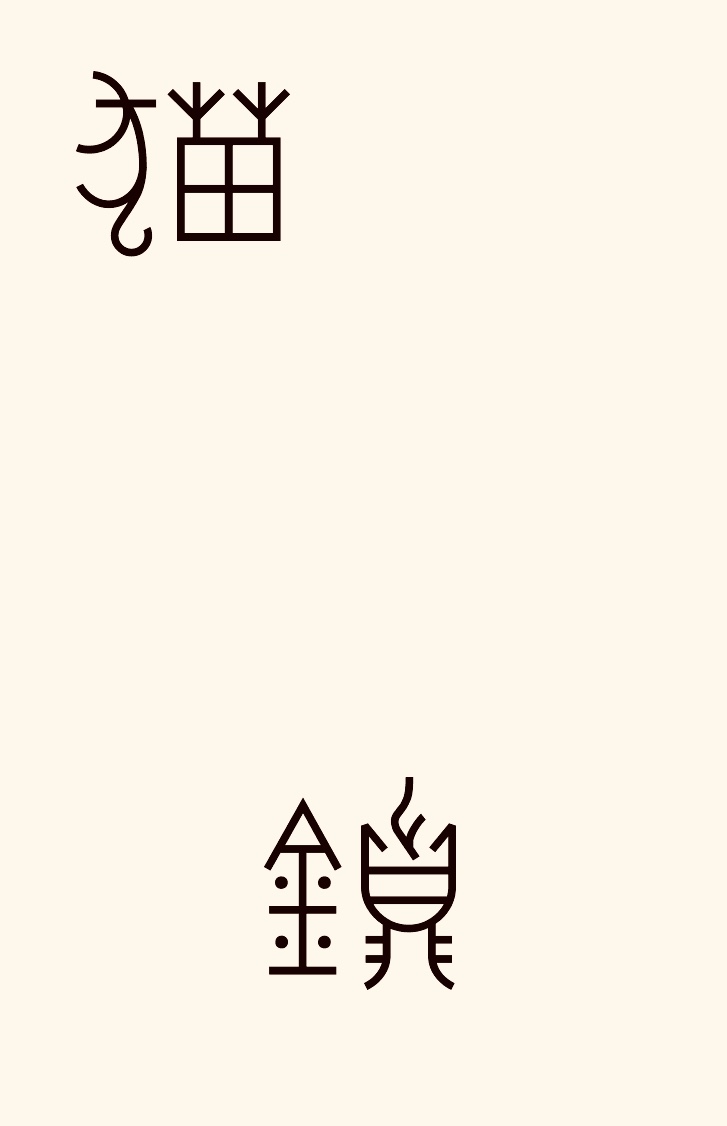华不石道:“嗣昌兄此言,小弟也曾听另一位好友说过,如若你二人相见,说不定倒是能成为知已。”
杨嗣昌道:“哦?那人是谁,嗣昌倒想结识一番。”
华不石道:“嗣昌兄应当早就识得那个人,他就是曹暮云。”
杨嗣昌脸上一愕,半晌才点了点头,道:“原来是他。”
曹暮云是朝中“宦党”的重要人物,杨嗣昌当然不会不识,但他却是“五王党”中人,这两党一向都是冤家对头,他们两人自是难以成为知已好友。
华不石却微微一笑,道:“其实这世上并没有永远的敌人,有志相同,嗣昌兄又何必去计较党派之争?”
杨嗣昌听得出这位大少爷话中有话,问道:“华少爷此言何意?”
华不石道:“嗣昌兄认为当今的大明朝,最大的危机是甚么?”
杨嗣昌本是才智出众之士,且身在官场,对于当今朝廷的忧患早已深思熟虑过无数次,当下便道:“当今朝廷的危机,首推各境纷起的匪寇,如今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成了气候,还有其他十余股流寇,拥兵数十万之多,实是国家大患,除此之外,北境的满清鞑靼,亦是一大威胁。”
华不石却摇了摇头,说道:“匪患和异族固然威胁甚大,但以小弟看来,大明朝廷最大的危机却并不在此。当日在豫境开封城的杨家大宅,兄台与我畅谈天下大势,嗣昌兄见识广博,对于如何应对义军和满清鞑靼早有卓见,令华不石由衷佩服,只不过这许多年过去了,何以却全然未得实施呢?”
杨嗣昌闻言一愕,道:“说来惭愧,自罢官之后,这些年愚兄一直赋闲,且父母先后亡故,只能在家守孝,在朝中未任实职,虽然我在‘五王党’内有些根基,但以一党之力毕竟无法掌控朝中的大局,那些想法自然也就无力实施。”
华不石一拍手掌,道:“这就是了。在小弟看来,当今大明的首要问题并不在于兵患,而在于党患。试想朝廷中的文武员官皆把一党之私置于家国之上,整日为争权夺利而争斗,又岂能齐心携力,应对其它的危机?”
杨嗣昌叹息道:“朝中官员结党弄权自古就有,大明朝自也是少不了,到了前朝宦官魏忠贤专权之时犹为严重,当今圣上继位后,虽然铲除了魏宦,但这十余年各党羽翼已成,争斗反比前朝时更加激烈了,几近到了不结党便不能保官保命的地步。此乃朝廷的大患,愚兄又岂会不明白,只不过无力改变罢了。”
华不石想了想,忽然道:“如若没有党争之患,嗣昌兄得到朝廷之中大部分文武官员的支持,且能够调动大明朝现有的所有财力兵力,可有应对当下内外兵患的把握么?”
杨嗣昌凝眉道:“如若真有那么一天,嗣昌虽不敢说有绝对的把握,但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保住大明江山社稷数年的平安,应当是能做得到。”
当日在豫境时,华不石与杨嗣昌便曾在一起指点江山,纵论国事,此时虽然已是深夜,二人却无困意,在桌边一边饮茶一边议论,直聊述了两个时辰,直到东方天色微明方才作罢。
倒是那位将军余爵虽通晓兵法,对于政事方面的见识却是平平,只在一旁陪坐,插不上甚么话来。
在言谈之中,华不石得知杨嗣昌这些年虽然赋闲,却四处游历,对于时下各境义军的发展形势极是了解,亦取得了各地藩王的信任和器重,俨然已成为了“五王党”内的牵首人物。
大多数江湖中人对大明朝廷都没有效忠之心,华不石亦是如此。当日在豫境时所见官府屠杀无辜流民的景象还依然历历在目,而他亦不会记,小宁宁一家人便是死在官军马队的手里。
华不石曾相信李自成是胸怀救世之志的大英雄,也曾经全心帮助过义军,但结果却是令他失望之极。而在这位大少爷看来,皇帝朱由检就与闯王李自成一般,他们一心所想争夺的只是江山和皇权,所以并不值得投效。
当然,连年的战事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无尽的杀戮之灾,亦非华不石所想见到。如若能真如杨嗣昌所言,开创一个新的格局,平定忧患保住大明朝的江山社稷,他也并非不愿出力。
与杨嗣昌的述谈之中,一个念头在这位大少爷的心头闪过,只是他却并没有说出口来。
※※※※※※※※※※※※※※※※※※※※※※※※※※※※※※
第二日一大早,众人便即拔营启程。
剩下的路程走得颇为顺利。一行人马浩浩荡荡沿着虎什山西行,既未遇当地女真部落的阻截,也没有发现“黑风旗”和“虎憨兔部”人马的踪迹,想来他们自知难以敌过霹雳营,早已远远逃遁了。
晌午过后,前方便已到了白马关。
在北境万里长城的诸多关隘之中,白马关只能算是一处小关塞,距离京师约有二百里路程,驻守在此处的官军仅只有百十余人,守将是一名从七品的把总,名叫于天成,亦是“五王党”的人。
早在数日之前,杨嗣昌就已遣人给于天成传了消息,当队伍靠近关隘时,远远便瞧见有二三十名戎装齐整的兵士,在关口之外列队迎接车驾。
眼见着队伍行近,为首的一名满脸胡须,身材粗壮的军官迎上前来,对杨嗣昌参拜道:“末将白马关把总于天成,见过杨大人!”
杨嗣昌早年官居河南按察使,现下虽无官职,在“五王党”中的地位却是不低,是以于天成依然称他为杨大人。杨嗣昌打量了这壮硕的军官一眼,摆了摆手,道:“于把总不必多礼。我在密信中嘱咐过你,不得向外泄露太子和公主的行踪,你可照做了么?”
于天成道:“末将谨遵吩咐严守机密,便是守关的兵士,也不知道今日到来的是太子公主的车驾。”
杨嗣昌点了点头,道:“好。你带兵士在前方开路,我们立时入关。”
于天成应道:“是。”随即又道:“现下已到晌午,末将命人备好了饭食,太子和公主是否在关隘内略作歇息,用过了午饭再走?”
杨嗣昌道:“不用了,我们在此地不做停留,直接赶往京城。车驾入关之后你要小心把守关隘,回到京师我自会给你记上一功。”
于天成道:“末将遵命,多谢杨大人栽培。”
他回身传了几句命令,在门外列队的数十兵士随即向两侧让开,迎候车驾入关。
一行人马行进的顺序,杨嗣昌和余爵带领官军骑兵走在最前,护卫着朱徽婵朱慈烺所乘车驾,之后是押送君父的囚车,“恶狗门”的两部人马和“百隆行”的弟子垫后,华不石,司马如兰诸人也都走在后队之中。
前方的人马很快便进了白马关,太子和公主的车驾也在一众骑兵簇拥下进了关门,华不石行近至关前,目光望向关墙之上,脸色忽然一变,道:“此关好象有些古怪。”
三丈多高的关墙上黄龙旗高悬,旗下站着一排数十名身着号服的兵士,皆是腰挎着长弓箭袋,一个个神情肃然,垛口上还摆着数架连弩、投石机等守城的器械,皆有人在旁操纵。
若只是迎候友军入关,这些兵士本是完全没有必要如此严阵以待,华不石的目力甚佳,立时就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
华不石的话音未落,一匹马已从这位大少爷的身边如箭一般蹿了出去,马上所骑的正是厉虎。相比华不石,厉虎对危险的感官更加敏锐,一到近处便已察觉到周围的杀气,他策马前冲,一面大喝道:“小心,他们都是‘天诛’的人!”
却只听到“喀喀”声响,前方的门洞中间,一道铁闸直落了下来!
此时的朱徽婵,正闷闷不乐地坐在马车厢里,弟弟朱慈烺就在身边,而马车已驶进到了关门之内。
使得这位公主千岁心情低落的人,正是厉虎。
昨天晚上,厉虎来到朱徽婵的帐篷,聊了几句话,便说起车驾回到京城以后,他要去追踪施青竹和葛力,暂时不能到皇宫里当侍卫。因为先前向厉虎讨剑之事,朱徽婵的心中本就有些不满,听到此话就沉着脸道:“你不当侍卫就算了,谁稀罕么!”
她说的只是一时的赌气之言,满想着厉虎定会低声下气说些好话哄她开心,却不料厉虎在旁边“嘿嘿”笑了几声,便告辞走了。
朱徽婵从小在皇宫里长大,就象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儿,此番被劫出京虽然过程颇为惊险,但她却经历了以前从未想过的事,又品尝到了那种或许是爱情的滋味,内心倒甚觉快乐。
想着进了白马关,再过两天就要回到京城,又得过回到以往那种无聊乏味的日子,朱徽婵心中颇为不舍,只想着在外面多玩几天才好。幸好厉虎进皇宫里做侍卫,以后陪在她身边教她武功,也可以聊解寂寞,却没想到这时候他竟会变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