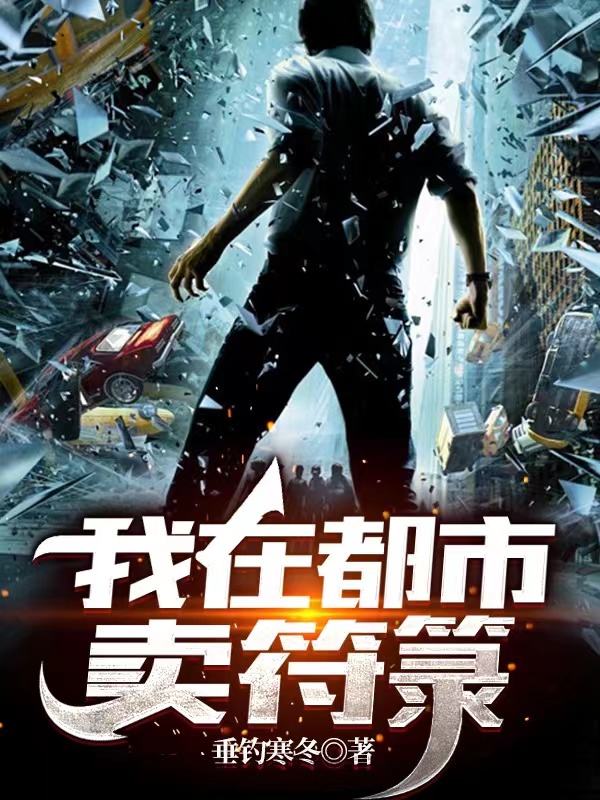焦安泰把两孩子支出去。
东屋里也把心放下了,摸黑在院子里听了会儿动静,稀稀拉拉的说不定哪个方向就响起枪声,听着溜墙根儿了,鸡犬相闻的热闹渐渐消停了,夜幕掩盖了人们猜测的真相,家家户户揪着心,灯都不亮一个。
冯妮湘忽然的伸出胳膊抱着焦安泰的脖子吧嗒吧嗒掉了好几滴眼泪,也说不上委屈,也说不上害怕,就是想这样的撒会子娇,焦安泰把光溜溜的冯妮湘抱出木盆,轻轻地拿布蘸净了水珠,心疼的放进被窝里:“姑奶奶!我去找找还有跌打酒什么的吗?”
“不用,不怎么疼了,折腾的大哥他们也不消停,好像多大事儿一样。”冯妮湘枕着焦安泰的胳膊,咕噜着眼睛:“今晚我看见绺子旺了,专杀龟儿子来的。”
“吓傻了,你怎么可能看见那个胡子头。”焦安泰半信半疑揉着冯妮湘的背:“听着好几处枪响呢!听说绺子旺也就一百多杆子枪,哪来的这么大阵势。”
“真的!”冯妮湘淘气的挠着焦安泰的下巴:“骗你狗狗!”
冯妮湘就把绺子旺枪杀龟儿子的过程着重讲了一遍,自己帮忙弄枪和被人踢来踢去的哪一环节省略了,焦安泰胆儿小,可别吓着他,唠唠叨叨的能把大天唠叨下来,当然,关于那个耳熟的丫头片子声没说,说了大哥还不得扒了焦仲玲的皮,在未证实之前,冯妮湘可不想给家里扔个炸弹,末了冯妮湘还嘚瑟一句:“我很花木兰吧!”
焦安泰喘了几口大气:“天哪!你傻大胆啊!认识绺子旺这还了得!没人看见吧!”
“黑咕隆咚的,就客厅门口的一盏小灯,我趴在阴影里,谁顾着看我!”冯妮湘小得意,啃焦安泰的下巴。
“记着,这可不是显摆的事儿,跟谁也别说,要掉脑袋的。”焦安泰后脖颈子嗖嗖冒冷气,抱紧了冯妮湘:“你看吧!鬼子还不疯了。”
“听着好像给龟儿子喂枪子儿了。”冯妮湘觉得很解气,在焦安泰怀里不安分的踢腾着。
“明天就知道了。”焦安泰拉灭了灯:“你看吧!鬼子还不铲平了驮马沟啊!”
“你以为绺子旺是省油的灯啊!既然敢戳这马蜂窝,一定就有防范。”冯妮湘脑际闪过短胡茬的眼神,竟觉得一凛,是个人物,不!是条汉子!
“是条汉子!”焦安泰觉得前几天损失的那几根金条也没什么了,耿耿于怀的劲儿也没了。
“我见着高贵妃了。”冯妮湘一点不高兴,把焦安泰拉上来的薄被子一脚给踹到脚底下去了。
“凉!”焦安泰用脚勾着又把被子拉上来:“不是没开锣就乱了吗?”
“她单独给我嚎了一嗓子!”冯妮湘一肚子火发作了,又一脚把被子给蹬了:“就这么脸儿对脸儿。”
冯妮湘往上爬,和焦安泰平行对脸的演示一遍,光看见眼睛里晶晶亮了,其余的啥也看不清。
“不会吧!媳妇儿!你这么大面子,清唱的?”焦安泰好奇了,把冯妮湘摁回自己的怀里:“老实点儿!搁章太太屋里?你沾光吧!”
“在桌子底下,绺子旺用枪给打的锣鼓点儿。”冯妮湘像鱼一样滑溜溜的在焦安泰怀里翻身,拧着细腰,撅着屁股,给了一个愤懑的后脑勺,把牙磕在焦安泰的胳膊上:“她居然骂我,还把我往桌子外面推,要不是我脸皮厚就不出去,要么被打成筛子要么就被踩成肉饼子了。”
最委屈的莫过如此,自己的偶像竟然转眼之间暴露本性,冯妮湘觉得受到了欺骗和伤害。
为了看她的戏,还和焦安泰冷战了好几天不说,还在阎王爷的门口打了个逛。
“做人和做戏是两码事,说过多少回了,长点记性好不好?哇!拿我撒气啊!你的脾气呢!你干嘛当时不回敬她一段《打渔杀家》。”
抚摸着焦安泰的胳膊上一圈儿牙印子,冯妮湘无声的抽笑 ,火气没了,高贵妃见鬼去吧!
“你就跟我有本事!”焦安泰扳过冯妮湘的肩,轻轻舔着冯妮湘的鼻尖,而后嘴巴,而后颈窝儿,而后······
第二天,折腾了一夜的林城就像个雷区,所有的人都小心翼翼,***像安在了每个人的神经里,生意也不做了,门打开条缝儿,先探头探脑一番,街上冷清的厉害,日上三竿才见有人走动。
松北路没有以往挨门挨户的扫荡,但是不代表波澜不惊。
翟小第一趟溜溜的回来:戒严的是警备旅,一队队的鬼子开出城了,车站和码头抓了好多人!
金爽可没翟小机灵,溜墙根儿还没出松北路就转弯儿回来了:悬赏缉拿绺子旺,五千大洋!末了跟了一句:那告示那叫红,粘告示的浆糊还热呢!
貌似还平静啊!
松北路渐渐地热闹起来,街头巷议,绺子旺被这个嘴巴出那个耳朵进,说的跟天兵天将下凡一样,街坊四邻的交头接耳。
焦安邦到章知礼府上周到,据说章知礼挂花了,成了一只耳。
傍晌午,仲槐和仲玲结伴儿回来了,溜儿溜儿的,一见焦安邦没在家,伸腰展眉长出了口气,不痛不痒的挨了娘的几句骂。溜溜儿的各自回屋了,冯妮湘没跟焦安泰上柜台,悄悄的跟仲玲,仲槐是个锯了嘴儿的闷葫芦,问也问不出个囫囵话。
“婶儿!你吓死我了,跟我干嘛啊!”焦仲玲悠荡着两大辫子,关上门。
冯妮湘看她装模作样的拍打前胸,一屁股坐在小仲心的床上,对面的仲玲也坐在床上,故意没事找事的忙活着不看冯妮湘的眼睛:“婶儿,听说,昨晚上可热闹了,龟田被绺子旺打死了。”
“你没凑热闹啊!”冯妮湘打眼细看仲玲,仲玲一脸若无其事,这个小丫头!
“婶儿!我哪有胆量凑那个热闹!”焦仲玲把床单弄得像床板一样平还在弄。
“那谁是杨靖宇的队伍!”冯妮湘抱着膀,胳膊肘还有些疼,她就这么笑眯眯一切明察秋毫的看着焦仲玲。
“婶儿!”焦仲玲圆乎乎的脸白了。
“丫头片子!你没那个胆儿?你哥没你那个胆儿我还信,你婶儿我的眼睛不但好使我耳朵灵着呢。”冯妮湘揪了一下焦仲玲秀气的小鼻子:“看你还赖!昨晚儿我也章府,差点儿没被踩断了脊梁骨,喏!”冯妮湘一抬下巴,半寸长的血道子正在下巴颏,不留神还不注意:“再给我装!”
“我的好婶儿!可千万别给我爹说,您得给我保密!”仲玲挨着冯妮湘磨叽,冯妮湘看见她的膝盖上包扎了,手腕肿了,淤青一大块。
“不给你保密,我们得被抄家,小祖宗!你爹打死你也不多,你说你丫头家的你胆儿忒大了,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小孩子家家的。”
焦仲玲反正知道婶子刀子嘴豆腐心,被点的脖子一抽一抽的光抿嘴儿不顶嘴。
“仲槐呢!你二哥?”冯妮湘脑仁子疼。
“也去了。”
冯妮湘的脑仁子不是简单的疼了,简直就是被打了个洞,嗖嗖的风冷骨寒,自己还没后怕呢,为这两孩子后怕死了:“你早晚得把你爹你娘给吓死!”
“婶儿!我们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您别这样,不告诉他们没事儿的。”焦仲玲拍冯妮湘的后背。
“啊!还有组织?”冯妮湘几乎要惊掉下巴:“还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