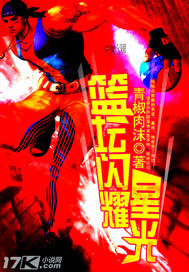“小心!”一抹黑影飞奔而至,单手携着花爻不盈一握的腰堪堪避过那人的一剑。花爻抬头便看见,那头戴头盔,身穿战袍的人,全身萦绕着淡淡的杀气,平日柔和的下颌也分外刚毅不羁,那温暖的双眸此时也迸发着摄人的目光。
“张青……”花爻小心的唤着,害怕这如梦境一样的画面一碰即碎。
微微侧目,凌厉的眼光不禁也柔和了些,张青点点头,飞身将她带到安全处。随之长剑一挥,那两百随骑便杀气凛然的奔向那几十个黑衣人。将他们团团围住。他站在圈外犹如掌控生死的神明一般,漠然的看着他们的苦苦挣扎犹如困兽之斗。旁边张东篱也抽身出来站在他一旁,张东篱有些紧张的看看黑衣人随即目光一转,看向了花爻,眉头瞬间就释然了。
“陛下,刺客已然被捕,还请陛下明示。”张青一身黑甲肃然的说道。
“呵呵,爱卿回来便又替朕费如此心,真是难得。至于这些……”他故意停顿了下,眼角瞥瞥花爻,轻笑道:“即刻处死。”
花爻一愣,这些人突然的袭击,好不容易全部活捉,皇帝竟然不问缘由便要即刻处死?花爻有些疑惑的看看刘澈,只见他低低的同陈年年说着些话,那女子的脸上不觉的便浮上娇羞的红晕。
“呵呵,皇帝陛下,张将军不愧为我天朝第一男儿,不过,”平乐公主眉眼一瞥,笑盈盈道:“花爻姑娘也算是吉人天相啊,那么多人竟是没有伤到你分毫。倒像,呵呵,倒像是是有意放手呢?”平乐公主看似好心的握着花爻的手嘘寒问暖道,却引得花爻心中鸡皮疙瘩不已。
“花爻姑娘人好心善,这群刺客看样子也是无心为难她,长公主难道还希望波及无辜么?”皇后平淡无波的看向她,嘴角仍旧带着浅笑。
“民女该死,没能好好的保护皇上,娘娘,让皇上,娘娘受惊了。”花爻拜服。心中却苦闷不已,自己到底是犯了哪堵大神啊,在此时竟然惹得长公主和皇后将争斗放在了明面上。
“罢了罢了,你且起来吧,不关你的事,何来该死之说。”皇上有些不耐烦的说道,“张青。”
“诺!”
谁知,张青还未走到那群人面前,便见那黑衣人一个个的闷哼一声便倒地不起,花爻大惊,其中一名黑衣人还眷恋的看着自己,双目澄明却饱含不舍,那是刚才故意对自己忍让的夏问。虽知对方是敌非友,但,他也只是单纯的保护他想保护的人,只是弄错了而已。看着他痛苦的扭曲在地上,随即瘫倒在地再也无任何生命的气息,花爻心中仍有些唏嘘不已。扭头看向那顶着香川容颜的陈美人,花爻目光满是讽刺。
这样,你可满意?
凤鸣摇,凤鸣摇……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何?让我代替你再去死一次么?
刘灵,你竟如此恨我!
“陛下,刺客自服毒药全部毙命。”
刘澈摆摆手,有些兴趣乏乏的点点头,“朕本意是迎接将军胜利归来,不想却惹上这样让人扫兴的事。罢了罢了,晚上朕设宴接露殿,替将军接风!”
张青叩拜在地,“谢皇上!”
一场欢迎会被闹成了这样,羽林军头领劝说皇上先行回宫。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往皇城行去,花爻站在空荡荡的城门下方,却觉得有些难受。方才张青刻意躲着了自己的目光,难道是相信了自己与那些刺客有关系么?
“怎么了,回家了呀。”张东篱用宽厚的手掌在她眼前晃着。
花爻抬头,一脸迷惑,紧张的看着他,“东篱,我……”
“别想了,舅舅定然不是那般认为的,开始公主那般针对你,加上确实,确实那些刺客有意为之,舅舅也没办法明目张胆的为你开脱。放心,皇上圣明定然不会牵累于你的。我们先回去可好?”
张东篱小心的牵着她的手,道路因为刺客的原因空落了不少,张东篱命人牵过马,携花爻上马。
不远处有人一双眼睛却紧紧的盯着这有些失魂落魄的人,喃喃自语道:“是她?”
“主上,我们该撤了,想来不过多时那皇帝也要下命封城,到时我们便不好脱身了。”
缓缓的合上纸扇,望着那骑马而去的人,若有所思,“阿顿都,派人注意那女子,还有查明她的身份。”
“是,属下这就去办,还望主上早早出城。”
“呵呵,好,这长安呵……”
月色迷人,宫灯初上,清风飞扬,高高的琼楼仙乐韶韶,飘荡的衣袂容颜姣姣。钟鸣鼎盛,觥筹交错,一派太平盛世的和乐胜景。
艳丽的红灯照着一群谈笑风生的人,高高的龙椅上坐着慵懒的刘澈,身旁坐着的皇后则更显端庄大方,左右下首分别坐着陈美人和平乐公主,琼浆玉露几杯下去更显人婀娜多姿。
张青端正的坐在席位上,微笑着接受众大人的祝贺,张东篱因为深得皇上宠爱加上又是张青的侄子所以也破例坐在张青的旁边,也骄傲的看着旁边自己崇敬的舅舅,自在的喝着酒。
“呵呵,陛下,关内侯青年才俊,屡建数功,真是我们天朝难得的好男儿啊!侯爷,年年敬您一杯。”陈年年摇曳着婀娜的身姿,巧笑倩兮,顾盼生姿走到张青面前。
“美人抬爱!为国效力,张青只是做了应做之事。”
“呵呵,关内侯还真是谦恭有礼啊。陛下,此等优秀男儿难怪会让长安城的女子芳心暗许呢。”陈年年含笑看了他一眼便走回了座位。
“是呵,关内侯早年丧妻,如今建了这般伟绩是不是该成家了啊。”刘澈突然似来了兴趣般,微微睁开了眼。
“微臣早年克妻,心中仍有余悸,万望不敢再伤害其他女子。”
皇后容颜有所一动,仍是含笑浅饮着琼浆,张东篱则为其感到一丝悲哀。
“胡说!爱卿贵气逼人,何来克妻一说!如若真是有这样的说法,那张爱卿,朕给你指的这婚可更该接受了啊。”刘澈笑着豪饮下一杯,眼中若有所思的看着张青因为听见此话的一怔。
“皇上,臣弟早年凄苦,幸得一妻与之同甘共苦,想来是仍有些情分的。可能心结仍未……”
“人总要忘掉过去的,皇后太过仁厚了,若真是为了青儿好,早该为其寻觅可靠家室才对。”刘澈不耐烦的打断了皇后的话语,仍是盯着张青笑说道,心下思索,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样,是不是更会让他们享受到无上的荣耀啊。“张爱卿,朕几番观察,你与平乐公主也算缘分不浅,平乐公主贵为皇胄定然会让所谓的克妻之说荡然无存,加上,皇后嫁于朕,已是一段佳缘,若你娶了平乐长公主,有了张家的努力朝音的国土才会更加固若金汤呵!张爱卿,意下如何?”
“臣惶恐,微臣家奴出身怎敢高攀公主殿下?”张青立马离席拜服。
“侯爷此言差矣,英雄莫问出处,将军如今英勇有为,公主则是蕙质兰心,气质高雅,所谓男才女貌不过如此啊。”对面一男子一副愤然样朗朗说道。张青抬眼,便看到了正是御史大夫宋诘。其父乃前任御史宋治,为官清廉,虽掌管刑法为人却偏善和蔼,用刑也是很有分寸,然宋诘幼年熟读朝音律令,对父亲的仁义行为不愿苟同,常谓人曰:“仁义乃妇人之为,天朝律令乃是锢人罪恶,倘不能触及其身心,灵魂仍不得醒悟,何谓惩戒之说?”帝感其忠义,颇有赞同,便命其承袭父位,其父老泪纵横,感戴帝恩,却仍不愿接受,旁人问曰为何,其父答曰:“吾儿焦躁过甚,狠绝狡戾,恐其执法酷辣,惹怨他人,不得善终。”然宋治病逝之后,刘澈一纸诏令便擢升其为御史大夫。其接任以来,果如其父所说,对待刑犯无所不用其极,对圣上有所猜忌之人更是千方百计拉入牢狱之中,进而深得帝心。
张青浅笑着,正要起身回礼答复,却见下首东篱已然气愤的站了起来,身子俊朗,神情傲然:“酷刑闻名的御史大夫宋大人何时也中意了月老一职?皇上,如今舅舅虽然凯旋归来,击退了乌智不少侵略,然而,乌智野心勃勃,舅舅是一心惦念边陲安危才无心于儿女情长。大丈夫生于天地,不为国,何来家?公主金枝玉叶,舅舅一莽夫只恐公主受了委屈。微臣窃以为此举不妥。”
刘澈把玩着酒盏,薄唇轻抿,微眯着眼,看着座下那青年男子桀骜不驯的神色,唇角不由得勾了些,这模样,可真像早年的自己呵。
场中因为这年轻男子的朗朗声音,异常的安静了下来。张青微微抬头,却见皇后眉眼之间因东篱的话语而越加紧锁的眉头,侧目再看长公主唯有愠色的面容,嘴角还噙着一丝冷冽的笑意。
众官员察言观色半晌,有想讨好皇上欲说些说服之词的看着张东篱一脸坚毅的模样谁也不敢再惹这个“张大头”,而对于圣心,也不敢贸然揣测,大家只好默然喝酒。然而就是这样,时局虽是有利于张青,张青心中却无奈万分。这无异于秦时赵高的指鹿为马,如今皇上说了有想赐婚的想法竟然因为张氏一族的婉拒惹得朝臣不敢再向皇上进言,倘若仍然拒绝,是不是张氏一族已然会成为皇上心中不得不拔出的钉子啊。
他走出了坐铺,一袭青衣出尘不染,他缓慢的走在殿中,服拜在地,动作恭敬而不失文雅,声音清明有着成熟的沙哑性感。
“臣,叩谢皇恩!”
回忆起白日在家中那女子姣好的面容,如清丽的芙蓉一般,脸侧似乎还有她秀发的香气,手中仍能感觉那如凝脂般的皮肤,耳际仍在徘徊着她带有些愉悦而兴奋的话语“张青,你原是在乎我的!”心中唯有叹息。是呵,正是因为在乎所以,才如此。自己已然被权势,被尔虞我诈弄得如此不堪,不想,不想呵,她也卷入这腌臜的漩涡。
“舅舅!”东篱愤然出声,手不由自主的握成拳头,本想踏出去,质问为何,却见那高高在上的皇后正微不可见的面带忧色的冲他摇头。紧抿嘴唇,他按下了心中的冲动。
“好!哈哈哈哈,快起快起。张爱卿神勇无比,逐外贼出我国境,擢升兵马大将军!今日复得如花美眷,更是喜上加喜啊!天道官,近日可有吉日?”
“回奏陛下,腊月初九乃是吉日,距今日时距也正好,恰能筹备婚事。”
“好,就腊月初九!张大将军,以后可要叫你驸马爷了呵!”刘澈畅快的举杯豪饮,坐下大臣继而恭贺声不断,丝竹声起,仙舞飘飘。
平乐公主微微勾起唇角,似在冷笑,眼角却瞟向陈美人,她微微举杯,笑意加深。陈美人懒懒的侧做在榻上,随意的玩弄着发丝,朱唇轻启,几不可见的说着:“恭喜。”看着眼前众人喜形于色的表情,平乐突然觉得很累,那高高在上的人呵,到底是不遗余力的将自己利用得干干净净的。
无声的饮下一杯酒,面无表情,就如同一个局外人冷眼旁观他人所上演的闹剧一样,就似一个布偶冥冥中被人牵扯着无能为力毫无自由,挣脱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