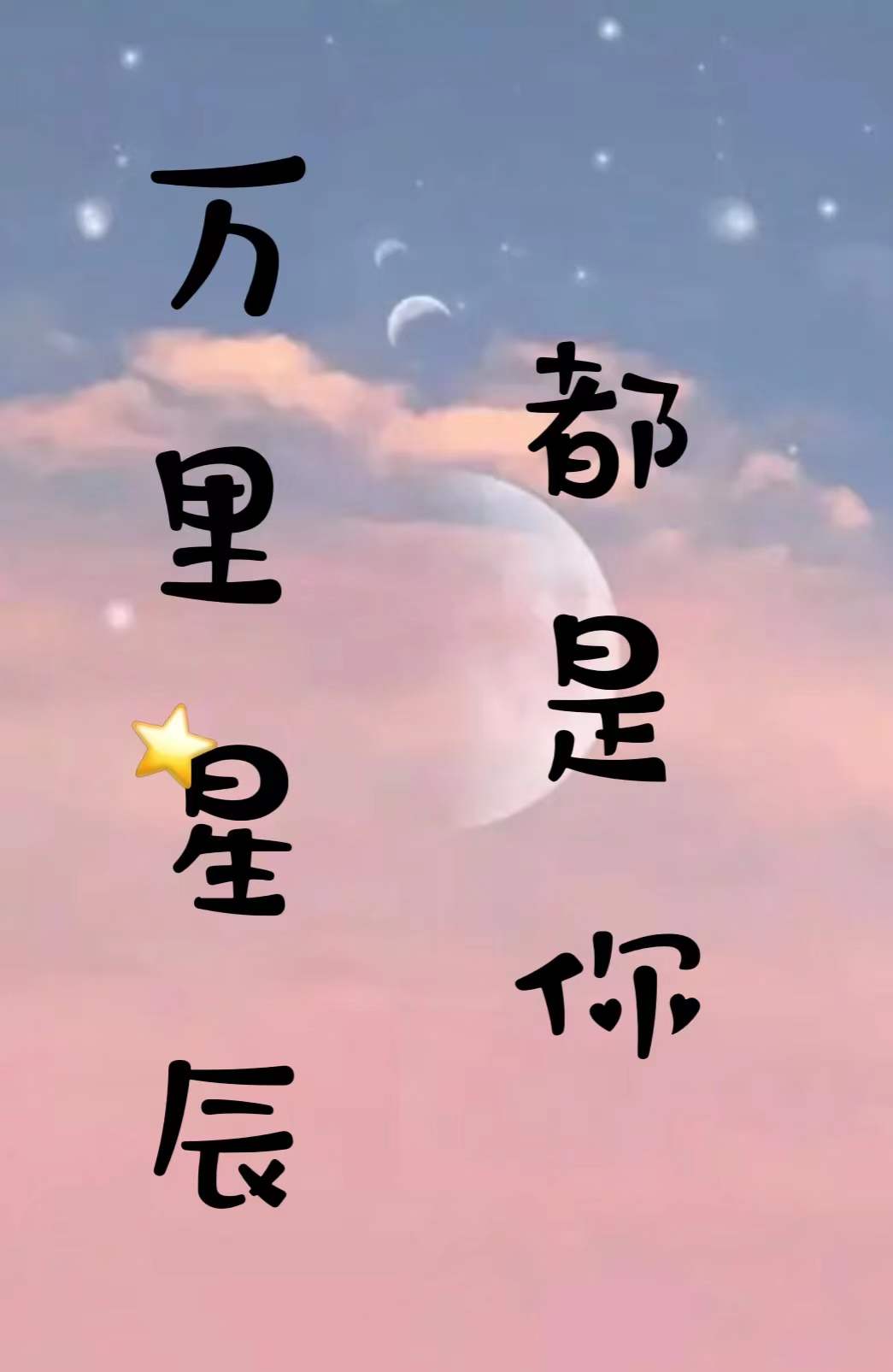序【3】
七岁,签过保证书的女孩,就读乡村小学二年级。
正是放学,学校外不远处三条路分叉口,一个单马尾小姑娘拽着女孩不让她走。
女孩心里害怕又无可奈何。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最终老师出来,才得以调解。
第二天,她被请家长了。
自己千防万防不让母亲知道的事,还是被知道了。这是她整个生命中第一次,也或许是最后一次被请家长--对方那个小姑娘先哭了,她被对方家长,自己母亲,还有老师,逼迫着道歉。
母亲一直向老师赔礼,母亲看她的眼光,像是要将她千刀万剐。
女孩最终还是低头道歉了,从此,她更加自卑,懦弱。
她知道,回到家,自己又免不了一场毒打。虽然早已习惯了,但年幼的她,仍是害怕。
她解释,没有人听,她更不敢说。
仍是熟悉的小破屋,熟悉的拥挤房间。父亲不知道在哪儿,女孩只记得耳边非常吵闹,两个妹妹坐在小小的电视机面前,看着电视。房间非常狭窄,却装着一张稻草铺的木房,一把竹子长椅,两个妹妹就坐在上面,房间里还堆着粮食。
女孩小小的身体跪在挨着门的床头,母亲收拾着东西,走路风风火火,她的表情,眼神,说话的语气,足以令女孩害怕至极。每次自己犯错,母亲都会先打她,再让她跪着靠墙,面壁思过。
忽然,母亲拿起一把衣架,女孩心里腾地一跳,已经形成行为习惯地哭着跑出家门。
母亲愣了一下,随即拿起衣架追了出去。
跑到外面放柴的小棚子,女孩被抓住了。母亲一下一下地打她,女孩哭得惊得人耳朵疼。
母亲进房间拿起她的书包就丢出来:“出去了就不准进家门!”
奶奶听到,出来劝架。
女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从不管母亲一家人的奶奶,为什么要帮她。她也不知道奶奶是什么性质。她只知道,在奶奶得知母亲生了她这个女孩后,要把她丢了,最后外婆把她拦住了;她只知道,在爷爷奶奶知道自己婶婶生了一个和她同岁的弟弟后,搬家尽全力,照顾出了一个蛮横,娇贵,还经常把手放到女孩下身隐私部位的男孩。
没有人听她低声哭喊,没有人听她解释。母亲只说她偷钱,不问原因。
因为,小时偷针,大时偷金。
最后,女孩认了。却再也不知道公平如何写。
她向着神忏悔:我确实偷东西了。我错了。
………正文………
“现在,告诉我,你们累吗?”方阵前,负责我们班的冯教官终于站了出来。
我没仔细观察过他,之前是因为比较懒,也懒得关心这些。
但现在,宅了两年的我因为某些事情才开始恢复锻炼,但对于这样在大太阳天连续站个一小时的事情,还真的是有些应付不过来。
冯教官是有些发福的。但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据说他是来这儿的教官中实力排名第二的。至于第一是哪位……喏,隔壁班那个长相儒雅,相处起来如沐春风,但明显训练得更可怕的男人……也不能说是男人。他看起来特别年轻,可能也只有二十或十九那个样子。
不过也是苦了隔壁班。从一开始看见帅哥教官的欣喜,变为被受魔鬼训练的悲伤。
收回目光,我的视线重新落到我们面前这个便宜教官上。
“不累。”经过一开始由于喊累加时间的痛苦,我们现在学聪明了一点。
没想,冯教官却严肃地看着我们,不知为何,我竟能从他眼里看出一抹狂笑——果然,他用一股正义感十足的声音,说出了能够让我们崩溃的事情:“既然都不累的话,那就再加半个小时吧。”
“什么?!”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是比这句话更能让人崩溃的了。
我也有些无奈,趁着人群杂吵的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刺目的太阳:它实在太过耀眼,在我眼里已经没有了完整的模样,只能透过眯起的眼睛留下的两条小小的缝,窥见它的光芒。(不好意思话有点多。)而下一朵能遮住它的白云,还远在天边,一时半会过不来。看来今天注定是要被晒成咸鱼干儿了。
“什么鬼啊?给你脸了是吧?!”
“你耍我呢!半小时又半小时,我们不中暑才怪!”
班上几个皮肤白得过了头的少年少女早已克制不住烦躁的心,忍不住开始骂起了教官。
“都给老子闭嘴!”
着实是万万没想到,表面上啤酒肚的男人,其实是这么有魄力:“你们才站多久?想当年老子是新兵的时候,第一次军姿训练就站了整整一天。才早餐吃完,一直到别人开始吃晚餐,我们都还在训练场上呆着。”
“我们又不是新兵!”立刻有人抓住了他话里的漏洞,尽管我觉得可能不怎么有用。
这时,旁边的一个教官也开口了。不过与冯教官不同,他是为我们求情的。
“冯教官,这些孩子说得也对啊,他们毕竟是拿笔杆的。我们完成上级给我们指派的训练标准就行了,没必要加训吧。”
原来任务已经完成了啊。我还以为我多么不行呢。松了口气的同时,又不免在心里骂骂咧咧。
忽然,趴在我背上很久都没有出现的那个阿飘开口到:“小叶儿快注意,前方有瓜,请准备好小板凳!”
听她惊喜的语气,我不免开始猜测是什么样的瓜了。虽然平时我也会默默看着旁人的热闹,但那都是一个人。现在却又多了个阿飘,虽然感觉没太变,但好歹是多了点活人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