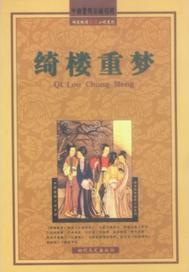淅淅沥沥的秋雨如母亲的双手,温柔地为这名为喀尔巴阡的孩子擦洗着沾满身躯的风露。
南方的乌云,边边角角尚还浅薄。夜幕的另一端,天堂灯塔的熠熠之辉接续中极北的虹桥,在中天凝噎的圣歌中,似乎正将一批批殉难的使徒引上归路。
“……歇息吧,战友!请原谅我的粗鲁;黎明前燃烧的故土,无法给你慰抚……”
“吱呀——”
老旧的木门粗暴地推开,山岚裹挟着雨滴席卷了逼狭的小屋,冲的本就略显黯淡的灯影一阵晃动。
凄怆悲壮的旋律被令人牙酸的门轴摩擦声肢解,穿着破旧军大衣的男人眉头一皱,拨开了留声机上略带锈迹的铁唱针。
来人有些神经质地朝黑漆漆的山道上瞅了几眼,才不安地关上了大门。雨点的滴答声中,借着渐渐稳定下来的火苗,男人仔细端详着来客胡须浓密的方脸,眉头依旧紧锁。
“别看了老兄,我就这熊样。”大胡子有些不满地嘟囔着,刻意压低的声音在风雨交加的夜里有些含混不清,“歌呢?咋不放了,这不挺好听的。”
“听个屁!就这烂歌还被你给搅和了。”大衣男人有些压抑地笑骂着。朝着大胡子的腰包勾了勾手指头。
“真是的,也不给我来一杯。”大胡子从腰包里掏出一封盖着火漆章的羊皮卷,自顾自地拔掉了威士忌的木塞,往嘴里大口大口地灌着。
昏暗的灯火下,大衣男人仔仔细细地解读着羊皮卷上的每一个字符,紧皱的眉头逐渐舒展,看到最后,双手甚至有些颤抖。
风势渐渐弱了下来,两道被文字和酒精刺激的有些杂乱粗重的呼吸,在静谧的小屋中越发清晰,与愈发急促的雨滴交融成曲。
“呼——”
长长地吐出一口辛辣的烟雾,大衣男人收拾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带着颤音发问道:“消息准确吗?”
“不会有错的。”
大胡子灌下了最后一口酒,斩钉截铁地回答。
“感谢上帝,为我们送来了如此丰厚的礼物!”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大衣男人瘫倒在椅子上,眼眶湿润地感叹道。
“谁说不是呢,”大胡子放下了空空如也的酒瓶,苍白的脸庞在酒精的作用下有些病态的红润,“还有吗,我还想再来点。”
“抱歉,这是最后一瓶了。”大衣男人转过头去,不再理会指着空瓶子的大胡子。
“别给我装糊涂!你那瓶十几年的白兰地我可馋了好些日子了!”大胡子指了指满是酒气的大嘴,骂骂咧咧地催促着。
“滚!想都别想!老子当年连枪都扔了也没放下这宝贝!”
“MD,看来我这辈子是没这口福了。”看着护犊子一样的大衣男人,大胡子不满地嘟囔了几句便闭了嘴。
雨点零星,滴答声的逐渐减弱,让两道粗浅不一的呼吸在幽深的寒夜里显得有些突兀。
“我该走了,记得替我向温莉问好。”
大胡子站起身来,清亮的月辉在他高大的身躯上流过,衬得本就惨白的脸庞愈加瘆人。
“等等。”大衣男人突然站起身,从身后的木柜里取出了一只标签模糊的玻璃瓶,琥珀色的醇酿在冷银的月色下轻轻震荡,愈发诱人。
“霍,铁公鸡怎么转性了?”大胡子显然吃了一惊,诧异地盯着友人。
“我改主意了,最好的酒就该找最好的朋友喝。”大衣男人默默地回应着,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将剩下的大半瓶酒都递到了友人手中。
“干杯!”
打量着手中自己垂涎多年的美酒,大胡子似乎有些触动。他点了点头,将瓶子在友人手里的酒杯上轻轻一碰,“咕嘟咕嘟”地把瓶子里的酒全都灌下了肚。
“走了!”
放下酒瓶,大胡子大步流星地朝门口走去。一旁,大衣男人将唱针拨回了原处。
“……安睡吧,战友!你将不再孤独;那晨曦中杀到的【翼骑兵】,如圣灵造的基督!”
“咚——”
如喀尔巴阡山般雄壮的身躯轰然倒下,银河的辉光如圣水倾落,照亮了战士腰间早已枯竭的血洞。尚未散去的雄浑余音,同大衣男人孤独的呼吸交织着,为殉道者送上最后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