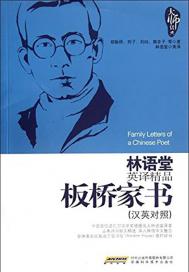向东北方向派出的两千疑兵走后不到一个时辰,阿达尔进来禀报:敌军有后撤迹象。
贺然果断道:“出击!紧紧咬住他们,以游击为主,你就当是咱们援军将至那样用兵,装的越像越好,抓到时机就狠狠打一下。”
阿达尔领命而去。大军发动时,贺然顶盔冠甲带领四百藏贤谷子弟及四百番王近卫随中军而行。
两军初始相距五十里 ,杀到敌营时已经是座空寨了什么都没留下,看得出他们昨晚就撤走了,只留下了一部分人在此虚张声势。见到这种情况贺然反倒是很高兴,这说明敌军将领已然受了各方假消息的迷惑。
得理不饶人的时候到了,贺然不住的催动大军猛追。
敌军并非是一味的逃跑,遇有高丘、长草地等可设伏的地形经常留下一小撮人布下疑阵,迟缓对方的追击,几经延误之后,阿达尔大为气恼亲自跑到先锋营作起了先锋官,这样一来追击速度快了很多,有几十个布疑阵的敌兵甚至都来不及撤走被斩杀了。
到日暮扎营时分,追出了不下两百里,两方距离再次拉近至五十里,这一天敌军丢弃的牛羊已不计其数,贺然传令一概不许收缴,要做出全力追赶的样子。
当晚,贺然把阿达尔从前锋营召回来,笑着道:“一会还得让你那些弟兄们辛苦一下。”
阿达尔会意道:“军师是要趁夜劫营?”
贺然点点头,道:“正是,可这次劫营所为不是杀敌,而是为把戏演足,让他们坚信咱们这支人马就是要死死缠住他们,为后面的大军争取赶上来的时间。劫营要谨慎些,或许敌军会有所准备,未免中计,不需要真的冲进敌营,派一千人作作样子就行了。”
“我这就去安排。”阿达尔领命欲去。
贺然唤住他道:“且慢,这作样子也是有讲究的,首先去的要早一些,过了午夜就行动,其次不是到那就回来,而是要多折腾他几个时辰,第一次撤回来后隐秘潜往东南方向,一两个时辰后再从那边袭扰一下,然后绕着敌营转到东方,把他们外围的明哨、暗卡都惊扰起来,这之后就可以回来了。”
阿达尔猜到了军师的用意,笑道:“军师是不想让他们睡踏实了,我明白怎么作了。”
贺然笑了笑道:“你只说对了一半,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乱其心神,让他们不敢来劫咱们的营,至少让他们不敢倾全力来劫营,敌军兵力三倍于我,必须让他们有所顾忌,否则今晚就难熬了。”
阿达尔皱眉道:“军师这么肯定他们会来劫营?这一天追逐可都够累的了。”
贺然平静道:“如果白莲花真的受过中原高人指点,那今晚很可能会这样作,你不能再凭以往经验对敌了,咱们得提高警惕,宁可让弟兄们辛劳些多作些准备也不能稍有疏忽,敌军若来劫营那他们可是动真格的。”
“我把前锋营向后收一收吧。”
贺然淡淡一笑道:“敌军不来则已,若来了要劫的就绝不会是前锋营,而是绕过前锋营直奔咱们这里,以图一举击溃咱们这支人马,这样就可从容面对后继到来的敌军了。”
阿达尔想了想道:“军师分析的或有道理,那咱们怎么应对?”
贺然嘴角含笑道:“若论防守可是我们中原人的拿手好戏,你该怎么设哨卡就怎么设,我会增派我的人暗中警戒,扎营时我已经安排好了如何防范敌军偷袭,只可惜我们善用的火油等军资匮乏,否则他们来了就别想再回去了,现在只能把他们惊吓走然后掩杀一阵,你去营寨查看一下吧,如见有不妥的地方就跟云野商议。”
阿达尔出去看了看,见四下易军正带领这番兵紧张的忙碌着,有的在挖陷坑,有的在设拌索,还有的再做着他一些他看不明白的事情,整个营寨与平常所扎营寨并无什么区别,不过前半部营帐是空的里面堆了干草,军卒都集中到了后面,成月牙形布局,在后营见到云野时,他正通过万金对几个千夫长吩咐着什么。
云野看到阿达尔后笑着迎了上来,低声对他解说了军师的各项安排,阿达尔听的不住摇头叹息道,“你们中原人打仗的招数真是太多了,以后我可不敢去劫你们的营寨了。”
云野哈哈笑道:“这些能算什么,若是所需之物齐备了,更厉害的招数还多着呢。”
阿达尔暗自咋舌。闻知主将回来了,一些心有怨气的将领纷纷找来,低声抱怨易国军师这样作太多余了,让士卒不堪劳乏。阿达尔虽也有此想法,但这个时候只能一一安抚,上次中伏之败让他有些底气不足了,不管怎么说,人家易国军师来了之后稍动心机就把敌军吓退了,仅凭这一点人家就比自己高,何况他已听说了,军师在乞扎里山那边动了动嘴就逼得赵国军队临阵而退,使敌军阵脚生乱,帮大王痛痛快快的大胜了一场。盛名之下无虚士,这位年轻的易国军师确实有两下子。
用过晚饭后,贺然传令全军早早歇息,任何人不得走动喧哗,这些番兵番将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就算明知晚上会有人来劫营亦可安稳入睡,何况他们大多数人心中都觉得这事不太靠谱,所以很快就鼾声四起了,这一天真是太累了。
藏贤谷子弟睡得更是踏实,以前高强度的训练早已让他们对这些习以为常了。午夜刚过,云野唤起了一百人,交代了番语口令后不用过多吩咐,这些人就潜入夜色中各司其职的担负起远近各处警戒任务,为了便于易国军卒记忆,这口令设置的极其简单,几个音节不至记错。
阿达尔没有睡,尽管对易国军师的话半信半疑但不敢稍有大意,他本来就是个谨慎之人,上次之败让他变得愈发的谨慎了。独自喝着酒,他回味着易国军师跟自己说的那些话,尽管对方没明说,但他如何听不出其对三弟的疑心呢,这让他心里很不痛快,不过他比巴彦尔要稳重的多,不愿因这事而起争辩,易地而处他能体谅对方为何这么想,毕竟相处日短,他还不了解乙安宗。